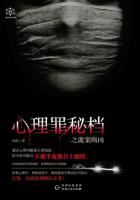她一口气跑到医院的门口,搭乘了一辆出租车,直接去了爸爸和小陈阿姨居住的家。
是小陈阿姨来开的门,见到她,意外地睁大了眼睛。
“爸,”豆崩故作轻松地走进客厅。父亲坐在电视机前的沙发上,电视机开着,但是父亲却在看报纸。
弟弟并不在客厅,听说他今年是关键的小升初,肯定在房间里做功课呢。
“你怎么来了?”父亲放下报纸,问道。
“我到这边来办事,顺便过来看看。”
“你在这边会有什么事?”
这时小陈阿姨急忙插了一句:“你还没吃饭吧,正好还有剩的。”
豆崩忙道,“好吧,我还真的好饿。”
“那你直接说是来蹭饭的不就好了。”父亲重新低下头去看报,他明显地消瘦了不少,却又像没发生过任何事一样。
“你去洗洗手吧。”小陈阿姨说道。
豆崩答应着进了洗手间,她关上门,既没有洗手也没有上厕所,只是直接坐在马桶盖上,她想透一口气,感觉胸口堵得厉害。因为一进门时就看见餐柜的旁边随意靠着一副双拐,陡然间悲从中来。她竭尽全力表现出什么也没看到,的确是路过蹭饭而已。
并没有看见轮椅,估计放在阳台上吧。
豆崩调整好情绪,才从洗手间出来。每个人的演技都是这样练出来的,你做得很好。豆崩这样安慰自己。
小陈阿姨已经热好了饭菜放在餐桌上,米饭和白萝卜焖排骨。小陈阿姨还问:“要不要给你煎个鸡蛋?”豆崩说:“不用了。”
这时她发现那副拐杖已经不见了。
豆崩大口吃饭,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幸亏她背对着父亲,父亲也并没有注意她。
小陈阿姨急忙起身给她倒了一杯水。
她微低着头,不看她。
那个晚上,她和父亲之间几乎没说什么话。父亲还一个劲地催促她:“天都黑了,你还是赶紧回家吧。”
小陈阿姨送她出来的时候,豆崩含糊地说了一句我们还在想办法。但是小陈阿姨似乎已经感觉到了某些端倪,脸上的神情变得有些僵硬,虽然她一直都在安慰豆崩说别太难过了,又自责自己那天实在是太冲动了,不应该跑去找豆崩诉苦。
但无论如何,可以明显感觉出来她的无奈和悲伤。
经过一路的颠簸和塞车,子弹头终于停进了车库。直到管家跳下车,为豆崩打开了车门,豆崩才如梦方醒。
她不再气急败坏,沮丧之情牢牢笼罩着她。
野晴小姐还没有下班,这让豆崩暂时松了口气,否则开场白还真让她不知所措。
她的房间被保姆打扫得一尘不染,有一种久别重逢的亲切。
豆崩当然不是总住在天台上的帐篷里,不过是想检验一下自己有多么与众不同。离家数日,最想念的还是可以肆无忌惮翻滚的大床。
张豆崩一个大字倒在松软的席梦思上。
不过很快,父亲治病的现实又开始让她心绪纷乱,心情就像打摆子一样忽冷忽热。热血沸腾的大吵换来的却是冷若冰霜的沉默,这便是母亲送给她的别开生面的挫折体验。
她明白了一个道理,钱这个东西无论作何用,也无论是对多么亲近的人开口,人家不给你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的。
她坚持不睡,但还是关了灯。竖起耳朵,等待着野晴小姐在黑暗中推门进来,矗立在她的床头。她要对她说,爸爸已经出院了。此后便不发一言,在难堪的长时间的静默中泪流满面。仅仅是这个想法,她自己已经提前泪流满面了。
然而她并没有等到那种她认为经典的画面,便草草睡去。
第二天早晨,她在早餐桌前,看到了正襟危坐的正在喝鲜榨西柚汁的野晴小姐。野晴小姐微微扬着下巴,一副胜利者的姿态。
数日的精神折磨让豆崩低沉而恭敬地说了一句:“早上好。”
野晴小姐嗯了一声示意她坐下来吃饭。
西柚汁可以说全是苦涩,豆崩不免皱了皱眉头。
“有减肥作用。”野晴小姐平淡地说道,“对一个女孩子来说,身材比博士文凭更重要。”
豆崩又喝了一口西柚汁,以她此刻的心情,实在不想谈减肥这个话题。然而当她放下厚实、坠手的水晶玻璃杯时,发现装有火腿蛋和全麦面包的白瓷盘旁边有一个信封,“这是什么?”
“打开看看不就知道了。”野晴小姐面无表情,还指责豆崩道,“不要总是用夸张的表情,会长抬头纹的。”
这也的确是野晴小姐的风格,她极少大笑。
豆崩打开信封,是一个存折。翻开,上面的钱数让她的嘴巴瞬间变成了O形。旁边还有一张名片。
野晴小姐解释道:“名片上的人是治疗股骨头坏死的专家,他说如果有条件到美国去做手术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你让他们自己去商量吧。”
豆崩激动地一个劲点头,几乎窒息。
“不像你想的那样,”这时野晴小姐已经起身,将餐巾轻轻放在餐桌上,冷冷地说道:“不要误会,治病和爱情没有关系。”
张豆崩微笑着看着母亲,原先苦涩的西柚汁开始回甘,不仅在嘴巴里,同时在心里都有了一丝甜意。
豆崩很想拥抱一下野晴小姐,不过她没有这么做。
野晴小姐说过,儿女才是这个世界上最势利的人。
直到走至门口,野晴小姐才轻抚额头,背对她说道:“哦,对了,密码是他的生日。”说完之后便优雅地走到门口,换上她的红底高跟鞋,一摇一摆地出门了。
豆崩只能行注目礼,望着野晴小姐美丽而冷峻的背影远去。
5
琴声。
还是琴声。这些单调、乏味、硬邦邦的练习曲,崖嫣都听恶心了,听到想吐。琴房里的那架钢琴,在崖嫣的眼睛里只不过是一台冰冷的印钞机,家里全部的吃穿用度都是妈妈一下一下弹出来的。
妈妈今天偏头痛,头上扎着日本浪人一样的布条,耐心十足地教着那些孩子。崖嫣心疼妈妈。
妈妈说:“我这辈子做得最正确的一件事就是生下你。”
因为崖嫣与年龄不符的冷静,让她成为妈妈的精神支柱。她曾列举了单亲家庭子女的十大优点,其中包括懂事、少言、替别人着想、会做家事、会照顾人等等,也让妈妈对她的自信另眼相看。
星期天的下午,崖嫣塞着耳塞在家煮中药。
母亲大半年没吃的中药,又开始生生不息,就在她那天去见了江渡的爸爸之后。
那个被兰老师捧上天的“永远不会独行”的心理师,不止一次的到班上来进行心理辅导。虽说是满心抗拒但也必须坐在他的面前,他熟悉崖嫣全部的个人资料,表现得比她自己还要了解她。不过别的没记住,只记住他分析崖嫣的母女关系时用了一个词汇,叫作“母女倒置”,意思是在实际生活中,崖嫣充当了母亲的角色。
当时只当是听了一则鬼吹灯的故事。
现在想起来,或许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那一天隆重的约会,母亲回来时的情绪却十分沮丧。她跟崖嫣讲了她和江渭澜的故事,虽然她努力作出轻描淡写的样子,但也能听出来她伤得很重。居然住进精神科,医生说低血糖脑病随时可能不再醒来。
她还写过一本《死亡日记》交给江渭澜的妈妈,担心江渭澜回来找她的时候无迹可寻。
崖嫣没有掉一滴眼泪,心里满满的都是怨恨。
“我都不记得我们拉过手。”母亲不知想说明什么。
这是最让崖嫣愤怒的一句话,没拉过手,就什么都不欠吗?就是免责条款吗?这是什么逻辑?相思可以致死啊。杜丽娘。梁山伯。林黛玉和贾宝玉。也是因为这句话,崖嫣替母亲不值。
“妈,你是想说你们很纯洁吗?”
“我们就是很纯洁。”
“彼此拥有心灵。那你现在还拥有他啊。”
“你是在嘲笑我吗?”
“是他一声不响地走了,早就把你忘了,你没有那么重要,是可以一刀两断的过去。这就是事实啊。”
“是啊,必须承认这就是事实。”
“你也要跟过去一刀两断。”
“……本来以为这辈子再也碰不上了,没想到……你说我是花痴,他过得好像也不见得有多好,那么黑,那么结实,两只手粗得让我想哭,脸上还有一种奇怪的凝重。”
我看他一切都好。崖嫣极想这样驳斥母亲,他们一家四口其乐融融,幸福温暖。而我们呢?实际上是我们活得凝重。尽管崖嫣什么都没说,但是内心深感母亲仍然活在历史的阴影里,所以她决定不跟这家人有任何的关联。没有命运的交错也许是最有力的报复。
所谓美好的东西变得不堪一击,全部都是碎片。
虽然陷入遐想,仿佛化身复仇女侠。但是看上去崖嫣却是端坐在陈旧的台式电脑前,百无聊赖地挂在网上。
这时QQ里亮起了一个熟悉的头像,是程思敏。
“干吗呢?”
“煮中药。”
“闷吗?”
“还好。”
“我过来陪你吧。”
“不用了。”
程思敏不再回复。
知道他的心意,是他给她寄了一封同城快递,里面有两本她想看的书,估计是在读书会活动时无意中提到过。另有一本手抄的诗集,上面用英文写着:送给崖嫣,我的早晨、阳光和雨露。下面的落款是思敏。
全部是那种看一遍就足可以得糖尿病的情诗。
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读书会或公益活动中,他们经常见面,但是他却小心翼翼地寄给她珍贵之物。
那些诗句也的确像冬天里的一杯热巧克力,温暖了她的心。对于饥渴的人,幸福就是手边的那个富士苹果。
她完全可以告诉他谜底。
神使鬼差,她居然什么都没有说。明明知道这么做一下子辜负了两个人,两个对于她来说最亲密的人。
但是以当时的心情仅仅是想做一千件一万件坏事,来弥补内心深不见底的空虚。都说我们是自私的一代,可是有谁真正看到,并且理解我们的孤单——孤单到想象出一个父亲还要被拎出来示众。那些所谓的关心并不是崖嫣所需要的,孤单无解,这就是事实。
妈妈的角色让她更觉得孤单。她不能想象跟那个叫江渡的人怎么风花雪月,眉目传情。
她和程思敏开始互粉,在QQ上聊天。
他第一次到她家里来是给她补习数学,崖嫣的数学一直吃力。程思敏的讲解温和、耐心,而且看上去精力充沛。只是第一次可以明显感觉到他的紧张,一直都在讲数学,整整一节课的时间。后来就好了,他们经常插出去讲一些八卦和学校发生的好玩的事。
再回到数学,崖嫣更觉头大,不禁叹道:“我想我根本考不上大学。”当时程思敏脱口而出,“那有什么关系,你还有我呢。”这是他说过的最像样的一句表白。
这话她没接住,掉在地上,碎了。
但是他仿佛并不介意,又说他的意思是就喜欢平凡平淡柴米油盐,喜欢古老的穿着长布衫的教书先生的样子,想象着伟大的鲁迅先生也曾在灯下记豆腐账。
“我就想当个教书先生。你呢?”
“西点师。有自创品牌的小店。”
“那我们就握握手吧,”他伸出手来,“因为自甘堕落是可耻的人啊。”他笑起来,牙齿整齐洁白。
他们握手。他的手比预计中晚两秒钟松开。崖嫣想起兰老师提出的“我们清华见”的口号,同学们很振奋,许多手撂在一块高喊“加油”,彼此都激动得热泪盈眶。
她也问过他:“你为什么不读藤班?”
“因为害怕孤单。”
“怎么讲?”
“我很小的时候就被束之高阁,一个人在一间办公室里做题,受到夸奖和称赞。但是心里空荡荡的,觉得不会做题反而好,可以去球场踢球,还可以用仿真的鬼头套吓唬女同学。”
“原来是这样,我一直以为你的内心很骄傲呢。”
“也是在那段时间,我看了一些佛教方面的书,觉得许多话都说到我的心里,尤其骨粉弘一法师,从浊世佳公子到黄卷孤灯人,他的内心和品格强大到我不能想象。后来几乎是以戒毒的方式戒掉了,关于他的书也全部送人,一本不留。”
“为什么?”
他沉默了很长时间才说:“我不想让我的爸爸妈妈伤心。”
看得出来,这些话他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因为很难开口的样子,也因为他的眼角可以感觉到微微的晶莹。
崖嫣有些惭愧,她觉得应该跟程思敏道出实情。
对于江渡老师,她并没有丝毫悔意。如果说是给多年积累的负面情绪找到了发泄口,怨他抢走了自己的爸爸实在牵强,但又唯有这么想才觉得解恨。为母亲,也为自己。她不会跟他们家的人有任何来往。
然而对于豆崩,却是抱有极大的歉意。
她们是闺蜜,她们是闺蜜吗?为什么她会从心底嫉妒她?就因为她有钱?有爸爸还有一个弟弟?但她什么都没有。
这也是她痛恨江渡老师的原因,他让她变成了一个坏小孩。
她本来一直以为她和豆崩之间的友谊坚不可摧,然而华丽的泰坦尼克号冰海沉船也不过是一瞬间的事。
这时门铃响了,一下,两下。
崖嫣跑去开门,见是程思敏,竟然也并不觉得意外。
他现在的身体比以前强健许多,大概又从心底放弃了自己,所以总是一副拉风的表情,看上去颇有喜感。
一只手还提着一个打包的圆形饭盒。他解释说是芋圆红豆,想到崖嫣的妈妈吃中药会很苦,特地买给她缓冲苦涩的。又说他家所在的那条街一口气开了五家所谓的台湾甜品店,想也知道最终必死无疑,不如在关门大吉前多吃一碗。因为有竞争,每个店都饱含十足的诚意。
崖嫣心里也承认,程思敏因为付出真情,让人难以拒绝。
她说:“你突然跑过来干什么?”
“陪你熬中药啊。”他正色回道。
“难道我们两个人对着一罐药发呆吗?”
“也不是不可以。”
他们进了厨房,第一轮的汤药已经煲好,崖嫣把汤药倒到小陶瓷碗里,准备翻渣煲第二遍。倒药的时候,她侧着头,有一绺头发滑落下来,程思敏自然地帮她轻轻拨到耳后。
这让她想到程思敏的诗集里,有村上春树先生说的,如果女孩答应喜欢的男生,男生就可以帮她拨一下头发,若并没有答应就告诉她头发乱了。说这大概是最纯洁的爱情观。程思敏把那些并不是诗句的但是老辣温情的话断开,变成了诗句。
没有村上的青春应该是不完整的吧。
崖嫣心想,她今天无论如何要对程思敏说实话,否则都没有办法原谅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