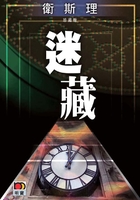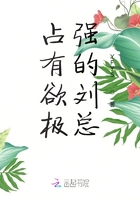后来,清理事故现场,并没有找到王觉的尸体,他是在一瞬间被深深地掩埋了。他的墓碑下面是一个衣冠冢,只有他的一套2号军装和军帽。小贞曾在结婚前提出要去看一看王觉,他们便一块回了老部队,回了那个墓园。小贞抱着墓碑,她的单薄的身体伏在墓碑上,哭了很久。
江渭澜和王觉过去的战友,那时已荣升为指导员,他把江渭澜拉到一边,他说,你跑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回家?你的父母大老远跑到部队来问我们要人,结果谁都没有你的消息,那边民政局的复员军人办公室也查了,说你根本没有去报到,我们也觉得奇怪,难道你人间蒸发了吗?怎么可能?为什么呀?江渭澜说,我直接去了深圳,那边是特区,大搞城市建设,活儿多,在部队干苦力,回去也只有干苦力了。
指导员还是不理解,他说那也要回家啊。江渭澜马上说回了回了。算是搪塞了过去。
那些石头,几乎让他窒息。年轻的浪漫的心根本接受不了残酷的现实。
所以,江渭澜才会做出决定,他要成为王觉。如果命运注定需要一辈子扮演王觉,那他就是王觉。
这是他跟小贞共同的救赎之路,此后都是余生。
他不能回家,回自己的家。
他知道回去,他就走不出来了。不为什么,而是他有他的生活轨迹。生活本身有很强的还原能力,就像太阳每天从东方升起,就像鱼在水里,香蕉呆在香蕉皮里,年画贴在墙上,筷子成双鞋子成对,火车在铁道上飞驰,总之他没有能力和生活对抗。
他要成为另一个人,就必须和从前的一切彻底告别。行注目礼。永远保持沉默。
在此后漫长的岁月里,他也曾经想过他的另一种人生,或者考上了音乐学院的作曲系,成为庞大的交响乐团的指挥,开始创作自己的音乐作品,一展个人艺术生命的蓝图。或者只是在乐团当了一名首席小提琴艺术家,演绎古今中外的经典曲目,每一天都可以是自由的、轻盈的。
但他知道,江渭澜已经死了。
王觉不拉琴。在去深圳的前一晚,他在江边拉琴。一曲终了,他伸出左手,优美的小提琴悬挂在半空中,不胜细雨凉风的娇羞。一松手,香琴入水,很快就看不见了。
还是老兵见多识广,部队的确是成功的地消灭了他的爱好,从此再无踪迹。
只是,那一天他拉的曲子不是《野蜂之舞》,而是《梁祝》。
6
光控的街灯还没有完全熄灭,江渭澜看了看手腕上黑色的电子表,是清早差五分钟七点整。雨虽然是停了,但仍旧是阴天,阴沉得差不多要掉下来,天地间仿佛支起偌大一个帐篷,一切都灰蒙蒙的,总之天低云重。
昨晚,在暴风雨的间歇中,算是把家搬完了。拖拖拉拉的直到天亮,客户自己都不好意思了,一个劲地解释风雨不由人,因为是选定的日子,所以抱着下刀子也要搬家的心理,想不到还是人算不如天算。江渭澜反而没说什么,心想这也是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好差事又怎么可能轮到小蚂蚁。
虽然得到双倍的报酬,但是一家三口已经累得筋疲力尽。
回到家里,小贞赶紧去了厨房做简单的早餐,因为江渡要赶回学校上班,江姜也梳洗完毕要去上学。只有江渭澜坐在客厅木制的长椅上点着了一支烟,顿时感觉整个人散了架,就是那种形神俱散,都收拾不到一块了。
他得承认他老了,昨晚搬家要是没有江渡,还真吃不住劲。好在江渡年轻,又一直坚持长跑,身体强健。居然一个人背着高过他的大冰箱下楼,令江渭澜暗自吃了一惊,不服老还真不行。
江姜倒是精神焕发,头发一丝不乱的梳着马尾,衬着一张小蜜桃脸分外紧致。她背着书包径自向门外走去。
小贞追出来道:“你不吃饭了?”
江姜不屑道:“我去肯德基吃法国烧饼。”说完头也不回地走了。
小贞转过脸去就冲着江渭澜道:“是你给她的钱吧?”
江渭澜不说话,只是笑了笑。他有时候想,家庭关系就是金钱关系,没有什么道理好讲。他偷偷给江姜零花钱,马上就和好如初。
小贞又道:“你就惯她吧,都没样了,我们一晚上没回来,累成这样,她问都不问一句,什么人啊。”
江渭澜轻描淡写道:“女孩子嘛,任性不了几年。”
小贞张罗着把早餐端上桌,也就是白粥、蒸花卷和几样咸菜。
江渡一边用干毛巾擦着头发一边走进客厅,他换了一件三文色的衬衫,藏蓝色的毛背心。身板笔直如坚实的倒三角,加上微湿的头发,犹如刚出锅咬一口就会爆浆的青玉米,饱满而性感。这在江渭澜眼里不仅是王觉,简直帅气得如好莱坞明星。
江渭澜不觉想到,哪怕自己的人生就是由若干次破产所组成,得子如江渡也是夫复何求。
江渡听说江姜去吃法国烧饼了,笑道:“江姜本来就是爸爸的小情人嘛。”
江渭澜一边喝粥一边抿着豆腐乳,似是很享受平淡中的滋味。
小贞说了一句:“肉麻。”
三个人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笑毕,江渭澜还是对江渡说了一句:“昨晚真是辛苦你了,今天还要上班。”
江渡笑道:“妈,你说我是爸亲生的吗?”
小贞当即脸色微微一暗,不觉人察地跟江渭澜对视了一秒钟。好在江渡又道:“怎么突然跟我客气起来了?我就是家里的小毛驴啊,你们都老了,有事不找我还能找谁?”
江渭澜和小贞又都笑了。
江渡飞快地吃完饭,出门上班去了。
剩下的两个人还在慢慢吃,隔了好一阵,江渭澜才道:“永远都别跟他说,他就是我儿子。”
小贞点头,然而表情却是那还用你说吗?
江渡七岁的时候,江渭澜给他做了一个弹弓,他的观点是男孩子小时候没玩过弹弓就不知道自己的性别。很快,江渡就用弹弓打烂了教学楼的玻璃,被叫到老师办公室的外面罚站,而且要家长到学校赔玻璃、领人。
江渭澜在老师面前点头哈腰,掏腰包赔钱。出了学校的门就带江渡吃了顿麦当劳,后来两个人手拉手嘻嘻哈哈回了家。
小贞说:“他在学校闯了祸,你不骂他也就算了,难道还奖励他不成?”
江渭澜道:“男孩子哪有不闯祸的?又不是什么大事,你看你严肃的样子,跟计生办主任似的。而且学校负责罚他,我们负责爱他,不就是这么回事嘛。”
江渡十七岁的时候,利用一个暑假的时间,跟着江渭澜泡在建筑工地上,什么也不干,只是当跟屁虫。
就是体验一下“父亲每天在外面都干了什么”。
即便如此不等于不辛苦,江渭澜说起来算个工头,大伙都叫他江队长,但是他什么活都得干,在烈日炎炎的高温下东奔西走,登高爬低,解决各种问题。有技术层面的,也有人事矛盾,还要跟各种各样的生意人打交道。
第一天吃的第一顿饭是中午一点半,盒饭,可疑又难吃的样子,大家都一样。江渭澜没有半点特殊,这种习惯应该是在部队时养成的。
江渡真的是给饿稀了,但因为热得吃不下东西,下午就中暑了,大汗淋漓的晕倒在地,被父亲背回了家。
一个假期下来,江渡晒得何止又黑又瘦,简直就是三度烫伤。小贞都有点看不过眼,半夜起来坐在儿子的床头,给他扇扇子。
那一年的夏天,天热地辣,人像吃了毒蛇椒似的,擦根火柴都能点着。
江渭澜说,这还是性别教育。
上一次破产之后,父子两人已经可以开始男人之间的对话。
也是一个傍晚,也是在自家的天台。江渡困惑道:“我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你这么落力的工作,又这么讲诚信,但是为什么……”他没有把失败的人生这几个字说出口,觉得无论如何太伤害父亲的自尊心了。
所以后半截话以沉默结尾。
见父亲无语,江渡又道:“可是有的人,坐在国家给的位置上,拿着国家的俸禄,有权有钱不愁吃喝,为什么还要鱼肉百姓?让人有理都没地方去说?怎么这样的人都过得比我们好?”
江渭澜叹道:“杀人放火金腰带,铺路修桥无尸骸。从古至今都是如此啊。”
“那还有人当好人吗?”
“你以为当好人是为了什么?好人是最没用的,不当吃喝,现在说谁是好人就是一句骂人的话,无非是没用的意思。”
也许实感意外,江渡的脸上出现了若干惊叹号。
“做好人只是为了心安啊,孩子。”
江渡没有作声,他还太年轻,不是那么明白,也不一定觉得心安那么重要。
江渭澜想了想,又道:“其实人生无所谓成功还是失败,因为既没有统一标准,也没有正确答案。你看十三行行商潘振承,当年是世界十大富豪之一,占住几条街修潘家祠,如今只剩下半间破屋出租放货,连匾额都没有了。所以我看人这一辈子唯一要做的,就是把心给安置好了,人不就是活个踏实吗?”
“那你的心安置好了吗?”
江渭澜觉得答案是肯定的,但当时却出乎意料地沉默了。
老半天,才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
从前的一家人,无论过得怎样,都要整整齐齐地去一次艳芳照相馆,开票,等着叫号,然后整理一下头发和衣服,照一张全家福。这样一张黑白照片可以说是人有我有,家家都有。江家当然也不例外。
照片至今还挂在客厅的墙上,江渡就站在江渭澜的身后,一只手插在裤兜里已经会扮潇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