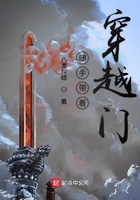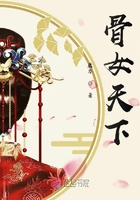霍去病撑起身子,活动了活动小腿,韩陶刚才的神情蓦地掠过眼前。适才王唊提到小人误国的时候,人人都垂头叹息,只有韩陶似乎颇不以为然。他在朝鲜一向职掌藩市,与中国打交道的机会要远过他相,中国的国力兵备他应是了解甚多,理应对王唊的话更有感触才是。
他思绪翻涌,尚未理出什么头绪,突然听到车外金铁交响,一人大声喝问道:“什么人如此大胆,竟敢拦阻郡驾?!”霍去病皱了皱眉头,出没如此风雨之中,难道竟是歹人行劫不成?那可真是个天大的笑话了!霍去病耸了耸身,抬手将门帘打开一条缝隙,扒开牛皮围障,烟雨朦朦之中,根本看不到前方发生了什么变故。
“东郡楼船司马邢而道,求谒郡守任大人!”雨中传来一把低沉的声音,霍去病摇了摇头,这个小小六百石的部尉司马在如此雨夜求见任破胡不知所为何事?“大胆!”霍去病这回辨认出是董戚泽的声音,“你个小小的部尉司马,居然也敢惊扰骠骑将军与郡守大人的车仗,难道你就不怕人头落地吗?!”“都尉大人!”邢而道并未因董戚泽的威胁而稍显却步,依然不卑不亢的回道:“卑职既然敢只身前来,自是早将生死置之度外。只求都尉大人应允卑职所请,卑职随后甘将人头奉上!”
霍去病闻言不禁一愣,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竟使得此人不惜身命的要与任破胡谋见一面?他脱手放下帘栊,身子向下沉了沉,心中一时犹疑不定。“放屁!”董戚泽怒斥一声,“亏你还在军中身负职司,居然敢腆颜说出这么无耻的话来!等秩难道对你来说只是摆摆样子,说逾越就可以逾越的吗?!还不赶紧退下,给我回到营中候罪。来人,把他给我叉到路旁!”霍去病立时立时听到几声怒喝,跟着“扑通”声响,似乎有人被击倒在地。“邢而道,你小子造反了!”
“卑职不敢!”邢而道的语气中却无丝毫不敢之意。“卑职既未手持凶器,又未动手伤人,大人如何就为卑职定下这样一个不赦之罪?”“你......!”董戚泽一时语塞,张着嘴说不出话来。“邢而道!”任破胡苍老的声音在董戚泽的身后响起,不知何时他已经离开了车驾。“你要陈说的可是有关军务吗?”霍去病点了点头,姜还是老的辣,如果事干军务,邢而道确是有权越禀。“那倒不是。只是事关军校生死,卑职恳请郡守大人过问!”霍去病这才松了口气,既然与军务无关,那便事不关己。如此暴雨滂沱之中,哪有什么能比一壶热茶更让人舒服。他将臀部重又坐回腿上,眯起眼睛,只待任破胡打发了此人再继续行程。
“邢而道,我看你是糊涂了!”任破胡的声音不高,却充满了威严。“东郡水师在我的治下,但有所请,你自可禀陈部尉沈无伤,回头自可由他向我面陈。千万不要因一时情急乱了律条,自毁前程。现在让开吧,不要拦阻了骠骑将军的车仗。”“大人!人命关天,须臾不待啊!”“嗵”的一声,似乎是邢而道跪在了泥水之中。
“我告诉你,不要再得寸进尺了!”不等任破胡答话,董戚泽已经抢着说道:“郡守大人宽仁,不说如何治你的罪,你还不赶紧退下思过,居然还在这里胡搅蛮缠。难道我大汉的律令真的就奈你不何吗?郡守大人虽不追究,本都尉可放你不过。来人,将他拿下候问!”“慢着!”邢而道的声音响起,“不知都尉大人要以何罪名刑拘在在下?”“你顶撞上官,语多不敬,本都尉难道还拿你不得吗?!”
邢而道深吸了一口气,朗声应道:“卑职虽然奉任东郡水师职司,但受命征伐,尚未归建。都尉大人您似乎没有权力羁押在下!”“猖狂!”任破胡闷声接道:“你奉有楼船将军的军令吗?私离大营,董都尉自然有权将你羁縻至杨仆将军处听候军法。亏得你还敢在这里肆意张狂!”默然半晌,只听邢而道缓缓说道:“卑职本非妄人,自然也知尊卑有序。今日若非情势逼人,断不会出此下策!家兄千人邢自古现在营中候斩,而道只求大人可以主持公道!”
“哦!”任破胡此际仿佛愣了一下,“邢自古的事情我是知道的。他无视郡令,擅自封锁河道,依律自是当斩。而且......”他似乎犹豫了一下,“处斩邢自古是我的意思。沈部尉昨晚连夜突审,邢自古宁死不言。沈部尉是因县守与兵备相结,怕其事干叛乱,所以才不得不因势立斩邢自古,以免更遗祸胎。何况此事也已上报廷尉,这样你还觉得有什么不妥吗?”“正是!”邢而道见任破胡也是这种说辞,不由得提高了音量喊道:“不知大人可曾想过,只言不发也许是为势所迫。俯首认命,或许正是蒙冤待雪!”
“胡说八道!”不等邢而道说完,董戚泽已经插言道:“邢自古罪无可绾,当然只有俯首认命了。他阴结县守,而且斗胆在我楼船军即将行经之际,私命属卫封闭黄河水道。若说其无反意,那可真是天理难容了!”“你才真是一派胡言!”邢而道抗声道:“我绝不相信家兄会有叛乱之举。何况苏县令父兄尽在朝中为官,如果真是事涉干犯,岂有不追查清楚,而直接斩了嫌犯的道理!”
霍去病心内暗自点头,邢而道这话问的有理。不管邢自古是否事涉谋反,杀了他只会令事态更加难明,不知任破胡该怎样解释?看不到任破胡是怎样表情,只能在风雨夹杂中听到他的声音,似乎并不因邢而道的质问而为忤。“你说的情形理应无此可能。沈无伤是他的上官,平素并无恩怨相结,断无构陷他的可能。而且本郡生怕出现冤情,昨日特命董都尉随堂听问,即便邢自古有什么难言之隐,也无须更加隐瞒。他既无言以对,当然是默认了自己的反迹。何况他擅自封闭河道,为一众楼船卒所亲见,更无冤枉的可能。”
顿了一顿,他又道:“更大的问题是,邢自古的事情已经在军中引起骚动,随从闭锁河道的楼船卒颇有自危之感,虽然沈部尉已经宣称此事乃邢自古假符出兵,但假以时间,恐怕仍会淆乱军心,甚至使得邢自古部属就此生事。趁着楼船大军栖泊于东郡之际,本郡想以雷霆之手段,一举压服乱众。杀了邢自古,军卒无首,自然无法生乱,其后本郡自会使人详细追查原委。此事难道做的错了吗?”“卑职此时已是无话可说,只求大人能够亲至军营一趟,听听家兄是如何一个说法!”
“够了!”任破胡一声断喝,声音中已经带出无法遏制的怒意。“本郡之意已决,你也不要再多生事端了。本郡体念你心系兄长,今日之事便不再追究了。此刻骠骑将军在此,你若在蓄意纠缠,可别怪本郡翻脸无情!”“大人!”邢而道语带哭腔,凄然道:“您怎么不想,那苏武苏县守赴任不过数月,如何便与家兄阴相结交,甚至生出反意?如此清平天下,岂不是自寻死路,这世间哪有这样的道理!”
“什么?!”霍去病长身立起,身子一晃险些栽出车外。苏武!他怎么跑到黎县来了?而且莫名其妙的蒙祸在身,被人盖上了一顶谋反的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