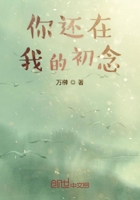一
颠倒,是常会发生的事情,不足为奇。
昨天的真理,今天的谬误,往日的毒草,如今的香花,这种经过一段时间沉淀以后,所作出的重新判断,我们称之为还历史本来的面目。
但这也不容易,事后说起来总是轻巧的,可过程本身,却决不轻松。有时候,明明白白知道那是错的,可由于这样和那样的原因,你得认为那是“对”的,这当然很糟糕,但我们大家差不多都领教过。当其时也,也许你的良知,使你不甘随大流说违心的话,做违心的事,但你决不会,也不敢逆错误潮流而动,铮铮而言,掷地有声,说那是鹿,而不是马。拍案而起的勇敢者不是没有,但为数一定很少。于是,沉默的大多数唯有等待一途,人们会抱着这样一个信念,哪怕要等好多好多年,哪怕已经盖棺论定,板上钉钉,总会有那么一天,该颠倒的,终究要颠倒过来的。
这大概就是人类的长处了,也是与动物的区别所在。否则,人类失去了这份自我完善的能力,这世界也许早就沉沦,也无进化可言了。
但也不是所有的颠倒,都应该颠倒过来,那些不该颠倒的颠倒,譬如,就人而言,人鬼颠倒,人妖颠倒;就事而言,是非颠倒,黑白颠倒,如果也颠倒过来的话,就要弄得老百姓莫知所从了。近年来,鲁迅先生忽然被狗血喷头,周作人忽然被香火供奉,就是文坛上的一份最大的颠倒。最初,实行者还有些“犹抱琵琶半遮面”,迩来,则明火执仗,为周作人鸣冤叫屈,至于粪土鲁迅,则成一股甚嚣尘上的风气。
任何一个具有正常思维能力的人,对周氏兄弟,一个大大缩水,一文不名;一个金身重塑,供奉庙堂的现象,都会匪夷所思的。一个贬值掉价,一个行情飚升,斗士被辱骂,汉奸最光荣,这世界究竟怎么啦也真是令人嗟叹世情之诡薄,人心之险恶。对于最起码的公正或公道的认知,度量衡竟能失准到这样差劲的程度,也不知道这个社会吃错了什么药最近,我读了一篇《且看骂鲁迅的狂人》的文章,给我一点启发。此文刊于1999年1月29日的《羊城晚报》的《书趣》版,作者署名为闵良臣。他在文章中这样写道:“1998年11月20日南京某报登出头条新闻,其中就有几位所谓‘天才’的狂人,对鲁迅口出狂言,大放厥词。这个说:‘鲁迅是块老石头……他的反动性也不证自明。对于今天的写作而言鲁迅也确无教育意义。’那个说:‘我们根本不看老一辈的作品,他们到我们这里已经死亡。’”
在这篇文章里,作者用郁达夫《怀鲁迅》的一句话,来回敬那些发表高见的勇士,实在是意味深长的。“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如果将郁达夫这番话,反其意而用之,那就是:一个出汉奸,出许多汉奸的民族,说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大约是不会错的。而出了汉奸,还要加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假如是这样的话,以此类推,说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也不算为过。
闵先生的文章中还写道:“有人说:‘鲁迅小说绝对比不上郁达夫,他的杂文谁都可以写……’更有人说:‘鲁迅在文学上的成就与他的地位不相称。他的大多数作品一般作家都能达到。以鲁迅来衡量文学,标准太低,影响了中国文学的发展。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鲁迅早已是个过去的话题。’”
看到这里,我不禁想起十年“文革”期间,郭沫若先生一时兴起,写的一部享“誉”华夏,风行神州的《李白与杜甫》了。当时,他之所以要把诗仙与诗圣拉到一块来比,不遗余力地推崇李白,百般揄扬,想尽办法地埋汰杜甫,奚落备至,说白了,那是专为一位特定读者而写,具有强烈的政治目的。但如今把郁达夫的小说评为A+,而将鲁迅的小说评为B-的勇士,该不至于抱有郭老的宏图大志,有投桃报李之盼吧?
所以,我想,这样的比法,恐怕更接近于上海弄堂里的顽童,并排站着,比赛谁尿得更高更远的游戏心理作怪,和小孩子人来疯的表演欲吧那么,这些“骂鲁迅的狂人”,愤世嫉俗的同时,某种程度上还保存一份童真未泯的率直和可爱呢!
把郁达夫和鲁迅拉在一起比小说的长短,就如同要将福克纳和普鲁斯特,定出上下,把茨威格和川端康成,分出高低一样,是徒劳无功的事。大师与大师之间,是没有可比度的,因为每一位大师,都是历史上的唯一,也就是黑格尔说的“这一个”。如果硬是要比,那就是明初陶宗仪在《南村辍耕录》里所说的,“庸人孺子,见画必看,妄加雌黄品藻,本不识物,乱订真伪,令人气短”了。
我的写作间,约五个平方大小,很奢侈地拥有一扇朝西的窗子,可以感受下午三四点钟的阳光,这对我垂暮的年龄来说,倒也十分吻合。窗对面为另栋楼高耸的山墙,其间为一不通行的夹道,每当学校放学以后,就会有一些小朋友,来这里玩耍。玩累了就坐下来叽叽喳喳,时常听他们夸耀自己的家庭成员:“我妈是处长!”“我爸是局长!”“我哥是团长!”“我姐是空中小姐!”到底谁高谁低,小孩子们经常争得不可开交。偶尔,我也推开窗,参加他们的讨论。说实在的,局长和处长,或许能比,而解放军的一位团级干部,与一位飞洛杉矶的空姐,我也说不上来谁大谁小。
想起窗外孩子气的争论,倒也觉得“骂鲁迅的狂人”,顶多是意气用事罢了,年轻人的叛逆行为,或许应该加以理解;而那些变着法儿想为汉奸正名者,才真正令人齿冷,在光天化日之下,作不该颠倒的颠倒,恕我说句不敬的话,就怕有为鬼作伥之嫌了。
人来疯,是病,又不是病。你说它是病,就是病;你说它不是病,也就不是病,因为人来疯死不了人。但人来疯现在愈来愈成人化,一些老爷们,老娘们,还是有头有脸的,也人来疯。而且沾上就有瘾。
一位医生朋友对我讲,人来疯,属于医学上定名为“儿童多动综合症(MBD)”的一种症状。多动症,通常发生在三岁到六七岁的儿童身上,主要表现为病儿活动过多,不能休止,甚至不择时间、场合、跳蹦闹乱,总处于躁动不宁,心神激奋的状态之中。100%的病儿,注意力很难集中15分钟以上,情绪起伏不定,行为鲜能自律。因此,所作所为,事前既不加思考,更不顾后果,具有很大的冲动性。由于不能自控,加之精神亢奋,所以,在群体中往往不能依秩序活动。
但愿,也是属于一种人来疯的表演行为。
二
其实,那是儿童成长期间才有的心理失控现象。
“需要治疗吗”我请教医生。
“如果仅仅是人来疯的话,倒也用不着,长大以后,不药而愈,这种现象就自行消失了。”
我们称之为人来疯的孩子,就是当家里来了客人以后,环境有所改变时,所表现出来的那种情不自禁的,超过一般活泼、活跃程度,近乎张狂的兴奋状态。譬如,跑来做个鬼脸啊,在门外发出怪声啊,乱跳乱蹦故意撞倒什么啊,跟头把式做出各式可笑动作啊,这种神经质的表演,其实,目的只有一个,是要引起来客对他的注意,使屋子里的人意识到他的存在。
而成年人的人来疯现象,则是社会公共关系日趋表面化,竞争化,商品化的结果,尤其对一些表现欲强的人士,即或上了年纪,七老八十,到了人多的场合,有时,也很人来疯的,捏捏小姑娘的脸蛋啦,说些语惊四座的疯话啦,在饭桌上点着牌子要酒啦,告别时死死握住小姐的手不放啦……也是很想引起在场人士对他注意的。
这也是古已有之的。最近,读《且介亭杂文》对不起,恐怕要让先进们讪笑了,还在看这些“早已是个过去的话题”的鲁迅作品,其中有一篇记他买了一部禁书《小学大全》的文章,讲了一个清代人来疯的故事,挺有意思。
故事的主人公叫尹嘉铨,是位道学先生,讲《朱子集注》,极负盛名,官做得也不小,大理寺卿,相当于最高法院,或司法部的长官,熬到这个位置上,也就可以了。人就是这样:没有钱的时候,物质欲望特别强烈;有了钱以后,权力欲望就会上升;而在官瘾、钱瘾都满足以后,求名的欲望就会浓厚得可怕。
没名者求名若渴,有名者求名更热,名小者求得大名,名大者与人比名,名不怕多,就怕不名,名上加名,最好是举世闻名。按说,一个人当上了皇帝,譬如杨广,应该是得到了名欲的最大满足吧不,他对大臣杨素说,我的骈体文,四六句,也是满朝第一,当仁不让的。由此看来,名是一个无底洞,永远也填不满的。
小孩子人来疯,希望大人注意他,恐怕是初级阶段的求名。所以,成年人的人来疯,或颠三倒四,装疯卖傻;或出出洋相,唱唱反调;或怪叫两声,仰天大吼;或故作谬论,语出惊人,都是为了求名,自己炒作自己,而企图引起别人的注意。这是一点也不必大惊小怪的,至少在文坛,大家早就司空见惯的了。
尹嘉铨已经离休回到老家河北博野,做一名体面的乡绅了。论理,享他老太爷的清福吧!不,他不大甘于寂寞,因为“名”这个东西,如同海洛因,染上了就没救,一生一世也摆脱不了,乃至死了以后,墓志铭怎么写,都是要斟酌再三的。所以,尹老先生想出来向乾隆为他父亲请谥,就是名欲才弄得不安分起来的。时下,我们看到,作品是放在头条,还是放在二条,是得正式奖,还是提名奖;评级为一级二级,还是一级半,或二点五级;在悼词里,是“坚强的”,还是“坚定的”;是“久经考验的”,还是“忠诚的”,一个个都会寸土必争,寸步不让地讨价还价,争得面红耳赤的。看来,这是“名”之酷爱者的古今同好了。
鲁迅先生写道:“乾隆四十六年,他已经致仕回家了,但真所谓‘及其老也,戒之在得’罢,虽然欲得的乃是‘名’,也还是一样的招了大祸。”
“戒之在得”,说来容易,做到却难。近年来,文坛上有那么几个人,说写得不那么太坏,可以,但绝说不上写得很好。能力有大小,才华有高低,这本也无碍,谁也没规定凡写,必传世,必不朽,方算。但这些人常常“功夫在诗外”,非要在书斋外面奔走竞逐,非要跑到脚后跟不落地,谋一个什么头衔。好像有了这顶桂冠,立刻那作品像镀了层金似的,就能洛阳纸贵了。其实,作家水准如何,学养怎样,能吃几碗干饭,是个什么量级,一天看不清楚,两天弄不明白,天长日久,总也八九不离十吧。
即使封为作家之王,作家之帝,又如何,能改变他们先前说不定是草包的实质吧墙上芦苇,山间竹笋,毛泽东早就嘲笑过的,但笑者自笑,捞者照捞,他们偏要顶这尊桂冠,赢这份虚名。有时不禁替他们设想,深夜扪心,会不生出“所为何来”的感叹吗但这等人,永远感觉良好,或者永远感觉麻木,用热水烫烫那肿胀的脚后跟,第二天继续追名逐利,绝不嫌累的。
由此也可资证尹嘉铨为名所诱,为名所驱,竟敢做出令乾隆爷都大为光火的事,也就不奇怪了。
公元1781年4月,乾隆西巡五台山驻跸保定时,在籍致仕的这位前大理寺卿,按捺不住他的人来疯了。当然,这样的接驾盛典,他这个侍候过乾隆的大臣,怎么能缺席呢他像热锅上的蚂蚁,向北眺望,会不会从大路上飞来一匹快马,奉圣旨,传召老臣尹嘉铨入觐。他后来才明白,保定府、直隶省的现任官员,才不愿意他老人家出现,而分去一份圣眷皇恩呢!这也是所有冀图固宠的臣下,希望皇帝的眼睛只看到他一个人的自私心理。这位道学先生,站在路口,左望不来,右望不到,真是心急如焚啊!
人来疯,是一种容易成瘾的病。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作家也上了报纸的娱乐新闻版,在报屁股上,男女文人与歌星、影星挤在一起,频频出镜,常常亮相,成为大众传媒的主角,就是因为瘾在驱动着。有的作家,天下何人不识君,已经相当知名了,还嫌不足,还要与党羽们,三日一新闻,五日一消息地炒作。因为,人来疯成瘾之后,最怕偃旗息鼓,最怕鸦雀无声。如果说,作家怕传媒冷淡,那么乾隆爷到了离博野几十公里的保定,竟不召见尹嘉铨,他为之痛苦欲绝,再正常不过了。
博野在蠡县、安国之间,离保定府,要是开桑塔纳,也就几十分钟的路程,照老先生退下来的三品官,享受二品的离休待遇,肯定地方政府会给这位京官,配官轿或马车的。要不,他自己去一趟,尽一分老臣护驾之心,人家不会用乱棍将他打将出来;要不,他就现实主义,死心塌地在家待着,只当没有发生这回事,也就人来疯不了。四月份,雨前毛尖也该上市了,泡杯新茶,与夫人、小妾调调情,也是怪不错的养生之道嘛。
那就去吧,步行到保定,早发也就夕至了呀!但道学先生,自然难免知识分子那种又自尊,又自卑,既想吃,又怕烫,进一步,退两步,前怕狼,后怕虎的两面性。去吧,怕人家把他这过气的官僚,不放在眼里。主席台,上不去;贵宾席,没位置,只能跪得远远的,用望远镜才能看到圣上。不去吧,这就意味着他真成了在野之人,林下之民,拉架的黄瓜,实质上的无名之辈了,这绝对是他受不了的。
可他做不到,瘾烧得他坐立不安。
名,是原动力;人来疯,是外在形态。
名,不得;人来疯,不成,尹嘉铨那把老骨头,一夜在炕上折翻烙。
三
医生说,多动症者具有很大的冲动性,通常事前不加思考,至于后果根本想也不想的。
尹嘉铨终于灵机一动,想出了为他老爹尹会一添光加彩的主意,一是请谥,二是从祀,皇上恩准下来,孝子当上了,风头也出尽了。想到这里,高兴得直搓手。天色露曙,让下人赶紧为大少爷备马,火速前去保定府,向乾隆皇帝呈上这份两全其美的奏折。谁知好梦破灭,招致杀身之祸,押赴刑场,也就是如今的宣外菜市口,才后悔这一回的人来疯,顽得太过分了。
成年人的人来疯,就不能像小孩子那样没头脑了,得看场合,看地点,看对象。有一次文学聚会,一位前辈对一位穿着无袖衫的女作家,作出关切的样子:“这屋里空调开得太大,你不会感到凉吗”一面伸出老手,抚摸那支半老徐娘的丰腴臂膀,一面做出很心疼的样子:“哦,都冻得冰凉冰凉的了!”这显然不够庄重的举止,也只有他倚老卖老的人来疯做得出。不过,要是这一支胳臂,长在乾隆皇帝的哪位宠妃或者公主身上,这位前辈若也是十八世纪的一位文人,敢这样放肆么借给他老人家胆子,也不会冒失行事的。
“天子呼来不上船”,是李白的人来疯;“吹皱一池春水,干卿底事”,是冯延巳的人来疯。这两位敢于跟皇帝逗逗闷子,都是有先决条件的,是吃准了皇帝在那一刻心情不坏,胃口很好,血压正常,精神不错。问题在于尹嘉铨退居乡闾,已是闲云野鹤,肯定信息闭塞,孤陋寡闻。他不可能安装一个锅,接受卫星电视,了解北京紫禁城的政治动向。而学问太大太多的人,也有其弊病,就是容易囿于己见,自成一尊,视他说为异端,拒绝接受外界新鲜事物,陷入自我封闭的心狱之中,就会非常的自以为是了。
所以,他不知道,即使知道,也不会当回事,乾隆在第五次南巡前,已经处理了已故江苏东台举人徐述夔的诗狱,这是一件很大的案子,涉及了许多人,还有很重要的高层人士。他在北京还有公馆,能看到邸报,也会有人通风报信,但他忙于讨小老婆,竟疏忽了。
凡文字狱,都是先有小人举报,之后才有皇帝震怒,下令严办,然后才有杀一儆百,人头落地,这次也不例外。在徐述夔的《一柱楼诗》集中,发现了“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大明天子重相见,且把壶儿搁半边”犯禁诗句,以其影射讥刺,于是,将徐述夔及其子怀祖,从棺材里拖出来戮尸,将其孙食田论斩砍头;失察的江苏布政使陶易,列名校对之徐首发等俱押往斩监候,用现代的话说,也就是死缓罪吧。
最关键的一笔,也是尹嘉铨无论如何不能掉以轻心的,是对礼部尚书,江南大才子沈德潜的处理。算起来,这位已故的尚书,是声望不让其父尹会一的朝廷同僚,尹会一是道学家,沈德潜是诗人兼诗评家。所以,尹会一在金銮殿,跪得离乾隆很远,沈德潜则不同,文而优则仕,是乾隆十分赏识亲自擢拔的首席御用文人,经常蒙召到内廷与很爱写诗的皇帝,谈论诸如唐诗宋词,李白杜甫之类话题,很神气一时的。
此公生前曾为这部诗集的作者写了篇传记,估计,也是情不可却,请名人作序作传,也是一种风气;估计,沈大学士,倚老卖老,人来疯一回,纵使我过格一点,官家又能奈我何但什么“明朝”,“大明天子”,“壶胡儿”,都是触动异族主子痛处的敏感话题,乾隆可就不念旧交了。勃然大怒,下令将御赐碑推倒,磨毁碑文,并将他的牌位撤出乡贤祠,死了也不能拉倒,一定要将他搞臭。尹嘉铨如果不是名欲缠心,人来疯瘾发,应该从三年前发生的这次文字狱吸取教训。乾隆对于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以为自己是李白,是冯延巳,经常性地人来疯,妄自尊大,不安分,是相当反感的。要是再弄一帮学子,簇拥着自己,俨然一代文宗,以名儒自居,就更不可恕了。
鲁迅分析道:“清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以为‘太平盛世’之累。”要是尹老夫子明白这一点,就在家老实呆着,不该派儿子到保定去给自己找不太平。没办法,人来疯拱得他无法安生,于是,眼看着儿子快马加鞭去保定,自己在家里坐等佳音。他不会不知道上一朝宋濂的教训,这第一步棋,就走了臭招。他要亲自去叩求,也许下场不至这样惨。
宋濂,曾是朱元璋很倚重的文学顾问,但年事已高,难免应对上有些差池,于是,恩宠日衰。他试着提出要求,能否回家养老,以为朱皇帝会挽留他,谁知大笔一批,就同意了。甚至连返聘或任个什么协会的闲职,也不安排。宋濂很失落,于是在离开朝廷的那天,当着众大臣,在金銮殿上耍人来疯,说他实在好想念好想念陛下的,能不能准许他每年上朝叩见龙颜一次,朱元璋笑着也就答应了,这自然也是好风光的事情。
第一年,他去拜谒了;第二年,他又去拜谒了;第三年,他发现去了这两年,明白朱元璋不会再有什么恩典给他,便撒了个谎,说有足疾,不良于行,把儿子派去代他拜谒。他哪知朱元璋是中国所有皇帝中,不是最小人,也是相当小人的一个,立刻打发手下的特务去暗访,回来向他报告,说宋老夫子不但健步如飞,连跳迪斯科都不成问题。于是,一纸命令,将宋濂发配,后来,死在充军途中。伴君如伴虎,跟皇帝办事,是要格外小心谨慎。尹嘉铨不但不以史为鉴,而且根本不当回事,好像乾隆是他老同学,到了保定,打发儿子去看看一样。大概,从古至今,凡儒必腐,学问大了,人情世故就差,加之文化人一得意,就膨胀,给梯子,就上脸,尹嘉铨把自己看成香饽饽,以为皇上多么买他的账呢!
乾隆看到他儿子替他送上来的奏本,为父请谥,当即恼了。这时肯定有潜台词的:“你是什么东西,竟不自己来,派你儿子来,如此将朕不放在眼里,简直混账之极!”遂提起朱笔,批上:“与谥乃国家定典,岂可妄求此奏本当交部治罪,念汝为父私情,姑免之。若再不安分家居,汝罪不可逭矣!”话说到这样严厉,要是平头百姓,吓也吓死了。但儿童多动症(MBD)的症状之一,患者常常是不依秩序行事的,接着又送上一本,请求皇上恩准他父亲从祀文庙。鲁迅说:“这一回可真出了大岔子”。乾隆火冒三丈:“竟大肆狂吠,不可恕矣!”
在封建社会里,九五之尊说不可恕,他的脑袋还保得住么?
大学士三宝奉命主审这件案子,此人手法,与几百年后的红卫兵批斗走资派采取的策略,大致相同,先从生活问题,男女关系入手。弄一串破鞋挂在脖子上,逼他自己骂自己大破鞋,西门庆,同性恋,鸡奸犯。所谓批倒批臭,只要在臭字上大做文章,将其批臭之后,不倒也歪了。
三宝对这位道学先生最具杀伤力的攻击手段,就是纠劾他强娶烈女为妾的道德败坏一事。跪在堂下的尹嘉铨,一边掌自己的嘴,一边说自己寡廉鲜耻,欺世盗名,假道学,伪君子。三堂审讯以后,定为“相应请旨将尹嘉铨照大逆律凌迟处死”。何谓“凌迟”就是行刑的刽子手,要对人犯一刀一刀剐三千次后令其气绝,那可是中国最残忍的刑法。
从康、雍、乾三朝,满族统治者,迭兴文字大狱,血也流得够多的了,杀鸡给猴子看,阻吓作用也已起到了,除个别文人如尹嘉铨者,大多数也都把尾巴夹得很紧。乾隆便不让他受凌迟之罪,改为处绞立决,恩准他一次痛快地死亡。他就为他的人来疯,付出了最终的代价。
写到这里,真为今天的人来疯们庆幸,要是早托生几个世纪,在有皇帝的日子里,怕就得不到这份快活和自在了。
所以,也就难怪,街上流行人来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