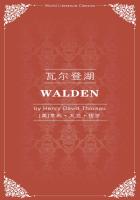清末小说中女性形象的建构,在女性现代化的意义上,有多层面的反映。
首先,梁启超为新小说搭建的新民框架,为新女性确立了一个和国家主义理想相符合的形象,这样的新女性就是所谓的女国民。但当时维新人士的女学观着眼点在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上,而不是在女性自身的解放上。这种理想女性按照梁启超的说法是“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妇道即昌,千室良善”,其实和封建的“三从四德”标准相去不远。更明确地说,女性首先被要求以母亲的身份行使教育职责,来承担对国家的义务,因此,她常常又被直接称为“国民之母”。对此,一些更为激进的人士撰文维护“女国民”所应有的权利和义务。这些权利包括受教育权、工作权、社交权、政治权等。在清末小说中可以看到对各类女权的阐释、想象和参差的实现。
由于清末维新派以废缠足、兴女学为振兴女界的切入点,所以,女国民形象首先以争女性教育权为重,出现了一批以兴女学为主题的小说;但最具冲击力和创新性的女国民形象,或许首推以民族革命事业为己任的一系列女豪杰。兴女学基本以男性为主导,其中的理想女性属贤妻良母型,她们既接受男性的指导,也和男性形成合作关系。这些女性从社会阶层来说,属于中上层社会,因此,实际上只涉及很少一部分女性。而在女豪杰小说中,女性自主型占到多数,虽然这些小说作者也多为男性,并且以男性为模仿对象,但不少小说把争女权和反抗男性联系在一起。这部分女性涉及各个阶层,不少女性带有底层女性的豪放甚至粗俗泼悍的气质。而民族革命的高尚目标,成功地改造了传统文学中的这种泼妇气,使它成为女性的一种积极气质,对于建构现代女性的双性同体气质有着开拓性意义。虽然这部分小说多为想象之作,但却因向底层的深入,而把大多数女性包含进去,最终在20世纪文学中,成功地成为现代女性形象的主流。而兴女学小说虽然在当时有着更多的现实意义,却因为其精英色彩而显得曲高和寡,并且同样带有相当的意识超前的想象特点。相比较,豪放的女国民小说更带有女性乌托邦色彩,往往以建立女性独立王国为追求。
清末小说作家面对的更大多数女性,是需要“启蒙”的旧女性,这就难怪和女性相关的写作,更多偏于谴责。除了带着旧眼光无端指责女性红颜祸水的厌女症,一些新派人士对旧女性的批评也带有前所未有的严厉。即使如梁启超,他也把当时的女性定义为分利者,把女性抚育子女如此重要的生产力,和女性承担繁重的家务劳动,完全排除在社会总体的生产关系之外。分利者无异于寄生虫,女性被看做对社会毫无贡献、坐享男性创造的财富的人。像梁启超这样有现代眼光的维新人士,对女性尚有如此浅薄的见解,社会大多数成员对女性的见解更成问题。因此清末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负面居多。其中对旧女性的着墨之处多落在迷信和缠足上,特别是常常把迷信和淫乱联系在一起,增强了道德批判的意义。而对缠足于女性的伤害,却很少有细致的刻画,多为口号式的呼吁。对旧女性的批判,其实也在为新的女性形象做推陈出新的工作。在谴责的缝隙,我们也可以找到一般女性社会境遇改变的种种线索: 女德准则的松动,女性社交面的拓展,对爱情婚姻自主的渐趋肯定,女性由家庭向社会职业发展的可能,家庭地位和经济状况的改变,通过破迷信引起对科学知识的关注等,使女性开始了由外在形象到内在气质的改变。
从文学的表现力来说,性资源一直是最重要的传统文学资源。这个领域也是最能体现传统知识分子优越感的领域。才子佳人、红袖添香、夫唱妇随,这种性爱想象题材,都是传统小说热衷描写的对象。但从晚明开始,近代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士大夫的优越感越来越面临危机。虽然商人还没有全面提升自己的地位,但重农轻商、重士大夫轻生意人的情况已经有所改变。最明显的是,当时的妓女不再视读书人为自己的保护人和理想客人,渐对商人更为青睐。晚清对废八股废科举的呼吁声浪,更动摇了读书人的自信。胡适说,清末社会小说家“大都是失意的文人,在穷困之中,借骂人为糊口的方法”。文人在晚清的末路状况,改变了他们之前相对女性高高在上的关系,在开始鄙薄他们的女性面前,他们失意“骂人”,对她们越来越不顺服的出格行为讥诮讽刺,但其实他们对女性又暗暗有了一种天涯同命人的认同感,对女权的倡导其实也寄托了他们提升自身价值的潜在愿望。
悖论的是,小说作者谴责的对象并不限于旧女性,新女性成为他们更为激烈的谴责对象。新女性是20世纪初小说中最纠结的女性形象,她既被要求符合西方文明进步的标准,又不能被西方的自由放浪所腐蚀;她既要清除身上传统的落后习俗,和不问国事只会“分利”的旧形象决裂,又要保持传统娴雅贞静的贤妻良母形象。新女性成了不得不“新”、又不能太“新”、终于不知道怎么“新”的大困惑。女性左右为难,社会也横竖不能接受,致使“新女性”竟在一般的使用中成为一个贬义词。这部分特指的“新女性”,一直延续出现在民初小说中,在她们身上集中了清末民初社会对女性解放认识的焦虑。她们是一般小说作者批判的对象,特别被从行为放浪,尤其是在恋爱婚姻上过于自由去表现。民初对她们的另一种称呼是“自由女”。这些新女性常常被排除在争取女权的积极形象之外,成为女权运动中的反面典型,她们被看做和当时狭邪小说中的妓女是同一类放诞的女性。而实际上,她们成为清末最为典型的自我奋斗、疏离男性的女权形象。
这些新女性不同于女国民们以天下忧乐为先,她们首先解放的是自己。她们对于清末女权主张不啻是一个重要的补充。对于女国民来说,国民身份要求她们将获得的权力和利益用来为国家服务,其实部分剥夺了她们获得的个人权力。这种约束明显地表现在梁启超等维新思想家提出的合群思想中。梁启超在《新民说》中明确表示:“本论以后各子目,殆皆可以利群二字为纲以一贯之者也。”随后,他对国家和个人关系做了进一步的阐释:“盖无群无国,则吾性命财产无所托,智慧能力无所附,而此身将不可以一日立于天地。故报群报国之义务,有血气者所同具也。苟放弃此责任者,无论其私德上为善人为恶人,而皆为群与国之蟊贼。”可见,梁启超以“利群”作为最高行为准则,认为个人应该无条件地服从国家利益,为此做出牺牲也是合理的。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他对晚清张扬的自由思想,也作了修正:“自由云者,团体之自由,非个人之自由也。野蛮时代个人之自由胜,而团体之自由亡。文明时代团体之自由强而个人之自由灭。”陈天华的《警世钟》也发挥了这种为群体牺牲个人的思想:“泰西的大儒有两句格言:‘牺牲个人(指把一个人的利益不要)以为社会(指为公众谋利益);牺牲现在(指把现在的眷恋丢了)以为将来(指替后人造福)。’这两句话,我愿意大家常常讽诵。”
而新女性却相反,她们要个人解放,要个人自由。清末小说中的“新女性”主要是女学生,在她们身上,有着现代女性的独立性、职业意识、个人自主性等。她们是这一时期小说中最富有生气的女性形象,比新政治想象出来的理想女性更具有现实性。虽然她们同样是清末女权思潮的产物,但常常被归入19世纪中期开始发展的狭邪小说中的妓女一类放诞的女性。她们被称为“新女性”的潜台词是: 和妓女一样放荡。新女性也因此彰显了清末小说中另一大群体——妓女群体在性别解放上的意义。
狭邪小说是19世纪小说自由发展出现的一个突出的类型,在清末小说中占据了相当的比重。狭邪小说的风行不是偶然的,清代道咸以后,官吏狎妓邀游,成为风气。洋商买办,更把妓院当作谈生意会朋友的地方。而妓女交接的理想客人,从传统的文人变为富商和买办,正是海禁开放的结果。加之咸丰以后,禁律弛废,小说写狎妓之事也就更加明目张胆了。这类小说是清末小说创作中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和创作潮流。新小说并没有终结狭邪小说的繁盛,相反,狭邪小说较之前在单篇的篇幅上和总的数量上反有惊人增长,晚清最后十年形成了中国文学绝无仅有的一个大规模描写欢场生活的时期。
狭邪小说对表现性别关系的才子佳人传统模式有了很大的突破。虽然同样以性爱关系为连接,但狭邪小说却没有多少真情实意,两性之间的关系主要靠金钱维系,表面的感情分合,由内在的利益冲突决定。在这些小说中,女性和传统小说中的佳人截然不同。传统的佳人面目一律如画,感情一律专一,但缺乏自己的思想和主张,而清末小说中的妓女往往被写成工于心计,用情不专,行为放荡。而其实,晚清狭邪小说中的妓女,不但是近代最早的职业女性群体,也是最早一批为争取自己独立的经济权利、恋爱婚姻权利而奋斗的女性。但她们特殊的职业身份,遮蔽了她们的努力。她们的积极行动,在晚清小说中常常是被作者用贬低的方式来反映的。
狭邪小说最后被清末的写情小说“洗白”。由于政治小说的贫弱,1906年前后,新小说退潮,写情小说取而代之,并在清末民初形成鸳鸯蝴蝶派小说的盛行。1906年吴趼人出版小说《恨海》时,开始倡导一种不以政治和革命为写作诉求的“写情小说”。在《恨海》之后,出现了一系列和狭邪小说写男女之情难脱渊源又有所不同的言情小说,如《禽海石》、《劫余灰》、《泪珠缘》、《新茶花》、《双花记》、《鸳鸯碑》等。清末写情小说以及之后的鸳蝴小说的盛行,都和清末狭邪小说的异常繁盛有关,所不同的是,写情小说和鸳蝴小说以良家妇女替代妓女获得了社会的接受,而且用保守的妇德获得了公众的认可,从而以“纯洁”遮掩了两者的相关性。写情小说的商业化运作,决定了它对读者取迎合态度,淡化了狭邪小说中包含的对社会文化具有颠覆意义的女性个人意识。它以妥协和退步为代价,赢得了商业成功,带来了鸳蝴小说的繁荣。
鸳蝴小说不但以女性为重要的书写对象,而且也把文学引向如女性一样的远离政治中心的地位。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鸳蝴小说时期或许是文学离政治最远、离商业最近的一个时期。它开启了都市通俗文学的传统,比“五四”文学走向乡村的民间,更早地就走向了都市的民间。因此,它虽然是多方面妥协的结果,但在通俗化和商业化方面,是一种创造性的发展,它形成了现代文学的一个重要支流,这或许是鸳蝴小说最重要的意义所在。但就性别话语而言,鸳蝴小说不但抹杀了晚清女权的很多进步因素,而且以单一替代了丰富。它能够透露出的晚清女权的积极信号,或许集中在对于女性恋爱婚姻自由的肯定这一点上,这是鸳蝴小说对女权本土化最成功之处,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女权实际可以接受的程度。除此之外,鸳蝴小说对于性别的狭隘想象是令人失望的。因此,晚清尚不成熟的性别意识和性别话语,只能遗憾地被鸳蝴小说暂时终结。鸳蝴小说为晚清文学收束,决定了晚清文学的女性话语发展是不完整的,并没有完成它的现代转型。我认为,20世纪初清末文学的女性想象,只是现代女性想象的过渡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