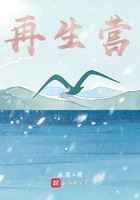太宗孝文皇帝前十三年(公元前167年)
初,秦时祝官有祝,即有灾祥,辄移过于下。夏,诏曰:“盖闻天道,祸自怨起而福由德兴,百官之非,宜由朕躬。今祝之官移过于下,以彰吾之不德,朕甚弗取。其除之!”
齐太仓令淳于意有罪,当刑,诏狱逮系长安。其少女缇萦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虽后欲改过自新,其道无由也。妾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
天子怜悲其意,五月,诏曰:“《诗》曰:‘恺弟君子,民之父母。’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无由至,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轻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具为令!”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奏请定律曰:“诸当髡者为城旦、舂;当黥髡者钳为城旦、舂;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止者笞五百;当斩右止及杀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赇(qiú)、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而复有笞罪者皆弃市。罪人狱已决为城旦、舂者,各有岁数以免。”制曰:“可。”是时,上既躬修玄默,而将相皆旧功臣,少文多质。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畜积岁增,户口浸息。风流笃厚,禁罔疏阔,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错之风焉。
六月,诏曰:“农,天下之本,务莫大焉。今勤身从事而有租税之赋,是为本末者无以异也,其于劝农之道未备。其除田之租税。”
“天下有罪,罪在朕躬。”这是后世的皇帝哥哥们经常说的一句大方话,是不是从这里开始,待考。
这是一般的规律:最高层做的见不得人的事,都是在后世才揭开厚厚的黑幕,把真相公之于众。秦帝国的编制里,有一个岗位叫“祕祝”,他的职责就是把上天对皇帝的警示和惩罚转移到臣属身上。
这种嫁祸于人的勾当,原来以为只有长得像陈佩斯这样的奸诈之徒(陈佩斯在小品里的扮相)才会干的,没想到啊,长得像朱时茂这样的领导全国人民的皇帝也干这样的事。
面对权力不受制约的皇帝,大家也很着急,也想过一些办法,就是用天灾甚至天象来吓唬皇帝,日食、月食、台风、地震,都行,天子嘛,只有上天能管得了。这些说法不要说在科学尚未倡明的古代,就是在今天,我们着急了,尽管知道是无稽之谈,也愿意相信。
下有政策,上有对策,秦始皇找到一个办法,就是找一个专业人士,把这些个不祥的东东全部转移给别人,找若干下家替自己顶着。这一套只有帝王家才相传的秘密,一直传到汉文帝。文帝是个明白人,取消了这一套无聊的东西。
文帝既然不信这些灾异警告能够像癌细胞一样转移,那么,他对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的说法也就自有心得了。
这一年,有几件事,和今天有某种特殊的关联。
缇萦救父是流传千古的故事,属于大汉朝的“五个一工程”。
除去肉刑,不用说是仁政,但是文帝除去了肉刑,武帝可以随时恢复,我们亲爱的司马迁哥哥就被断了一肢,这种仁政人亡政息,我们只能表示有限度地欢迎,因为两千多年,我们这方面的进步那是相当慢的。
缇萦上书是典型的因案成例,因例成律,就是一个特别的案子变成典型的案子,并影响到法律的修订。现代社会的法律完善也是这样的,我们熟知的孙志刚案就是这样,死了一个孙志刚,因而修改了几十年的收容条例。
这一年,文帝彻底取消了农业税。前些时候,有些媒体宣传取消农业税的仁政时,不假思索地说,这是空前的,事实上,两千多年前,有个叫刘恒的领导人,也有这样的举措。要知道,那时的帝国主要靠农业租赋,现在我们每年四五万亿元的中央财政收入,免掉五百多亿的农业税,国家的承受力还是有的。
跨越历史看一些事情,我们会很着急,也会很踏实。着急什么?我们该做的,做得很少,很多事情,我们还没做。为什么踏实?有些事情,放在几千年的坐标下,三五十年,三五百年,也是一瞬,所以,对于一些无奈的事情,我们要有历史性的耐心,别着急,慢慢地等着沧海桑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