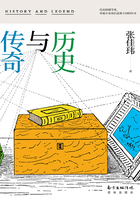苏联。
莫斯科郊外,祖巴洛沃别墅。
严寒结成的霜花写满玻璃窗,层层叠叠。苏共总书记斯大林坐在大写字台后面的一把转椅上,刚刚审阅完从秘书那儿送来的一堆公文。什么都得管。今天已经口授了多少电报,他自己也记不清了。虽然,渐渐地,这些工作都由助手、秘书和机关去办了。但是,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仍然喜欢亲自处理琐碎的问题,亲自决定一些人的命运。
斯大林在党和国家事务中的分量愈大,竭力依靠总书记个人指示来解决大量问题的人就越多。什么关于拖拉机手服兵役的问题,难道人民委员不能自己决定吗?而在首都要盖新大楼又怎样呢,就没有一位书记能过问一下?
不要说斯大林,大部分高级领导人都形成了这种习惯。
过几天,就要召开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在这次会上,要通过一个新的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尽管共产国际的官员一再声明,苏共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只占一票,事实是,真正获得国家政权的共产党组织只有苏联。于是,共产国际的意旨大多来自苏联,而苏联的意旨是由斯大林拍板的。
中共和苏共的有识之士已经清楚地看到,中国农村将发生普遍的农民暴动。据早期中共活动家蔡和森说,北伐之前,“我们只是在上海、广东和湖南对工人进行过充分的训练”。当蒋介石的军队攻入新的地区时,千百万农民从旧时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到了1927年春季,据蔡和森随后的估计,广东、湖北、湖南、江西及其他省份,组织起来的农民为数已不下1500万。
面对这场方兴未艾的风暴,共产国际的决策者们反而踌躇不前了。10月间,克里姆林宫曾电令中共领导人对农民加以约束,以免引起指挥北伐的国民党将领们的对抗,他们中间许多人显然都是地主出身。后来,在托洛茨基的攻击下,斯大林不得不承认发出这个指示是一个错误。
即使这样,在中国农村,打了胜仗的国民党军官对农会和工会的限制越来越多了。解放地区的政府,特别是江西省,也变得越来越保守了。对于江西地方上的许多共产党员担任地方行政长官一事,中共中央的看法是:“这些同志将失去同群众的联系,我们的党将不再为群众所信任。因此,这些共产党员必须辞职,或者退党。”
但是,这个指示刚一下达,莫斯科第七次全会就送来了新的通知,指示共产党员去参加政府,以与国民党分权……
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像一个要通过车辆疾驰的公路的孩子,不敢和身边的“大人”松开手,还要时时看着“大人”的眼睛。
而年长不了几岁也不十分成熟的“家长”,面对车水马龙的十字路口,也不免晕头转向,牵住“孩子”的手自然一阵紧似一阵……
还有一个情况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会议召开之际,苏联党内的分歧正愈来愈尖锐。七次全会前不久,苏共中央和苏共中央执委会联合会议决议给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和其他人以警告处分,并决定免除托洛茨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职务。关于中国问题的讨论,原是第七次扩大全会的主要议程,但也染上了宗派斗争的色彩。
11月初,当中国北路战事停顿期间,蒋介石的部队向东推进,于11月3日占领九江,11月9日占领南昌。当时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已经完成了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的准备工作。布勃诺夫、拉斯考尼科夫和维经斯基被委托起草《中国问题提纲初稿》。布勃诺夫在对中国进行短期访问后,回到莫斯科作了军事方面的情况介绍,并提议:为了利用国民党及其拥有土地的军官,借以掌握全中国的政权,共产党人必须支持北伐。这就意味着要不顾一切地防止土地革命。
斯大林看完布勃诺夫等人起草的提纲,放到大写字台上,便把转椅转向窗口,久久地、默默地凝视花园。总书记不喜欢密集的林木,每到春天,他都亲自指出哪些树应该锯掉。
总书记现在的这种姿态,意味着他要“锯掉”初稿这棵“树”。
是的,斯大林否定了布勃诺夫的提议。
斯大林和布哈林商议后,起草了一份截然相反的提纲。新提纲将重点放在土地革命的必要性上。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第一次会议,是在1926年11月22日由布哈林宣布开幕的。代表和来宾挤满了克里姆林宫的会议大厅,对布哈林的来到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他在开幕式以后宣告:我们特向坚持大规模革命解放斗争的伟大中国人民
致意,我们以整个共产国际和全世界工人阶级的名义保证,我们将不惜任何代价,千方百计、全力以赴地支持这一世界历史性的斗争。
在这次会议上作报告的,除了布哈林外,主要有谭平山、罗易和斯大林本人。
谭平山是代表中共来参加会议的。他是乘船至海参崴再转到莫斯科的。他和总顾问鲍罗廷的意见不同,他是鼓吹利用北伐,以达到在全中国展开土地革命这个主要目的的。但是到了莫斯科以后,他发现大多数干部都支持鲍罗廷打倒蒋介石、大规模重新分配土地的意见,而且都来说服他,他的观点也多少有些改变(奇怪的是,这两个人在第二年又都重新改变了观点)。
布哈林作为季诺维也夫的继承人,当了共产国际主席。他在发言中说到中共当时的主要错误在于对农民问题注意不够。他说,错误的主要倾向是过分地害怕农民运动的发展,并且对国民党占领地区实行土地改革的必要性坚持不够。
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委员的谭平山,在其随后的发言中,没有反驳布哈林的观点,只是做了一些解释:中国共产党在数量上和组织上都是薄弱的。过去一年中它的党员增加了五倍,但还没有来得及严密地组织起来,也未形成领导方面的紧密团结。同志们(特别是与农民问题有关的同志)大部分是没有经验和缺乏理论训练的。
他说的是实情。当时农民运动已在许多地方自发地开展起来,但大部分没有组织或缺乏有经验的领导。至今还没有明确的土地纲领和统一的口号,农民本身大都还在“封建制度的偏见和余孽”下面忍受痛苦。因此中国的农民情况是很复杂的。所以谭平山又说:为此,我们希望共产国际及其各部门在理论和实践经验方面给我们以巨大帮助。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才能不顾一切困难去解决复杂的中国问题。
至于中国共产党在农民问题上应取何种路线,谭平山顺从了共产国际的权威,他说,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完全赞同布哈林同志的观点:在反帝的民族革命运动中,发展中国的农民运动,维持各阶层的统一战线。
布哈林的这个论点也确定了谭平山关于“中国形势”报告的基调。
斯大林坐在一旁一声不吭,默默地叼着他那著名的与他同在的大烟斗。在那些日子里,如果有人向斯大林提到他所不知道的事情,他总是留意倾听,当他认为这个意见合理时,他会毫不含糊地立即采纳。可是,就在他酝酿措施之时,谭平山的话又将他拉入维谷。
“我们还有更大的难题。”谭平山说道,“自从去年7月间广州国民政府成立以来,它名义上是左派政府,实际上是右派掌权。”他又带几分矛盾的语气说:但是党的权力(即国民党的权力),是在左派团体手中,他们和共产党人共同控制了十分之九的国民党地方组织。共产党的任务是加强左派,打击右派,孤立中间派(指蒋介石)并将其推向左派。这一切都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因为中国革命迫切需要一个民族革命统一战线,需要一个包括全国人民中反对帝国主义者和封建残余的一切革命阶层的统一战线。在这里,又使中国共产党人面临基本上是进退两难的境地。我们必须维护农民的利益,但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维持和巩固民族革命运动的统一战线。在如此矛盾的情况下,要坚持一种正确的策略方针是非常不容易的。共产党从统一战线撤出来,就意味着它的分裂。所以,共产党人必须竭尽全力进一步发展国民党,并借助国民党来继续进行国民革命……
有趣和重要的是,谭平山在阐述中国革命的两种前途时,与布哈林不同。他认为:或者是中国无产阶级在世界无产阶级的支援下成功地把民族革命进行到底;或者是中国新资产阶级把中国革命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通过帝国主义的援助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并通过妥协手段慢慢地消灭中国革命。谭在这里还提到了周恩来一直认为是最危险的家伙的“戴季陶主义”和“中山舰事件”。他说这两件事是资产阶级企图从无产阶级手中夺走革命领导权的尝试。
谭平山的这种预测,后来全都应验了。
可是七次全会对此并未引起注意。在讨论谭的报告时没有人考虑到这种可能性:国民党领导集团中的资产阶级,特别是蒋介石会不会由于北伐的“辉煌”而利令智昏。大会只集中在中国共产党在农民问题和土地问题上的错误,尤其集中在中国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的问题上。
彼得罗夫慷慨激昂:同志们,遗憾的是,这一个完全错误的建议(指要求退出国民党)在我们苏联共产党内也得到了同情和反响。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十分有害的投降主义的观点,一种失败主义的思想,是必须加以清除的!企图夺取中国资产阶级领导权的右翼正在努力与帝国主义达成谅解,与共产党公开破裂。如果中共听从俄国反对党的建议,退出国民党,就会使国民党右翼有恃无恐。所以,保持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在当时中国革命历史发展阶段中是绝对必要的。
台尔曼的语气则平缓得多:我们对中国问题,有一部分感到新鲜有趣,但整个问题又非常复杂,因此我们在那里行动时要特别谨慎。说到这里,台尔曼举了一个不十分明白的例子。那意思还是说,如果不能充分利用国民党,说明我们怀疑或不相信共产党自己的力量。
国民党代表邵力子也列席了会议,他在表示国民党“在共产党和共产国际领导下一定会完成自己的历史任务”后,这个日后被称为“和平老人”的“小矮人”,竟说出一句震撼大人物的重要的话,这句话为斯大林所引用,后来又为毛泽东所接受。邵力子说:“我们坚决相信,没有武装便没有革命的胜利,中国的形势特别证明了这条经验。”
斯大林磕空他的烟斗,装上一撮烟丝。这时一个更大的声音将他震了一下。
罗易发言。与众不同的是,他首先针对美国:“美国力图在自由主义的、人道的帝国主义标签下,偷偷地侵入中国,以取代残忍贪婪的老帝国主义。这就是说,美国想要用‘仁慈’来扼杀中国,而不是用炸弹和机关枪。我们知道,对于这种‘朋友’必须多加小心!……目前阶段的中国革命,首先应该是一场农民革命。要没收大地主的财产,这个问题不能回避。它必须明确地提出来,并作出肯定或者否定的回答。”
在斯大林听来,罗易仿佛一个愤怒诗人在作诗。学生时代斯大林也写过诗,投身革命之后他抛弃了诗。但是他20年前的那首小诗《早晨》却上了格鲁吉亚小学生的课本。他总觉得诗让人温柔,革命更需要哲学、政治经济学,尤其是军事学。所以,他特别欣赏邵力子那句话。在罗易发言后,斯大林向全会作了报告,提出了一个日后为人们所熟知的论断:“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他解释说:在中国工农争取解放的斗争中,革命军队是一个极重要的因素,对这些军队估计过低,是提纲初稿的一个不可容许的缺点。由此可见,中国共产党人应当特别注意军队工作,将军队改造成为中国革命思想的真正的和模范的体现者。此外,中国革命者,包括共产党人在内,应当着手深入研究军事。
他说,不应当把军事看做次要的事情,因为军事现在在中国是中国革命极重要的因素。中国革命者,其中包括共产党人,应当学好军事,以便逐渐前进并在革命军队中担任某些领导职务。要使中国革命军队循着正确路径向目的前进,其保证就在这里。不这样做,军队中的动摇和犹豫就会不可避免。
他再次强调要通过革命军队来影响农民。“我已经讲过革命军队在中国革命中的极重要的意义。中国革命军队是这样的一种力量,它第一个打进新的省份,它第一个深入农民群众,农民首先凭它来判断新政权,判断新政权质量的好坏。农民对新政权、对国民党和对整个中国革命的态度,首先是看革命军队的行为,看它对农民和地主的态度,看它帮助农民的决心而定的。”
斯大林的结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支持国民党和武汉政府的同时,应当采取一切办法使军队中反农民的分子不发生坏影响,保持军队的革命精神,并做到使军队帮助农民,唤起农民参加革命。
不管斯大林后来犯有多少种错误,以及当时发出过多少条不切中国实际的指示,仅就斯大林的那一句名言而论,却不失为政治伟人的高瞻远瞩。有幸听到斯大林这一指示的中共高层领导,哪一位心中也不会不腾起一篷火焰!
以后的南昌起义,及稍后的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等,不能不说与斯大林的这句名言有关。每一次起义,每一簇火种,都是一次枪炮的宣言啊!
在这次会上,斯大林仍然要中国共产党用全力去支持国民党和蒋介石掌握的国民革命军。
1926年11月22日,在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的第一次会议上,作为印度共产党代表的罗易被选入共产国际主席团和中国委员会。于是,全会闭幕后几个星期之内,罗易作为共产国际一个新的代表团团长,动身前往武汉。蒋介石和中国共产党之间不断增长的冲突,是问题的实质所在。然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对这个新来的共产国际代表并无好感,他自然就和鲍罗廷更加接近起来……这是几个月后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