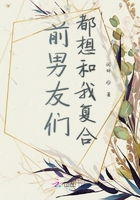在国内,将自己的儿子蒋经国送去苏联学习的蒋介石已大权在握。在他的心目中,共产党人是书呆子,苏俄顾问不过是黄头发、蓝眼睛的小小谋士而已。然而,他暂时还离不开这些共产党人和蓝眼睛黄头发的顾问们。北伐开始的时候,他是既自信又不自信,时时祈祷上苍:保佑北伐节节胜利,以便走上权力的最终顶峰。
国民革命军要在1926年7月9日誓师北伐的消息传出后,黄埔军校门庭若市。蒋介石和国民党方面都把这个誓师典礼视为开天辟地以来的第一个隆重典礼。当时湖南的战事很吃紧,赵恒惕、吴佩孚联军南下,唐生智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连战皆败,丢了长沙,败退到湘南各县待援,请国民政府派兵增援的电报如雪片飞来,乞援的使节,络绎不绝。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蒋介石慢腾腾地不发一兵,不输一弹,聚精会神地选择黄道吉日,筹备举行誓师典礼。
电话铃急促地响了起来。蒋介石站起来,慢吞吞地拿起话筒。
打电话的是唐生智的代表刘文岛。他已找过蒋介石几次了,但都被蒋介石借口“团结力量”、“巩固后方”、“筹措军饷”为由,拒绝了增援,急得如热锅上蚂蚁一般。
“蒋总司令……湖南危在旦夕,请你及早派兵……”
蒋介石平静地回答:“誓师是个大典,汤武革命,莫不誓师,没有誓师就动兵员那是轻举妄动。再就湖南战事说,也应该给唐孟潇(生智)一个锻炼的机会,兵法说置之死地而后生,湖南的局势还没有那样严重。”
刘文岛抑住了怒气问道:“誓师典礼,可否提前举行?”
“誓师典礼是关系全局,不能因为湖南一个局部的情况有所改变。”
刘文岛无奈,悻悻放下电话。
蒋介石在留声机上放了一张京剧唱片,摇足了弦,坐在椅子上,边听边想着心事。
事实上,他迟迟不发兵援湘,主要是他派到奉天与张作霖勾结的代表,同张作霖还没达成谅解;派到南京与孙传芳勾结的代表,还在讨价还价中。他也深知唐生智是一个自命不凡,野心很大的人,如果不使其几经危难,折去锋芒,将来不好驾驭。至于誓师典礼,蒋介石也确视为树立威信,巩固权力必不可少的象征。
留声机的弦跑完了,《空城计》的拖腔变得牛嚎一般。陈洁如闻声出来关了唱机。
蒋介石闭上了眼睛。陈洁如以为他睡了,诧异地抚摩着自己的肚子,斜眼向蒋介石瞥了一下,不断地微笑着。她小心翼翼地不让她漂亮的皮拖鞋发出声音来,一面把两手伸到身后,一步一步地向她的丈夫走去。她那因怀孕而丰满的胸脯,在绸缎的衬衣下面高高地耸起,胸脯上面是一串绿宝石一般的项圈。蒋介石拉过她的手抚摩着,呢喃着说:
“不知是生男还是生女……”
陈洁如得意洋洋地弯下腰,很快在蒋介石额头吻了一下。但她立刻吃惊地向后一退,因为蒋介石怒冲冲地跳了起来。
“这是办公室,你怎么能……”
陈洁如望一望门口的卫士,羞愧难当地逃回卧室去了。
蒋介石整整胸前的衣服,用手绢的一角小心地揩净嘴唇。他召来侍从秘书问:
“监誓和授印仪节的人考虑好没有?”
秘书回答:“拟请国民党中央主席张静江、代理国民政府主席谭延分别担任。”
“这样不够隆重。”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秘书。他以为谭延不过是北洋政府的一个督军,他属下的一个军长;张静江虽说是结拜兄长,他既无功业,又无学问,不过是一个富翁而已。他要选择一个地位很高,名声很大,相当于孙中山那样而又不会与他自己有权力地位之争的人。
秘书笑笑,心想这样的人哪有?
“有!”蒋介石喊道,薄薄的嘴唇和威严的下颚动了动。“不得已而思其次。让吴稚晖来!”
吴稚晖自被北京政府通缉以后,一直蛰居上海,以写作为生。他是同盟会的老同志,是孙中山的朋友,在北大教书多年,学术地位与蔡元培、陈独秀齐名。也算是门生满天下,又是国民党的监察委员,名声清廉,而且发誓不做官的。蒋介石决定请他来广东担任监督与授印的角色。
7月9日上午10时,正是烈日当空,热气熏人。广州北较场上搭了个很宽敞高大的将台,台上挂着金碧辉煌的装饰物和五颜六色的旗帜,坐着政府要人。台下站满了脖子上冒汗的士兵。
吴铁城拿着传声筒去担任司仪。
蒋介石身穿草绿色毛呢军服,手戴洁白的细纱手套,全副武装,腰配短剑,还佩上长指挥刀。蒋介石宣誓后,从容地站在一旁,等待着。吴稚晖缓步走过来,把一个红绸布包着的锡印放在蒋介石手中,向他点点头,又握了握手,队伍里爆发出一阵欢呼声。
誓师那天,广州各界五万多人像潮水一样涌向东较场。从主席台望去,旌旗翻动,人呼马啸,煞是壮观。蒋介石故意等誓师队伍都到齐了,才坐着小汽车驾到,登上高高的誓师台,向群众讲话:
“今天,是国民革命军举行誓师典礼的纪念,亦是本总司令就职的日子。本总司令自觉才力绵薄,为中国国民革命的前途负如此重大的责任,惶恐万分。但现在北洋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已来重重包围我们、压迫我们了,如果国民革命的势力不集中统一起来,一定不能冲破此种包围,解除此种压迫。所以本总司令不敢推辞重大的责任,只有竭尽个人的天职,担负起来,以生命交给党,交给国民政府,交给国民革命军各位将士。自矢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蒋介石慷慨激昂,可惜广东群众不懂他的话,只好由邓演达帮他翻译。
誓师大会以后,国民党中央党部举行了一个欢送会。主席致词以后,由总司令讲话。接着由妇女部长何香凝说话。她站起来,劈头一句就说:“革命者不成功便成仁。”座中文武官员都凝视着她。“廖先生成仁了,他是为着革命成仁了,……”说到这里,她泪流满面,泣不成声,全场肃然。
几个躲在角落里的右派人物开始掩着嘴,窃窃私语道:“瞧,廖夫人有会必演讲,演讲必讲廖仲恺,讲廖仲恺必哭,哭必喝汽水……
坐在何香凝旁边的邓演达,招呼她坐下。
晚上,总政治部的几位同志在邓演达家里碰头,谈到何香凝的痛哭和这次的北伐。
恽代英也来了。他听了右派编派的取笑何香凝的顺口溜,喃喃道:“廖先生和蒋校长是共同创办黄埔军校的,为黄埔立下了政治教育的规模,造就了许多革命的青年军人,遗留了革命军人必须与农工阶级亲密合作的教训。廖先生是为了这而遭人妒忌的,他为了这死于反革命派的手中。”
邓演达也感叹道:“廖先生经营黄埔军校,苦心孤诣,任劳任怨,后来受到右派的攻击,并且遇刺身殉。这自然是革命的巨大损失,而党内也失去了把舵的人。许多超越常规的恶劣事件连续发生。现在提出北伐,可以使党内的意见集中到这一点上。今天廖夫人的痛哭,是有深长的意义和难言的隐痛的。”
坐在一旁的郭沫若注意地听着他们的谈话,一种敬意油然而生。许多年过去了,恽代英那质朴机敏、短小精悍的风度,带着破嗓子的有力量的声音;邓演达那血气方刚、经验丰富、思维缜密而迅速,一说话好叉腰,斜着肩膀、梗着脖子的样子,都深深地印在他的心上。
“沫若同志,”邓演达一声唤,把沉思的郭沫若惊回现实。“为了你的工作方便,在宣传科长的职务之外,再给你一个行营秘书长的头衔,再破格设一位副科长来辅佐你。”
郭沫若点头称是,心里明白:这是他怕我嫌官卑职小和经验不够。其实在我自己,实在是一个冒险的高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