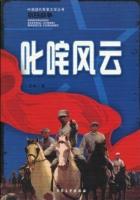人们抬起了担架。伤者还能使出气力说道:
“不,不,腰板更硬的人也照样会被彻底折断的……那些老顽固,像布拉和鲍兑,还不肯屈服,这我是知道的;可是我们,我们年轻,我们要承认新事物的发展走向!……不,高日昂,你看着吧,这是一个时代的结束。”
人们把他抬走了。罗比诺太太因为终于能够摆脱了让她烦扰不安的生意,在一种几近快乐的冲动里拥抱了黛妮丝。等到高日昂陪着年轻姑娘退出来,他向她坦白地说,罗比诺这个可怜的家伙说的话是有道理的。再要同妇女乐园斗争便是白痴。他感觉到,如果他再不服输,他便没有指望了。昨天晚上,他已经跟那正准备去里昂市的雨丹秘密地交谈过一次了。可是他认为不见得有希望,显然他已经很清楚黛妮丝的权势,所以他试图打动她。
“说实话!”他又说,“制造商倒霉也是活该的!当那鲁莽的汉子们相竟用最便宜的价钱从事制造的时候,如果我还因为别人的利益作斗争搞得自己破了产,大家都要嘲笑我了……天哪!正如你从前说过的,制造商只能用一种更良好的组织和新的方法追随前进的步伐。一切都已成定局,一句话就够了,满意的是群众。”
黛妮丝微笑了。她答道:
“你亲自跟慕雷去谈吧……你去看他,他会很高兴的,只要你能每一米提供一生丁的利益给他,他便不会对你有任何怨恨。”
在正月的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鲍兑太太停止了呼吸。半个月以来,她已经不能下楼看店了,交给一个做日工的女人去照看。她坐在她的床铺中间,用枕头支着腰。在她那苍白的面孔上,只有两只眼睛还有生气;她竖着脑袋,透过窗户的小窗帘,固执地看向对面的妇女乐园。鲍兑本人也受着这种折磨——这种绝望的目光凝视着的痛苦,有时他要把窗帘拉下来。然而她作出哀求的手势拦住他,她固执地要看,要一直看到她咽下最后一口气。现在那个大怪物把她的一切都夺走,她的店,她的女儿;她自己正在一点一点地随老埃尔勃夫一同消逝,她的生命的丧失是跟这个店丧失它的主顾是同步;在这个店完结的那一天,她也就不再呼吸了。当她觉得自己快死的时候,她还有力气强求她的丈夫把两个窗户打开。天气温和,一束快乐的阳光照耀着乐园,可是这个老房子的寝室却在黑暗里打冷战。鲍兑太太瞪着眼睛不动,那种巨大的胜利,那些明朗的玻璃,在玻璃里面有上百万的金钱在流转,让她满怀幻象。她那一双眼睛渐渐变得黯然无光了,被暗影包围住,当这双眼消失在死亡里的时候,依旧张得大大的,始终在注视,涌着热泪。
附近所有破了产的小商家又一次排队送葬。人们可以看见王普义兄弟,他们被十二月份的到期票据弄得脸色惨白,他们用了最大的努力算是付了款,可是他们再也经不起下一次了。贝多雷兄妹,支着一根手杖,那么忧心忡忡,导致他的胃病恶化了。戴里尼埃中风了,皮奥和李瓦尔默默地走着,鼻子朝着地面,绝望透顶。而且人们不敢互相询问那些消失了的人——奎内特、塔丹小姐以及其他,他们从早到晚被淹没在灾难的洪流里,一个接一个地被消灭了;更不要谈那断了腿躺在床上的罗比诺。但是人们露出最感兴趣的神情用手指着那些刚卷入这场灾难的商人们:香水商戈洛涅,女帽商沙德易太太,花商拉卡沙纽和鞋商脑德,他们仍旧屹立不倒,可是已深深陷入的将被依次被清除的忧虑中。在灵柩车的后面,鲍兑迈着像他护送他的女儿时同样的得宰的牛的脚步;同时在第一辆送葬车里可以看得见布拉的浓密眉毛下闪闪发光的眼睛和白雪一般的头发。
黛妮丝陷于极大的痛苦中。半个月以来,她被忧虑和疲劳累坏了。她必须送北北进学校,而且要为日昂去奔走,他是那么热恋着糕饼商的侄女,请求他的姐姐去求婚。其次就是这场重复的灾难——她的伯母的去世,这要把这个年轻的姑娘压垮了。慕雷又一次让她如愿:她为她的伯父和别的人要怎样做就怎样做。一天早晨,她听说布拉已被丢到马路上去而鲍兑也要歇业了,她又同他谈了一次。然后,在吃过早餐以后,她走出来,希望至少能够为这两个人做点什么。
在米肖狄埃街上,布拉站立着,面对着他的店杵在人行道上,昨天人们导演了一手漂亮的恶作剧——这是诉讼代理人下的功夫,把他从他的店里赶了出来:由于慕雷持有一些债权,他轻易地得到了阳伞商人破产的证据,于是由破产管理人来出卖,他用五百法郎买了租赁权。因此这个顽固的老人把他曾以十万法郎都不肯放弃的东西让人家用五百法郎夺走了。而且带着一伙拆毁工人来的工程师,为了要把他弄到门外去。都请了警官来。货物被出卖了,家具被搬走了;而他顽强地呆在他睡觉的那个角落里,人们出于最后的怜悯心,不敢赶他出去。拆毁工人甚至在他的头顶上敲打着屋顶。人们抽掉了石板,天花板崩落了,墙壁吱吱歪歪地响,可是他在这赤裸的老空架子下面,在这些残迹中间,仍然不肯离去。最后,警察到了,他才出去了。然而在他到附近的一家公寓里待了一夜以后,第二天一清早,他又出现在对面的人行道上。
“布拉先生,”黛妮丝温和地说。
他听不见,他那双火焰似的眼睛吞噬着那些拆毁工人,他们正在用鹤嘴锄砸那间小破屋的门面。现在通过那些空洞的窗口,可以看得见里面了,看得见那几间破屋子和黑暗的楼梯,那里已经有两百年没有阳光了。
“啊!是你呀,”最后他答话了,这时他认出她来了。“是吧?他们演了一出好戏,这伙强盗!”
她不敢再谈下去,她被的老住处的这种让人心痛的悲惨景象所感动,连她自己的眼睛都离不开那向下落的霉臭的石块了。在上面,在她的老房间的天花板的一角下,她还看得见那用歪歪扭扭的黑字写成的名字:用蜡烛火焰熏成的埃尔奈斯丁;于是她的心里又回想起那些悲惨时光,满怀对于一切痛苦的人们的怜悯。可是那些工人为了要一下子拉倒那面墙,正想从根基上把它挖倒。墙在摇摆了。
“如果能够把一切都毁掉啊!”布拉发出咆哮似的声音叽咕着。
人们听见了一声可怕的震动。那些工人惊慌地逃到街上来。在倒落的时候,这面墙摇摆着把一切残迹都卷走了。毫无疑问,这间小破屋在雨浸和龟裂之下已经支撑不住了:只要一推就足以使它裂开。这让人感到伤心崩溃,这间被血水浸坏的泥房子就这样被削平了。连一块壁板也不再竖立着了,地上只剩下了一堆垃圾,一堆落在街边上的过去的污垢。
“天哪!”那个老人喊叫了,仿佛是这一打击震响在他的内心里。他张着大嘴停立着,他绝没有想到会这么快结束。他注视着打开的切口,在妇女乐园的侧背上终于成了真空,那成为它的耻辱的污点被拆除了。这个小蚊虫被压垮了,这是对无限小的让人心烦的顽固一次最后的胜利,整个一圈房屋被侵占了,被征服了。过路的人聚集拢来,扯开嗓门同拆毁工人聊天,那些工人正在对这些非常危险的老建筑大发脾气。
“布拉先生,”黛妮丝试图领他到一边去,这样反复说,“你知道他们不会不管你的。你的所有要求都可以得到满足……”
他昂起了头。
“我没有要求……是他们派你来的吧?好啊!你去告诉他们,布拉老头子还知道怎样劳动,他到哪里都能找到工作……真的!给被他们所屠杀的人一点小恩惠,这真太舒服啦!”
于是她向他哀求。
“我求你,接受吧,不要让我这么烦忧。”
但是他摇动着他那毛茸茸的脑袋。
“不,不,结束了,再见吧……幸福地生活吧,你现在年轻,别妨害老人带着自己的主张去死掉。”
他向那堆垃圾最后瞥了一眼,然后他手酸地走了。她在人行道的拥挤人群中间,跟在他的背后。背影从盖容广场的角上转过去,一切都完了。
黛妮丝两眼茫然一动不动地停留了一会儿。最后,她走进她伯父的店子。布商一个人在老埃尔勃夫的幽暗的小店里。管家的女人只有早晚才来,作点厨房的事和帮助上下门板。他在常常的寂寞中处消磨时间,常常整天都没有人来光顾,每当极偶然有一个顾客走来时,他慌慌张张地也找不到所要的货物。在沉默中,在微光里,他就这样不停地踱来踱去,他保持着他在两次送葬时的沉重脚步,被一种真正被迫前进的症状所影响,仿佛他要将他的哀伤催眠并使它酣睡。
“伯父,您好些了吗?”黛妮丝问道。
他只停了一秒钟,便又走起来,从账桌走向朦胧的屋角。
“是的,是的,我很好……谢谢。”
她想找一个安慰人的话题,找一些快乐的谈话,可是找不到。
“您听到那声响吗?那房子倒下来啦。”
“唉!这是真的,”他惊诧而喃喃地说,“一定就是那座房子……我觉得地面震动了……今天早晨,我从屋顶上望见了,我就关上了门。”
他作了一个漠然的手势,表示他不再关心这些事情。他每一次走到账桌前,都要看一看那张空凳子,他的妻子和女儿就在这张坐破了的丝绒凳子上长大的。于是当他那永不停息的脚步把他运到另一头的时候,他注视着淹没在黑暗里的那些架子,架子上有几段布已经发霉了。这里成了一个孤寡的店家,他所爱的人已经去了,他的生意差得不能再差了,只有他一个人在数次灾难中,带着他那颗死去的心和被打倒的自尊心徘徊着。他向黑暗的天花板扬起眼睛来,他聆听着从小餐室的阴影里传来的静默,这个家的一角,就连它闷人的气味,从前都是他喜欢的。这个老房子里只有一种声息了。他那整齐而滞重的脚步让几面旧墙壁发出了回声,仿佛他在他心爱的人们的坟墓上行走一样。
最后,黛妮丝提及她原本要谈的问题。
“伯伯,您不能这样下去。必须做一个决定才行。”
他边走边答。
“当然,可是你让我怎么办呢?我曾经努力把货卖出去,可是没人来买……天哪!总有一天我将关了店门,然后就走出去了。”
她知道这次破产已经没有什么可怕的了。在这样的顽强的命运之前,债权人也会有所体谅。一切都已经付光了,她的伯父只需要简单地走向马路上去就行了。
“可是今后你要做什么呢?”她喃喃说,她想委婉地提到她不敢表明的建议。
“我不知道,”他回答。“随便人家让我做什么吧。”
他改变了路线,从餐室走向店头的橱窗;现在他每一次都用阴郁的眼神注视着那摆着被遗忘的陈列品的令人伤心的橱窗。他甚至不抬眼看看妇女乐园的胜利的门面,那一长排的建筑看不到边,从左到右占据了一条街的两端。这是一种彻底的被打败,他再没有力气发怒了。
“伯伯,听我说,”黛妮丝非常为难地终于说,“或许有一个位置给您……”
她又顿了顿,结结巴巴地说:
“是的,他们派我来向您提出一个稽查的位置。”
“在哪儿?”鲍兑问道。
“天哪!在那边,在对面……在我们的店里……六千法郎,一件不轻松的工作。”
猛然间,他停下脚步之后在她的面前。然而,他并不像她所害怕的那样愤怒起来,却是面色变得惨白,他已经被一种伤痛的情绪和辛酸的忍让压服了。
“在对面,在对面,”他嘀嘀咕咕地反复了好几次。“你要我到对面去吗?”
黛妮丝也被这种感动了。她又看见了这两个店家的长期斗争,她曾经一起给日内威芙和鲍兑太太送葬,她亲眼目睹老埃尔勃夫的倒闭,被妇女乐园掐死在地上。而叫她的伯父到对面去,戴着白色领带来回地走,这个主意弄得她也怜悯且反感起来。
“你看,黛妮丝,我的女儿,这可能吗?”他简单地说,同时他搓着他那颤抖的可怜的双手。
“不,不,伯父!”在她那公正善良的生命的跳跃中她喊起来。“这是不应该的……原谅我,我请求您。”
他重新徘徊起来,他的脚步重新搅动了这个店家坟墓般的空虚。当她离开他的时候,他在巨大的绝望中顽强地,来回地走,永远在走,这种运转是自发转动的,可是绝对不能够走出去。
那天夜里,黛妮丝又失眠了。她深深地感到无能为力。
即便替自己的亲人帮点忙,她都得不到一种安慰。她完完全全地必须帮助人生的不可战胜的工作,这种工作需要有死亡作为它不断向前的种子。她不再奋斗了,她接受了这种斗争的法则;然而她那女性的灵魂,想到苦难的人类,就有满怀眼泪的慈悲心和友爱的柔情。几年以来她自己被卷入这个机器的来回运转里。她没有在里边流过血吗?人们没有伤害她、驱逐她、用侮辱来折磨她吗?就算在今天,当她觉得自己被这种合理正当的事业所选中的时候,她有时还是惊恐的。为什么要选中她呢,她那么弱小?为什么她那迟钝的小手猛然间在这个大怪物的运转中会那么举足轻重呢?这扫除了一切的力量,也会依次消灭了她,她的到来就像是为了复仇。慕雷曾经发明了这个粉碎世界的机器,这机器的野蛮的运转使她愤慨;他在附近撒下了毁灭的种子,残害了一些人的生命;可是她正因为他的工作的伟大而爱他,每当他的权力恣意地发挥一次,她就愈加爱他,尽管在被征服者的可怕的悲惨面前她涌出了满脸的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