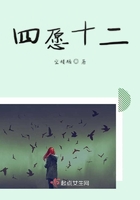这时附近一带的人都议论着将修的一条大马路,这条路将会叫十二月十日街,从新歌剧院一直通到交易所。征用的公文发下来了,两队拆房子的工人已经在两端打洞,一端在拆路易大帝街的旧旅馆,另一端在拆毁老通俗剧场的薄墙壁;人们听见尖嘴锄的声音逐渐逼近,沙奢街和米肖狄埃街都在为他们被规化了房子而兴奋不已。不出半个月,打的洞便将成为一个大隧道,充满了嘈杂声和阳光。
但是更使附近一带人激动的,是妇女乐园着手的事情。人们说它将大幅扩建,巨大的店面将占有米肖狄埃街,圣奥古斯丹新街和蒙西尼街的三个街面。传闻慕雷同不动产信托公司的总经理哈特曼男爵签下了合同,这一地带房屋所有权全归他,只除掉十二月个日街上未来的街面,男爵要在那里建造一座跟大旅社竞争的房子。乐园获得了所有的租借权,小店家关门,住户向外迁移;在一些空出来的房屋里面,大群的工人于一片灰尘之中开始新的翻造。在这场杂乱中间,只有老布拉的狭小的破店仍不愿拆迁,顽固地挂在布满泥水工人的高大墙壁中间。
第二天,当黛妮丝领着北北到她伯父鲍兑店里去的时候,正好有一排运砖瓦的垃圾车停在杜威雅尔老旅馆前拥堵交通。她的伯父站在他的小店门前神情悲伤地看着。妇女乐园的面积越是膨大,老埃尔勃夫就似乎越缩小了。年轻的姑娘感到橱窗愈加暗了,在低矮的夹层楼下压得更低了,与监狱的圆窗口相似;潮气使那旧的绿招牌愈加褪了颜色,窘迫的气氛将小店吞没,死气沉沉仿佛变得瘦小了。
“你们来了,”鲍兑说。“注意些!它们会从你们身子上压过去的。”
到了小店里,黛妮丝感觉到同样的紧张局促。她觉得它更阴暗了,愈加陷于衰败的睡眠状态里;空旷的角落形成黑暗的洞穴,柜台和架子上布满灰尘;同时一阵地下室的硝石气味从一捆捆人们常久不移动的布匹上发出来。鲍兑太太和日内威芙留在账桌边,纹丝不动,默不作声,仿佛是呆在没有人的空旷之中。母亲在缝抹布的边。女儿两手垂在膝上注视着她面前的空间。
“晚安,伯母,”黛妮丝说。“很高兴再次见到您,如果我曾经得罪了您,请别放在心上。”
鲍兑太太很感动地拥抱了她。
“我的可怜的女儿,”她答道,“若非另有心事,你会看见我更开心的。”
“晚安,堂姊,”黛妮丝又说,首先亲了日内威芙一下。
日内威芙如梦初醒。她也吻了黛妮丝,可是不知说什么好。两个女人随后抱起那伸出了小胳膊的北北。这一场和解就算完全了。
“好啦!都六点了,别走了,”鲍兑说。“为什么你不带日昂来?”
“可是他要来的,”黛妮丝很为难地喃喃说,“今天早晨我刚好看到他,他承诺会来的……啊!别等他吧,大概是他被东家执意留住了。”
她猜到也许有意外发生,所以预先替他声辩。
“那么,我们先开饭吧,”伯父又说。
然后他转过身子面向小店的阴暗的里面接着说:
“柯龙邦,一块来吃吧,不会有外人的。”
黛妮丝从未见过他。伯母向她解释说,他们不得已解雇了另一个售货员和那个姑娘。生意每况月下,柯龙邦一个人足够了;可是就连他也常常无所事事,常常打瞌睡,张着眼睛会睡觉。
尽管在漫长的夏日,餐室里却需靠煤气灯支撑。黛妮丝走进去的时候,两肩受了从墙壁上发出的冷气的侵袭,微微发抖。她又见到了那个圆圆的餐桌,漆布上摆着餐具,窗口有空气涌入,臭气哄哄的小院子狭道里射着光线。她看来,这些景物像是这家小店一样,显得愈加阴惨,如同在哭泣。
“爸爸,”日内威芙替黛妮丝觉得不舒服,“关上窗户好吗?这气味不大好。”
他感觉不到。他似乎很惊讶。
“你们要愿意,就随便吧,”他终于答话了。“只是我们没有空气了。”
果然人们觉得气闷了。这顿聚餐很是简单。喝过汤以后,正在使女端上了烂糊肉的时候,伯父照旧谈论对面的人家的事情。他起初表示非常宽大,允许他的侄女发表不同的意见。
“天哪!你尽管随便替这些专门骗人的大店家讲话吧……每个人意见不同,我的姑娘……人们缺德地把你赶出门来,倘若这仍考虑不了你们,那你就是有充分理由喜爱他们的;譬如说,即便你要再回去,也不阻拦……你们说是吧?在座的人也都如此吧。”
“啊!不,”鲍兑太太悄悄说。
黛妮丝像在罗比诺的店里谈话的情形一样,不紧不慢地陈述着理由;她谈了商业的论理的进化,现时代的需要,创造的可贵,最后谈到逐渐发展起来的大众的福利。鲍兑很是吃惊,撇着嘴,露出竭力去体会的神情,继续听着。等她把话说完,他摇了摇头。
“太不现实了。商业就是商业,它不外乎是这么回事……我承认他们赢了,可也不过如此罢了。我一直坚信就要倒闭了;是的,我是这么期望着,我耐心地等待着,你不会忘记吧?嘿!不是的,如今强盗像是走了红运,而正直的人们都很潦倒……事已到此,我不得不在事实面前低头。我认了,天哪!我低头了……”
他心里暗生怒气。他猛然间挥动着他的叉子。
“可是老埃尔勃夫一点不妥协!……你听着,我跟布拉讲过:
‘邻居呀,你要是退让了,你那些花花哨哨的东西是丢脸的哩。’”
“快吃吧,”鲍兑太太看见他这么怒气冲冲感到不安便插嘴说。
“等一下,我要让我的侄女彻底了解我的信条……我的女儿,你听着:我就像这个水瓶子,我绝不移动的。他们成功了,我自认倒霉!我呢,我抗议,就是如此!”
女仆端来了一块烤小牛肉。他双手颤动地切着肉;可是他眼神不好使了,他失掉了公平分配的权威。由于意识到他的失败,他不再拥有作为一个可尊敬的家主旧有的信念。北北以为他的伯父在生气:应该叫他安静一下,马上从他面前碟子上拿了一些甜点心和饼干递给他。于是他的伯父压低声音,想法转变一下话题。他谈了一下翻修马路的事情,他是赞成十二月十日街的,这次的辟路一定会带动这一带的商业繁盛起来。可是说到这里,话题回到妇女乐园上来了;所有的事情都使他又回到旧的话题,这成了一种病态的魔障。那里的人们已经成了泥人,自从运材料的车子堵塞了街道,他们就什么也卖不出去了。如此大的扩张,这真是滑稽;顾客们会迷了路的,为什么不索性改成大市场呢?尽管他的妻向他投射着恳求的目光,他也在克制着,他却从这个店家的业务上谈到它的营业数字了。这不是难以置信?不到四年,他们的营业数字竟增加了五倍:每年的收入,从前的收入每年八百万,而根据最后一次的报表,已经达到四千万了。所以这真是胡闹,这种事是史无前例的,跟这种东西是不能再斗争下去了。他们不断扩张,如今他们已经有一千个职工了以及有二十八个部门。这二十八个部门比什么都更使他气愤。当然有些部门是从原有的分出来的,可是也有些是完全新创办的:举例说吧,一个家具部,还有一个巴黎产品部。你们听得明白吗?巴黎产品部!真的,跟他们无道理可讲,他们最后还要卖鱼哩。黛妮丝的伯父虽然假装尊重她的意见,可是极力在劝她。
“干脆地说吧,你别想帮他们说话。我要是在我的布匹生意上加上卖锅的一部,你怎么想?是吧?你会说我发疯啦……你承认吧,至少你小瞧了他们。”
年轻的姑娘十分尴尬,知道说出有力的理由来也无济于事,只得含笑不答。他又说:
“总之,你是同他们一伙的。没必要说了,因为再闹翻也没有什么好处。看见我同我的一家人关系不和,这是我受不了的!……你愿意的话,你再回到他们那里去吧,可是别再将他们的事情传入我的耳朵里头使我心软!”
一阵沉默后。他素有的激烈情绪消退成烦闷的忍让。这间狭小的餐室,燃着煤气灯热烘烘的,人们感到窒息,使女只好重新把窗户打开;院子里潮湿的臭气以涌向饭桌。这时上了一道红烧土豆。人们慢慢地吃着,都沉默不语。
“瞧!你看看他们,”鲍兑拿着刀子指向日内威芙和柯龙邦又开始说。“你问问他们谁欣赏你们那个妇女乐园!”
柯龙邦和日内威芙每天两次要肩靠肩坐到这个照例的位置上从容地用餐,已有十二年了。他们一句话也不说。他呢,极力显出和善的神情,在他下垂的眼睑里似乎隐藏着那燃烧着他的内心的火焰;而她呢,在她那厚重的头发下面,头愈加抬不起来,她仿佛愁苦着心中的秘密,完全心灰意冷了。
“去年是大灾大难的一年,”伯父解释说。“我们不得不拖延他们的婚事……不,为了开开心,你问一下他们对于你的朋友们是怎么看的。”
黛妮丝为了令他高兴便这么做了。
“我不会的,我的堂妹,”日内威芙回答。“可是,你放心吧,并不是大家都这么认为。”
于是她注视着柯龙邦,他一脸茫然地搓着面包屑。当他感觉到年轻姑娘的眼睛落到他的身上,他便激动起来。
“一家肮脏的店!……无论哪一个,全是一群无赖!……所以他们才不愧是附近一带的虎列拉!”
“你听见他的话了吧!你听见了吧!”鲍兑兴奋地叫着。“这一个人是他们绝对拉拢不到的!……啊!你是独一无二的!”
但是日内威芙露出严峻而又痛苦的面容,注视着柯龙邦。她一直看透了他的内心,他感到不舒服,便更加倍地嘲骂着。鲍兑太太对着他们,不断注视着他们,沉默而又不安地像是预感到新的暴风雨就要来了。近来有相当长的时间,她的女儿的悲哀令她担忧,她感到她要死掉了。
“店里没人照管,”最后她离开餐桌说,她希望结束这样的情景。“你去吧,柯龙邦,我仿佛听见有人来。”
晚饭结束了,站起身来。鲍兑和柯龙邦去同一个中间人在谈话,那人是来取定货的。鲍兑太太领着北北去看画片。使女迅速地收拾了餐桌,黛妮丝靠近窗边发呆,注视着那个小院子,等她转过身来,她看见日内威芙仍未离开座位,直愣愣地看着餐桌的漆布,桌布刚刚用海绵洗刷过还是湿的。
“堂姐,你难受吗?”她问她。
年轻的姑娘并不答话,眼神凝固地在研究着桌布上的一条裂痕,仿佛她心里有无限缠绵的心结。然后她痛苦地抬起头来,注视着低头向她看的那副同情的面容。大家都离开了吗?她为何不起来呢?突然她抽咽起来,她的头垂在桌边上。泪水浸湿了她的衣袖。
“天哪!你怎么啦?”黛妮丝慌张地叫着。“需要别人帮忙吗?”
日内威芙神经质地抓住了她的手腕。她留住她,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不,不,不要走……啊!不要告诉母亲!……你知道,没什么事;可是别让别人知道,别告诉别人!……我跟你讲真话,我难以控制自己的情绪。我觉得自己非常孤独……等一下,我好起来啦,我不再哭了。”
可是阵阵的发作又袭来了,她打了几个大冷战,她单薄的身子随之而颤。好像是她那厚重的黑色头发把她的脖颈压得很低很低。当她的头在她交叉的手腕子上难过地滚动的时候,一支发针掉了,头发蓬散在她的脖子上,黑压压地包住了她。黛妮丝怕别人发现,悄声下气地试图安慰她。她解开她的衣服,看见她如此瘦削,悲痛得愣住了:这个可怜的姑娘,胸部像一个小孩子样深陷下去,像一个被贫血病啮噬的老处女那样一无所有了。黛妮丝双手捧起饱满的头发,这些漂亮的头发似乎吸干了身体的养分;然后为了叫她心情舒畅些,给她多点空气,便把头发结得紧一些。
“谢谢,你真善良,”日内威芙说。“我不胖,是吧?我从前没这么瘦弱,可是都完了……扣上我的衣服吧,妈妈会看见我的肩膀的。只要我能够,我就不让别人看到……天哪!我身体虚弱,我的身体真不好。”
可是她渐渐平静了。她疲惫地留在椅子上,眼睛竖盯住堂妹不放。沉默了一会儿以后她问道:
“你说真心话,他爱她吗?”
黛妮丝感到脸上有些发烫。她完全懂得她指的是柯龙邦和克拉哈。可是她故意问道。
“亲爱的,你说的是谁呀?”
日内威芙怀疑地摇了摇头。
“别装假啦,我求求你吧。帮我点忙,告诉我实情……你一定知道,我已经感觉到了。是的,你曾经是那个女人的朋友,而且我看见了柯龙邦追着你,跟你窃窃私语。他叫你向她传消息,对吗?……啊!行行好,跟我讲真话吧,我发誓,这样对我会有好处的。”
黛妮丝从来没感到如此为难。她在这个一向默默无闻而又窥察出一切的女孩子面前了眼睛。可是她仍然极力哄住她。
“可是他爱的是你呀!”
这时日内威芙显得很绝望。
“好啦,你什么都不肯透露……再说,这对我是一样的,我已经看见过他们了。他总是会跑到马路上去看她。而她呢,在楼上,笑的样子有些坏……毫无疑问他们在外头见过面了。”
“说到这个,可没有过,我对你发誓!”黛妮丝叫着,她为了至少要给她这点安慰,也顾不上她的身体了。
年轻的姑娘深呼吸一下。她有气无力地微笑了一下。然后发出稍为平复的软弱的声音说:
“我有点渴,想喝水……原谅我,我麻烦你啦。在那儿,在橱柜里。”
等到她接过了水瓶子,一饮而尽。她用一只手推开了黛妮丝,因为黛妮丝怕她这样喝法会对她有害的。
“不,不,别管我,我老是干渴……夜里也如此。”
重新是一阵静默。她又温柔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