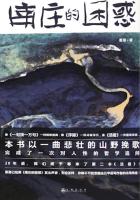“可是我没有做销售的资格呀,太太。”
“还可以做其它事情,小姐。各尽其能……去把东西叠起来。”
为了让来宾满意,人们必须把几个衣橱都翻腾出来,厅房的左右两边,在两排长长的橡木桌子上,摊出一大堆的大衣、皮上衣、圆肩衣,各式各样的衣服。黛妮丝并不响应,开始去整理,小心地折叠起来,再次分类,放在衣橱里。这是一些初来的人所作的下手活。她不再反抗了,她已经明白人们所要求的是顺从,她等待着主任批准她去卖东西,她觉得主任本来是有此意的。她一直在叠衣服,这时慕雷出现了。这搞得她神情慌张;她的脸羞红了,又感觉到她那奇怪的恐惧,她想他会来跟她讲话的。可是他似乎并没有注意她,这个小姑娘曾经在瞬间给他留下了好感,得到他的帮助,而现在他已经忘记她了。
“奥莱丽太太!”他爽快地招呼着。
他面色略现苍白,可是两眼炯炯有神。他查看了各部,发觉各部一个顾客都没有,在他那固执的对幸运的信心中,突然显示了失败的可能性。不错的,这时刚刚响过十一点钟,据经验所得,不到下午是不会有很多人来到。不过,有些征兆使他不安:在前几次大倾销的时候,早晨就有很多顾客了;其次,他也没有看见那些光着头的女人——附近一带的顾客,她们到他店里来就像去窜门。他像所有的大指挥官,虽然具有一个执行者惯有的顽强,而在实行作战的时刻,便有一种软弱的迷信捉牢了他。事情不大妙,他没了主张,可是他并知道这事怎么回事:他相信就在来来往往的一些女人的脸上都看出了他的失败。
此刻,一向都买些东西的布塔莱尔太太正要走开了,说着:
“不,你们没有我感兴趣的东西……我想想看,再决定吧。”
慕雷看着她走出去。等到奥莱丽太太听了他的招呼跑过来,他把她带到另外一边,两个人匆匆忙忙地谈了几句话。她流露着一副忧闷的神色,明显表示出她的销售情况不行。他们面对面站了一会儿,露出一种疑虑的神情,这种疑虑是一般将军们要对他们的士兵不表露的。接着,他拿出他那副雄赳赳的气派大声说:
“如果你们需要人手,就从生产车间调一位姑娘来……她总会用到的。”
他失望地去继续他的巡查。这一早晨他一直躲避着布尔当寇,这个人的长吁短叹令他气恼。他从生意差劲的内衣部里走出来,恰巧碰到布尔当寇,又只能忍受他那恐惧的表情。于是他毫不客气地教训了他一顿,在他不顺心的时刻就连他的高级职员也避免不了这种无礼行动的。
“躲开我,不要招惹我!一切都很好……总有一天我不会再雇用这些胆小的人。”
慕雷独自笔直地站在大厅楼梯口的边上。从那里他控制着整个店面,夹层的各部在他的四周,而且鸟瞰着底层的各部。在上面,那种空空洞洞的感觉似乎使他心痛:花边部里,有一位老太太没放过任何一个花边,可是却两手空空;同时,内衣部里,有三个无聊的女人挑选九十生丁一个的硬领,已经挑了很长时间了。下面,在有篷顶的走廊下,在从街道上射进来的光线里,他发现客人逐渐多了。一排人慢慢地走着,在各柜台前游览,几乎没有几个顾客;在零星杂货部和帽袜部,有一些穿紧身上衣的妇女正在挤来挤去;可是在麻布部和毛织品部就只有稀稀拉拉的几个人。店里的小伙计们,穿着绿色衣服,大铜钮扣闪闪发光,垂着手在等待顾客。不时有一个稽查员,态度庄重,白色领带把脖子系得笔直,走过去。大厅里一片死气沉沉的平静,没有任何东西比这更转紧缩着慕雷的心:阳光穿过磨光玻璃的门窗,从上面射下来,折射出一片含有白色尘埃的光辉,弥漫一片,像是悬在空中,在这下方,丝绸部就像在礼拜堂冷气袭人的静默中间沉沉欲睡。店员的脚步声,悄悄的谈话声,走过去的女裙的瑟瑟声,是寂静中仅有的点缀,这些声音闷在暖气设备的热气里。在此时,有几辆马车来到了:可以听得见马车紧急刹车的声音;然后,又听见砰地一声关上了车门。在店外面,远处传来了一片嘈杂声,有些好看热闹的人拥挤在橱窗前面,一些出租马车停放在盖容广场上,仿佛有人群光顾的景象。可是看见无事可做的收银员仰坐在收款的小窗口后面,看见打包的台子没有商品,上面摆着放绳子的盒子和蓝色的包装纸,慕雷虽然在气愤自己的胆怯,却坚信他的感觉那巨大的机器在他脚下不动了而且变得冰冷了。
“我说,法威埃,”雨丹悄悄地说,“你看看老板,在上头,……他好像十分沮丧的样子。”
“有这样的老板真的很不幸!”法威埃答道。“想想看吧,到目前为止,我还没卖过东西哩!”
两个人都在等待着顾客,彼此不看对方的简洁地讨论着。这一部里另外的售货员,在罗比诺的指挥下,正在叠起一段一段的“巴黎幸福”;同时布特蒙正在热心地与一位苗条的女士进行着谈判,像是小声地在接受一笔重要的订货。四周数排整齐的架子上,长条乳白色的包皮纸包着的丝绸,大把地叠起来好像大小不同的书本。柜台上满满地堆着各式奇妙的丝绸,有波纹绸、缎子和丝绒,似乎是用鲜花砌成的花坛,就像是丰收的漂亮且豪华的织物。这部很雅致,一间真正的客厅,商品是那么柔和,就像是豪华的室内装饰。
“下个星期我一定要挣到一百法郎,”雨丹又说。“如果我每天平均弄不到十二法郎,我就栽了跟头啦……我一直在期盼着,一次这样巨大的销售额的机会。”
“他妈的!一百法郎,不好办,”法威埃说。“我嘛,我只要五十到六十……你接待的那些太太非常有钱吧?”
“不是的,好朋友。你会想到么,这件事很让人郁闷的:我跟人打赌,赌输了……所以我要请五个人吃饭,两个男人,三个女人……靠!第一个走过来的女人,我就想办法叫她买二十米的‘巴黎幸福’!”
他们又谈了一会儿,谈第一天干的什么,谈这一个星期的计划。法威埃谈赛马,雨丹谈划船,谈给咖啡馆音乐厅的女歌手捧场。可是他们同样都是金钱的奴隶,除了金钱不想别的,他们从周一到周六拼命地挣钱,然后在星期天一起花光。在店里,他们无法摆脱的心事,就是无休止无情义的斗争。这时,圆滑的布特蒙已经把那个同他谈话的瘦女人——邵佛太太的使者——笼络好了!一笔好生意,总有二三十匹,因为这个着名的女裁缝通常有很大的需求量。在这时刻,罗比诺又想了个办法给法威埃搞到了一个顾客。
“啊!你看那个家伙,我们一定要和他做个规定,”雨丹正在策划抢占他的职位,利用最小的事件,便煽动这个柜台里的人来反对他。“主任和副主任应该作售货的事情吗!……大丈夫一言九鼎!我的朋友,要是我做了副主任,你们看我会怎样对待其他人。”
于是这个诺曼底肥胖可爱的小男人,便尽自已能力表示出善意的样子。法威埃不禁斜着眼瞟了他一下;可是这个肝火旺盛的男人却克制住了,仅冷冷地随意答道:
“是的,我知道……我是梦寐以求的。”
这时,正有一位太太走过来,他更加压住嗓门接着说:
“注意!生意上门啦。”
这位太太脸上长满雀斑,头戴一顶黄帽子,身穿一件红衣服。雨丹一眼就看出来这个女人不会买什么东西。他立刻弯腰躲在柜台后面,假装系鞋带,他躲着自言自语:
“啊!不管她了!叫别人去做这笔生意吧……谢谢!我宁可不做她的这个生意!”
可是罗比诺在叫他了:
“先生们,本次该谁做生意呀?是雨丹先生吗?……雨丹先生?”
由于雨丹坚决地不应声,于是这个脸上长满雀斑的太太只得由下面的售货员接待了。果然不错,她只要一些廉价的样品;而且她问东问西,耽搁了售货员十多分钟。不过,副主任却看见雨丹从柜台后面站起来。因此等新的顾客来到的,他面色一直十分严肃,把那个急忙跑过去的年轻人拦阻住,说:
“你的班已经过了……我跟你说了,可是你却躲在那后面……”
“可是,先生,我并不知道你说的啊。”
“不谈啦!……你等下一次循环吧……法威埃先生,该你啦。”
法威埃内心里对于这一次事件喜出望外,可是却向他的朋友瞥了一眼,表示希望他详解。雨丹,嘴唇都气白了,掉转头去。更令他气愤的是,他很熟识这个顾客,一个很漂亮的金发女人,经常到这一部来,店员们都管她叫做“漂亮太太”,可是她为人如何大家都不明白,甚至不晓得她的姓名。她总是买得很多,吩咐别人把东西放到她的马车上,然后就走。她身材高大,态度风雅,妆饰地很靓丽,像是有钱人,而且是属于上流社会的。
“我说,你的这个婊子买了什么吗?”雨丹在法威埃随同“漂亮太太”结完帐又回来的时候,便向他发问。
“什么!一个婊子,”法威埃答道。“不是的,她的态度可真不像哩……她肯定是一个股票商人或是一个医生的太太,至于她真正是什么样的人,我并不晓得,总是这一类的人吧。”
“算了吧!是一个婊子……外表高尚,谁也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法威埃浏览着他的销货记录簿。
“与我无关,”他又说,“我卖了两百八十三个法郎。我大概赚得到三个法郎。”
雨丹咬紧他的嘴唇,看着他的销货记录簿生气:这又是一种奇怪的发明,这样他们可以赚到很多钱的。他们互相无休止隐蔽地竞争。法威埃依旧表面上假装屈服,承认雨丹比他强,而背后却想把他吃掉。因此雨丹想到这个不如他的售货员,这么轻便地抢走了他三个法郎,就感到十分气愤。这倒真是一个好日子!如果这样继续下去,他会连请喝矿泉水的钱都没有了。在这种越来越激烈的斗争里,他在柜台前面来回走,把脑袋伸得长长的,要捉到他应得的那一份嫉恨着他的主任,这时主任正带着邵佛太太的使者走出去,而且再三地跟她强调:
“好吧!有数啦。请您带话给太太,我尽可能请慕雷先生答应这件事。”
慕雷早就不站在夹层楼大厅的楼梯口上了。突然间他又在通往底层的楼梯顶上出现了;站在那里他仍然鸟瞰着整个的店面。他看着那逐渐多起来的顾客,脸上有了光彩,他又恢复了而且提高了他的信心。期盼已久的拥挤,午后的混乱,终于来到了,他曾一度焦虑地感到绝望;所有的店员都各尽其职,最后一次的钟声宣布第三桌饭已经终结了;早晨的不吉利,无疑地是由于九时前落下的一阵骤雨,这还是可以补救的,因为早晨的蓝色天空又重新恢复了它胜利的欢乐。现在夹层楼的各部的生意也好了起来,他必须让路给一拨一拨上楼到内衣部和时装部去的太太小姐们;同时在他背后,在花边部和披肩部里,他听见有大量的交易在进行着。然而他最感到欣慰的,是在底层的走廊里的景象:零星杂货部里人们拥挤不堪,就连麻布部和毛织品部也都挤满了人,一排排买东西的人撞挤得寸步难行,眼前望过去几乎全部是帽子,中间还夹杂着几个迟来的家庭主妇的便帽。在丝绸部厅房的金褐色光辉下面,有些太太们脱掉了手套,轻轻地摸抚着“巴黎幸福”的料子,低声地讨论着。外面客人来的阵阵响声再也不会弄错了,马车声,砰的一下车门声,还有不断扩大的人群的喧嚣声。他觉得在他的脚底下,这个机器开始转动了,冒出热气,又活跃起来,收银台的后面,金子发着响声,在收银台上服务员立即把商品包装起来,一直到紧底下,地下室的发货部,送下来的包裹都已经堆满了,地下轰轰的响声震动着整个的店。在乱七八糟的人群中,稽查员茹夫谨慎地巡视着周围,他在秘查小偷。
“喂!是你吗?”慕雷突然说,他认出了保尔·德·瓦拉敖斯,被一个小伙计带着往这边走。“不,不,你不打搅我……而且,你要想巡视一下所有部门,只用跟着我就行了,今天我就呆在门口。”
他仍是不放心。当然,顾客是来得很多,但是生意怎样才会像期望的那样如心所愿呢?可是,他向保尔微笑着,带着他高兴地过去。
“像是要有点起色啦,”雨丹跟法威埃说,“只是我的运气不好,有的时候,的确比较倒霉的!……我又跟一个鲁昂女人交涉一番,那个倒霉鬼什么东西也没买。”
他说着便突出下巴指向一个刚刚走开的女人,她对我们这里所有的布料表示厌恶。如果他卖不出去东西的话,他那每年一千法郎的薪水是不能维持生计的;通常他要赚到七八个法郎的佣金和奖金,再加上他的固定薪金,每天平均可以得到十来个法郎。法威埃的日收入至今没有过八个;可是你看这个下流货又从他嘴里抢走一块肉,因为他刚刚卖出了一件袍料。招呼客人是这位冷酷的店员所不擅长的!真是气人。
“那些卖袜子和卖线的像是赚到了很好的收入,”法威埃悄悄地说,他所说的是帽袜部和零星杂货部的售货员。
可是雨丹,在店里四周巡视了一下,突然说:
“你认识老板的女朋友戴佛日夫人吗?……你看!手套部里那个褐色头发的女人,米敖正在招呼她。”
他停了一下,然后更把声音放低,眼睛一直盯着米敖,仿佛在跟米敖讲话似地说:
“喂,喂,我的老伙计,使劲捏捏她的手指吧,会有好的效果的!你的本事,大家有目共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