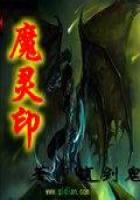我们来到外面后,虎子正坐在他的那辆私家砖车上冲我们招手。
我问虎子,瘸三让我们找你有啥美差事啊?虎子说,刚才张总回来了,说有一个老总在市里买了套房子要装修,让我们往楼上背水泥。二逼听后一下子跳的老高,这下子终于可以去外边转转了,整天呆在这个鸟不拉屎的地方,家里人都知道咱们是出去闯世界了,那儿知道是窝在个荒山沟里。
看你那德行,一看就是没见过大世面的人,富才瞪了二逼一眼说,你不知道,这里边有油水呢,这些大老板出手阔绰,就是给咱们一根烟抽,兴许还是中华呢。中华你们知道多少钱一根吗?我们都摇摇头。富才说,我也不知道,肯定比咱们一顿饭都贵。我和二逼又同时长大了嘴巴。
羊蛋,到时候给你烟你可别说不抽啊,先接下了再给我,虎子从车上跳下来拍拍我的肩膀说。
咱们怎么去呢?二逼张了老半天的嘴巴终于又说出了句话。虎子向圈墙根指了指说,让坐铲车去,现在正修呢。我顺着虎子的手望过去,见那辆破旧的铲车下,洼着一滩污水,水上趴着个穿橘黄色上衣戴橘黄色帽子的中年男子,他的两条裤子沾满乌黑的油渍,手里拿着个扳手正一左一右地拧着。
半个小时之后,他就从污水里爬了出来,换上了一套笔挺的西装,我听富才说,他叫小张,是张总跑业务的得力干将。富才还偷偷贴到我耳边说,咱们的张总说白了就是个包工头,土包子,咱们今天去给扛水泥的老总才真正的大款呢。
小张冲我们一挥手,我们就都跑过去躺到了铲车的铲子里。躺好了!他大叫一声,就跳上铲车,发动机器,把前面的铲子高高举起,我们也被猛地抛到了半空中。那天的阳光格外明亮,空气格外清新,瓦蓝的天上还游荡着一朵朵丰满的云。铲车在山间走的不快,我们都趴在铲子沿儿上东张西望作各种侦探。
先前荒芜的山坡上,一棵棵杏树桃树梨树山楂树还有各种叫不出名字的树,都在一夜之间神奇地开足了花朵,远望去,红红火火黄黄蓝蓝紫格铮铮的一大片,婀娜多姿的柳树也垂下了千百条青青的丝带,像少女倚在微风里吹拂着一头柔顺的头发。不断地有鸟儿在我们头顶叽叽喳喳地叫着,和我们同行一阵,又飞也似的去了。
经过刘嫂子的家时,我看到她围着一条淡粉色的围巾,坐在家门口那棵柳树下折下长长的枝条,也不知在编些什么。她笑着看了我们一眼,刚张开嘴,铲车就一跃过去了。接着是几个准备下地也不知道去干什么的农民,手里拿着把镰刀,肩上都搭着条绳子,绳子垂下来拍打着屁股又互相勾搭缠绕着。再后来迎面来了一群羊,放羊的是一个七八岁的小姑娘,一张黄黄的脸,顶着头像鸡窝一样乱蓬蓬的头发,她挥起羊鞭甩一声,羊群就扑扑通通地跳进了路边的草丛里。
来到镇上后,我认出了来时我和磨叔坐等瘸三的地方。我就贴着耳朵对虎子说,那天就是在这儿,我和那个姑娘下了车,我跟着她,她也跟着我……虎子瞪大眼睛举起手,刚要张口,就被一阵风刮得蒙住了头。我又慌慌张张地左右环视,想看看那天我们在那儿等车的时候那个邀请我们到饭店吃饭的老板娘在不在,要是在的话我也想向她招个手……
这时,车子突然停了一下,小张冲我们吼道,上平路了,你们都给我趴下,别再蹦来蹦去的,我要开快了。说着就猛的踩了下油门,我差一点儿就给扔了出去,赶紧抓住了富才的衣袖。碰到难走的路他开的慢时,我们就又偷偷地把头伸出来,像一窝刚孵化出的小鸡。富才和二逼一路上都在窃窃私语,我听了好久也没听出个什么。虎子一边指来指去一边说,他们在讨论车的牌子,那四个圈子的是奔驰,还有那辆叫宝马而不叫宝驴。
后来,一栋栋高楼拔地而起,就像来到了一片树林子里,车流人流川流不息,到处都是哒哒作响的皮鞋声,到处都是漂浮着鲜艳欲滴的红嘴唇子,到处都弥漫着一股说不出名字的香。我们都不再说话了,顾不上说话了,也不再你拥我挤了,只剩下脑袋像风车一样转着。我恨不能让眼睛变成十只八只,让它们两只跑到后面,两只跑到左边,再两只跑到右边。
一个卖菜的老大爷,赶着一头毛驴,在盲道上不急不缓地走,猛地一声笛鸣,毛驴吓得撒起欢儿来,白菜萝卜散了一地,老人跌坐在地上哭天喊地……一个水蛇腰,涂着浓妆的妇女,推着一辆车子,车上坐着个肥嘟嘟的婴儿,他朝我诡异地笑一声,就淹没在人流车流里……一个双目失明的青年,拄着一根拐杖,突然闯进了宽宽的大路中央,他就像一只热锅上的蚂蚁,就像一只掐了一条腿的蚂蚱,东奔西窜,慌慌张张……
车子猛地停住了,铲子落地,我们从铲子子里滚下来,就像滚下一截截圆形的木桩。小张跳下车说,你们先等会儿,我去找找看。他走到一边,掏出手机说了一通话,不一会儿,一个肥头大耳西装革履的男人迈着方步走了过来。他来到跟前后,果然给我们一人发了一根烟。虎子接过烟后就吸在鼻孔上深深地闻了闻,富才说怎么样?虎子又深吸了一口。是玉溪,富才把烟凑到眼前一看说,这烟很贵的,听说吸起来有一股子香味儿,劲儿很足。
虎子把烟点上了,富才也点上了。刚点上小张就说,快点来,往铲子子里扔水泥。我们就抬起水泥往铲子里扔,刚扔几袋就烟雾滚滚,呛得人喘不过气。扔满后,他就开着铲车走了。一会儿又扔,又走,如此几次后,才让我们跟着铲车过去。虎子说,他奶奶的,这么贵的一根烟也不让好好抽,就这么浪费了。
我们跟着小张来到了一栋楼房前,小张指着面前的一堆水泥说,你们一人扛一袋,跟着我,就这个单元六层。说完他便噔噔噔地上去了。我把水泥往肩上一甩,就一步一步地顺着楼梯往上爬,不算太重,就是水泥味难闻。到楼上后,小张说,都放到墙根,别码的太高,把底下的水泥都扛上来就算完。
接连背了七八趟,腿有些软绵绵的,我们就在六层的楼道里躺了下来。虎子说,啥时候能住到这样的房子里就好了。做你娘的美梦吧,富才弹了一下虎子的脑门说,轮到你住到这样的房里,人家就搬到月亮上了,地球也要爆炸了。我就看不出这地方有啥好,怎么看怎么像个鸽子窝。二逼说着,就从耳朵上取下那根玉溪,吹了吹上面的水泥沫子,叼到了嘴上。
这时,虎子走到我的身后,正准备从我的耳朵上拿那根烟的时候被我发现了,我白了他一眼,取下来叼到嘴里说,借个火。二逼就把打火机扔给了我,我点着吸了两口,又吐出些烟雾。虎子说,尝出些什么滋味没有,让我抽吧你还不让,你这纯粹是浪费国家烟草。不就是从鼻子里冒烟嘛,我说着又把烟塞到嘴里,从鼻子里喷出些烟。富才看后哈哈大笑着说,你得先把烟咽下去,烟要经过肺才行。我于是猛地咽下去一口,呛得我眼泪直流,连着咳嗽了好几声,差一点儿呕吐出来,头也变得昏昏沉沉的,在后来背水泥的过程中,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
半下午的时候,小张上楼来给我们一人发了一个面包,还有一瓶矿泉水。小张说,好好干,老总夸你们呢,还让你们补充补充营养。我们都说谢谢老总。
我们正坐在楼梯口吃饭的时候,听到楼梯里传来了叮叮当当的声音,叮叮当当声越来越近,就上来两个头发卷卷睫毛弯弯的女孩,一个戴着条金灿灿的项链,一个挎着个亮闪闪的包包,她们从我们身边侧身而过,就钻进了房间里。我们都把面包丢到楼道里挤着脑袋向里张望,可只看到了墙根下那一堆灰扑扑的水泥她们好像正靠在一间卧室的窗口前。
只听一个说,你怎么选个六层,冬天冷夏天热阴雨天气还漏水。
另一个说,他跟我说了,夏天给我装空调,冬天给我通暖气,楼顶破了就找人补补。
一个说,我还是觉得太高了。
另一个说,高处通风好,还能眺望,没人打扰。
一个说,指不定哪一天那个母老虎找了来,你往上走一层的余地都没有,只好从这里……扑通一声……说完,她们两个都笑了,笑得咯咯咯咯咯咯的,咯咯咯咯咯咯地笑着从我们身旁走过,又咯咯咯咯咯咯地笑着下楼梯,然后就叮叮当当的走了。
原来是个****,虎子突然骂了句****,就解开裤子冲到那间卧室里朝着墙壁重重地撒了一泡尿。
傍晚的时候,老总来了,问我们累不累,又一人发了一支烟。这是你们的辛苦费,老总从皮夹里抽出一张百元大钞伸到了我们面前,虎子拍了拍手上的水泥就接住了。
天黑的时候,我们背完了全部的水泥,我们又躺到了铲车的铲子里,车子发动了,我们又被高高举起,可这时每个人的身子都软绵绵的毫无力气,就像是一根煮烂的面条。我们东倒西歪地堆在一起,一路上都在听着车轮子单调的轱辘声和耳朵边沉闷的呼呼声。
到镇上后,车子停下了,小张说,我有点急事,要不你们先回去吧。虎子一听恼了,让我们怎么回去,这里离工地少说也有二三十里,要不你打个电话要工地上的人来接我们。小张掏出手机装腔作势摇头晃脑地拨了一阵,拍拍手说,没人接。我们就都蹲在了地上。他又绕着铲车转了两圈,从兜里掏出一盒红旗渠说,我也放放血,你们拿着这盒烟,一边走一边慢慢抽,烟抽完了,你们也就回去了。
我们都想了想,就把烟接了。小张就发动车子走了。我们就开始往回走。走了半里路,富才提议说,要不咱们从这一百元里拿出三十来打车咋样?要成,我就返回镇上去找车。他的提议立刻遭到我们三个的强烈反对,后来二逼说,我觉得这三十元留着走到刘嫂子家后搓一顿咋样?我们都举手赞成,富才也点了点头。
于是,我们就一人嘴里叼着一根烟,低着头慢吞吞的走。每走一会儿我们都要停下来商量一下到刘嫂子家后要什么菜,喝什么酒。富才说,他要吃鸡蛋炒肉。虎子说,鸡蛋和肉一定得分开炒才好吃,炒在一起说不定有毒。富才说,不但没毒,而且很好吃,他就吃过,叫木须肉。虎子说,要真有这么一道菜,他也要尝尝,他还想配上一杯二锅头……说完了,我们就继续走。
我像喝醉了酒一样摇摇晃晃地走着。我的两条腿沉甸甸的。我觉得背袋水泥上楼也没有这么沉甸甸的,我觉得就像是把两袋水泥分别拴在了脚脖子上。终于,我们来到了刘嫂子家的大门前。大门紧闭,院子里漆黑一片,我们拍着门上的铁环扯着嗓子喊了大半夜也没人应一声,我们像流水一样躺在了地上。
那时,月亮正挂在柳树的梢头上,刘嫂子家的大门前,散落着一地的花瓣,花瓣上杂乱地扔着些被折断的新鲜的柳条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