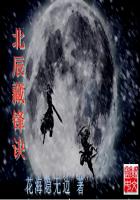空旷的地下室黑咕隆咚的,走起路来还有回声。我带着头灯,拖着水管子开始从一头浇起。正浇着,磨叔下来了。
我说,叔,你下来做什么?也是来加班的?
不是,就下来看看你。磨叔说,奇了怪了,一冬天没下,现在下起雪来了。冷不冷?
我说,不冷。磨叔说,夜长,后半夜就冷了,我给你生堆火吧。说完,磨叔就从我头上扯下头灯,四下里搜寻起方木头和纸盒子来,不一会儿,就在大厅中央燃起了一堆大火。
磨叔说,蛋儿啊,不用老拿着水管子在那儿站着,放地上来烤会儿火吧。我就找了两块砖,和磨叔围着火堆坐了下来。磨叔从口袋里掏出半盒烟递给我说,抽吧。我说我不抽。磨叔说,那就放先放地上,等后半夜困了就抽,可别睡着了啊。我说恩。
磨叔冲着火堆吐出长长的一口烟说,蛋儿啊,你也得学个一技之长啊,老这么干小工不是个事儿啊……蛋儿啊,你跟着老李学个泥瓦匠吧,学个泥瓦匠以后就不愁没人用了,也不愁娶不到媳妇了……蛋儿啊,娶个媳妇咱家就后继有人了……蛋儿啊……
磨叔喋喋不休地说着,他让我想起了多年前的磨叔,他赶着驴车三里五村买豆腐,他喊起卖豆腐咯像唱歌一样好听。有时婶子也会跟着去,婶子喜欢骑在驴背上,也学着他那样扬起脖子喊,卖豆腐咯……
我突然扬起脸对磨叔说,我想婶子了。磨叔听后就不再说什么了,只低下头闷闷地抽烟,那半盒烟抽完后,磨叔就走了。磨叔走后,地下室又恢复了先前的寂静和空旷,只有方木噼噼啪啪燃烧发出清脆的爆裂声和沉闷的流水声。我在火堆旁坐着,把手伸向火堆一正一反地烤着,就像烤羊肉串儿那样烤了一会儿之后,就决定到外面去看看。
我顺着楼梯爬上去一望,呼啸的旋风吹口哨般地响着,细碎的雪花正漫天飞舞,就像天女散花一样。刚站一会儿,手就被冻得冰凉,我把两只手塞到脖子里暖着。这时,我看到远处有个人影正慌慌张张地向这里走来,到近处才看清是小倩。她披了件青色的风衣,脚上蹬着黑色的马靴。
我问她去哪儿,她说她昨天在地下室干活儿时可能丢了一件东西,今天睡觉的时候才发现了。我问她什么东西。她说一串钥匙。我说明天再找吧,反正已经丢了一天了。她说找不到她晚上就睡不着了。
我们从楼梯下去后就分头去找。第一次碰面的时候没有找到,第二次碰面的时候还是没有找到,第三次碰面的时候小倩说,算了,也可能是丢在外边了。我们就朝着火堆走去。我弯下腰去把地上那块砖头吹了吹,示意小倩坐下。这时,我发现小倩的眼睛一亮,我顺着她的目光一望,看见一尾金色的鲤鱼正把头伏在柴火堆里,周身的鱼鳞在火光的照耀下闪闪发亮。小倩俯下身去拿了起来,我看见在金鱼的嘴里衔着一串钥匙。
这是我的护身符。小倩拿着金鱼朝火堆照着说,爷爷说我很小的时候,生了一场大病,她大半夜的赶着马车拉着我去外村看医生,那天,下着大雪,还刮着冷飕飕的风,车子一滑就陷到了雪堆里。爷爷说这条金鱼就是在雪堆里发现的,他给我挂到脖子上我的病就好了。
我说我和磨叔在这儿烤了大半夜的火怎么就没有发现。
也许是刚爬过来的,它在那边的泥水里又阴又冷我们又吵吵闹闹,就爬过来烤烤火。小倩冲我笑着说,谢谢你陪我找了大半夜。说完就转身要走。我说再坐会儿吧。小倩说不早了,该睡觉了。接着噔噔噔地上了楼梯。
我跟着她来到上面一看,细碎的雪花已经变成大朵大朵的了,就像无数只蝴蝶在风中飞舞。小倩大步流星地走进了雪花里,背影越来越模糊。我呆站在原地,突然就举起双手套在了嘴巴上大喊了一声,小倩,谢谢你给我缝裤子。
小倩好像听到了,又好像没有。还像站在雪地里还回头冲我笑了一下也好像没有。我觉得她是听到了,也回头对我笑了,因为当我又坐在火堆旁时,小倩就一直在火焰里对着我笑,第二天躺在炕上的时候又听到小倩说,没事,你太客气了,以后裤子破了还来找我。
想着小倩的同时,我还在想着磨叔,磨叔说,你娶个媳妇咱家就续上香火了。我没想什么香火不香火,我觉得我是该学门手艺了,学门手艺我就能挣到很多的钱了,有了钱我就回家盖一间漂漂亮亮的房子,再买个小电炉,冬天下雪的时候,我就也能像富才和梨花那样围着火炉烤馍吃了。
所以我就想学个泥瓦匠了,就开始拼命地巴结老李了。他说渴了我就给他打水,他冒汗了我就给他扇风,看到他扭腰捶背我就在他屁股底下塞上一块砖头,又一次他脱下外套我还在他口袋里放了一包香烟。三天过去了,五天也过去了,七天之后他就开始指点我了。
那一天,工地停了一会儿电,剩下最后一堆泥的时候,老李说,别弄上来了,你拿着这个在底下甩两下我看看。说着就把手里的瓦刀当啷一声扔到了我面前。我拿起瓦刀铲了一铲子泥用力一甩,却在面前甩出一个泥堆儿。二逼咧着嘴,露出黄渍渍的牙齿大笑起来,连个泥巴都甩不好,我看你甩的怎么越看越像一堆老牛屎。我不管他,又耐着性子试了两次,,不是堆在一起,就像零零星星地撒了一地。老牛肚子不好受了,拉的全是稀屎,二逼在架子上笑得前仰后合。我压住怒火,用尽全力猛地一甩,那把瓦刀就像只笨蛤蟆,一头扎进了泥堆里,只露出个把儿。
头把刀老李从怀里摸出一根烟,二逼赶快从兜里掏出打火机,用手捂住,凑到了老李嘴边。老李哼了一声,从鼻孔里喷出两道白烟,就这还想学砌墙,连个泥巴都撒不好,把瓦刀拿出来洗干净。我就把瓦刀从泥堆里拔了出来,放到水桶里洗了洗。
老李扑通一声从架子上跳了下来,从我手里夺过瓦刀,轻轻一弯腰,蜻蜓点水似的在泥堆尖上一削,就铲了一铲子泥,他随手轻轻地一挥,那坨你就像清泉一样从瓦刀尖上缓缓地流了下来,在地上摆成了长长的一条小蛇。他把瓦刀换到左手上,左胳膊又轻轻地去地上一收,那条小蛇就乖顺地爬到了瓦刀上,盘成了一个小小的圆堆。
二逼在架子上看的傻了眼,他跟着老李走南闯北这么多年,还没有见过老李的这套绝活,二逼后来赞叹说,那坨泥甩的真是龙飞凤舞出神入化几入仙境。二逼看了一会儿之后,突然就哇的一声大叫起来,原来是烟头烫着了嘴巴。老李听到了,忙在自己嘴巴上摸了摸,这时我们才发现他的烟头早已烧的连烟屁股都没有了。
从那天起,我就更加关怀起老李来了,要说以前那是巴结,如今就是打心眼里佩服了。二逼也一样,当老李的脚再次伸过来向他心口眼儿上猛踹时,他的眼中没有了一丝怨恨,全变成了满满的自责。如果那时谁要问我,当今天下谁是英雄?我会毫不犹豫地回答,是头把刀老李。如果还有人问我,你是何人?我一定会告诉他,我就是头把刀的二弟子,三把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