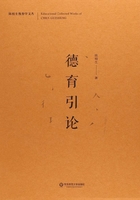据说在台湾电影界,《女朋友男朋友》被誉为“大时代的青春史诗”。
几年之前我还在念大学时,有一阵子也非常喜欢台湾青春电影,我想,那是我青春期的尾巴,坐上一列呼啸而过的火车,一路透过飞掠的车窗向外张望,看到隔海相望的那些咬着文艺腔的年轻人。某些殊途,实则同归。
《女朋友男朋友》前半段不可避免地落入俗套的窠臼,依然是“两男一女”式的人物格局,阿良、美宝与阿仁,三个经常腻在一起的年轻人,他爱她、她爱他、他爱他,这样模式化、无新意的三角格局。
不过可贵的是,影片注入了大时代背景,从1985年高雄的夏天,教官专制压迫的台湾高中,到1990年的台北,如火如荼风起云涌的学潮运动。有动荡不安的社会政治作注脚,他们纠缠不清的青春躁动、情感拉扯也就格外动人。
“乱世”中,仍有阿良摘下一把玉兰叶让美宝安宁的美好画面。她将叶片合在掌心轻捻搓揉,嗅着香气慢慢散出来,她身体内的疼痛就一点一点地得以减轻。这个习惯也生长在她生命的叶脉里,成年后的她开车在台北街头,还会停车摇下窗户向叫卖的阿嬷买两束玉兰花,并得以与失联多年的阿良重逢。后窗缓缓摇下,却是阿仁微笑的脸。
像所有的秘密都会有月亮的假面,阿仁始终知晓阿良对自己的心。学校楼梯口他背对着他,无奈地对阿良说:“你不要傻了,大家像以前那样在一起不是很好吗?”于是参军前夜,他才可以在玩游戏中借着醉意,半真半假地亲吻阿良,是慰藉,是交代,或许也是一个肆无忌惮又于心不忍的偿还。并在阿良耳畔呵出热气低语说,“友谊长存”。异曲同工于《甜蜜蜜》里的某年春节,李翘在香港一家M记当清洁工,她边擦玻璃边对站立不远处的黎小军笑着说:“友谊万岁!”
而要过很多年以后,我们才明白这也是世上最无力的四个字。
重逢后的三个人,没有了少年时对“你是喜欢红色还是蓝色”的纠结,也没有了在校刊上写藏头诗的心照不宣。已是1997年,他们各自藏着心事唱歌,有人不停地接电话,有人终于爆发吼着“友谊长存个屁”,有人甩出的巴掌声回响在空气中,谁都回不去了,回到1985年那个如梦如幻的家乡,那无数个弥漫玉兰花香的夏夜。
也回不去那个尚未干涸、波光粼粼的游泳池边,阿良与美宝并肩而坐,他把仁字写进美宝的手中,美宝也把自己的名字写进他的掌心握紧,脸上都画着被泪痕染湿的彩色颜料,各自托付生命中最重要的爱。
是因为知离别,他不能像恋人那样陪在阿仁身旁,从此将他交给她;也是因为知离别,她把自己留在他的心里,她要他一直都要记得她。当这一季过后,这一场梦醒来,天下早已会大不同。
成年后踏入社会,彼此关系重新洗牌,生活撕开道道狼藉伤口:曾经追求自由民主、最叛逆最激进的阿仁穿上西服,成了唯唯诺诺的豪门快婿、虚伪政客;美宝失去年少时剃掉半边头发的果断轻狂,以爱情的名义成了阿仁的情妇;阿良也比从前更沉默更木讷,他爱上一个有妇之夫,跌入孤独的宿命。
阿良和美宝在彼此身上看到一面镜子,如同照妖镜诡魅彻骨一针见血,他说:“其实我们都在自讨苦吃。”是呵,没有谁规定人生就要这样苦逼,是我们自己走上这条不归路。如果像剥洋葱一样层层剥开,你会看到一颗苦瓜心。那么苦那么寂寞又那么贱,却流下心甘情愿的甜的眼泪。如果没有你,故事又怎会浓墨书写,直至铭心刻骨回肠荡气?那一年曾有过奋不顾身的勇气,即使无疾无望而终,我的人生因此才有了附丽。让我感谢你,赠我苦瓜心,好让我看见,此生多美丽。
美宝在阿仁身边沉睡,又在重逢阿良后苏醒。怀孕、长肿瘤,两件事同时降临,在与阿仁相约私奔的机场,她望着阿仁临行前跟孩子在电话里语气温柔地讲童话故事,也听见自己灵魂里吹过的风。
她对着他跳起高中时的那段舞,欢快地转身去帮他“买咖啡”,高跟鞋滴答滴答滴答,伴着机票在电梯传送带上滑远,那一刻,她走路的样子好美。然后,她就消失了,如同那封没有字的空白信。
影片最后,人到中年的阿良孑然一身,带着两个靓丽可爱的混血双胞胎少女坐在公交站牌等车,那是他曾经最亲爱的两个人留下的孩子,这两个人也是他最好的朋友,在他十七岁的时候,一个女朋友,一个男朋友。
字幕滚出,音乐响起,我却哭了。我想我喜欢这个故事,在我二十六岁也终将过去的时候,像失去了一颗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