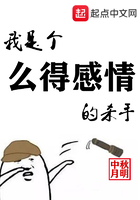陕北有个高西沟,我家就住在沟里头。
在峁梁交错,沟壑纵横的陕北高原,高西沟的几座山、几道沟实在算不了什么。最大的不同是“百灵子过河沉不了底,滚滚的黄河没有高西沟的泥”。这才使得高西沟与众不同起来。
作为黄土高原生态治理的一面旗帜,高西沟的声名在蛰居一段时日之后在今朝再度鹊起,吸引了一批又一批的各级领导、专家学者前来参观学习。
丁亥之金秋,把《米》杂志的创作笔会定在高西沟召开,这有华勇的一番良苦用心。作为一名地方作者,对本土情感趋于淡漠,你对他还能有什么期待?有道是墙里开花墙外香。西安城隍庙长大的那个叫冷梦的洋洋洒洒地数十万字的《高西沟调查》就荣获了陕西省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这是值得众人加以认真学习的。
华勇能弄事。一次县级文学爱好者的普通聚会,他竟能把省、市的一些文化名人给鼓捣来。这不能不说是米脂文艺界的一件幸事。狄马先生便是其中的一位。
狄马这个大名可谓是如雷贯耳。狄马文风之刚烈、桀骜不驯是大为人所称道的,有专著《另类童话》、《我们热爱什么样的生活》行世。狄马的随笔,贯穿着强烈的批判意识和道义承担精神。我极为佩服他的善思和敢言。在当代中国杂文界是有其一席之地的。当这个头发格外卷曲,胡楂铁青的这个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的真真切切地就站在你面前时,真有点不知所措的喜悦之情。情形一如一位在山梁上劳作的老农,婆姨送来一罐子饭,揭开盖口,里面竟有烙油饼,老农于是就又放手了,又是避了罐口拍手,又是在衣服上不停地蹭手,想象谋算着如何享用的喜悦之情。
农历九月的高西沟,犹如一位体态丰盈的少妇,处处充满着诱惑。在庙梁山顶,这一高西沟的至高点上,由省、市、县三级组成的采风团队里,人人都被朝阳辉映下的绚丽多姿的秋日山庄美景所慑服。更多的是被高西沟几代人战天斗地的冲天豪情所感动着。狄马始终在专注地倾听着,不时为之动容。完了在下山的路上,狄马先生告诉我,从高西沟村支书姜良彪,这个不足600人的深山沟里的支书那沉稳而娴熟的讲话里,挥洒之间的干练里,你就能感受到这个小小村落的恢宏大气。
座谈会结束之际,已是正午时光。看到这很好的太阳,我就忍不住与狄马先生合影于村委会前。在阳光的直射下,几次拍照都因我的眼睛眯得太小而失败。完了勉强能挑选吧,小眼睛照大,那还是我吗,丑就丑呗!狄马闻言哈哈大笑。声言,和我合影,你根本用不着自卑。他其后对米脂文风之盛队伍之大大大加以赞叹,盛誉不简单。
高西沟的避暑山庄里,我们是山庄启用后的第一批客人。避暑山庄的晚宴上,气氛甚是热烈。酒逢知己千杯少。不胜酒力了便以诵诗代之,唱歌代之。久闻狄马先生海量,可他也有到位的时候。华勇便撺掇着让狄马以歌代酒。我是不善饮之人,可也忍不了酒场之热闹,三杯过后便浑身燥热。便悄悄离席了在避暑山庄的院墙外的空地里不停地来回踱度。众人之吵闹不绝于耳。更特别是狄马如泣如诉的《女儿歌》在寂寂的山庄沟道上空回荡着。我一边听一边来回踱步,自言自语,地道!地道!不料被出来在墙根尿尿的醉酒者大声吓喊,谁?
寄情于山野的人们在求得一场难得的际遇。欢娱总是过于短暂,时光的流逝于诸人是多么的无奈,但这一场相会是在多少年之后而谈之甚慰之事啊。
归来之余,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一日夜读板桥先生《范县寄朱文震》,读至“彼元章但知好之为好,而不知陋劣之中有至好也”。便仰坐于床,痴痴望着墙壁,想象着狄马先生之大额颅,遂急推醒熟睡之妻,以笔墨伺候,疾书一幅字,缀于与狄马先生合影之下,其辞曰:陕北最丑的两个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