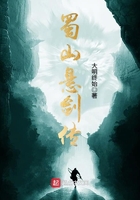晓戈要去日本了。机场上,我见到了关颖和她的女儿莹莹。
晓戈对她依然很冷淡,临上飞机前,甚至连句道别的话都没有。关颖呢,也早已失去了女诗人的浪漫,满眼流露出的都是惆怅。他们闹到这个份上,是我难以料到的。当初,她对晓戈爱的是那样的热烈,怎么短短几年,就僵成这个样子,简直不可思议。
莹莹是个懂事的小女孩,不停地在爸爸妈妈之间周旋着,像个小天使。
候机大厅乱哄哄的。又有几架国内航班晚点。电子显示屏不断地将临时变更的时间显示出来。昨天下午,又有一架民航客机被劫持到台北桃园机场。乘客们对此议论纷纷,称之为死亡游戏,可飞机又不能不坐。
晓戈一改往日不修边幅的邋遢样,也西装革履,很有风度。
“晓戈,预祝你画展成功,载誉而归。”登机前,我握了下他的手。
“谢谢老同学。”他微笑着瞅着我。
“爸爸,您可早点回来,别让我和妈妈等急了。”莹莹抱着他的大腿,仰起小脸蛋,很认真地说。
“好的,”他慈爱地将女儿抱起来,亲了亲她的小脸蛋,“我会给你买一个好大好大的玩具娃娃。”
“那你也该给妈妈买回点什么呀。”莹宝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吻说。
晓戈瞧了一眼关颖,她已将脸扭到了一旁。并在用手绢揩眼角。
“当然可以啦。”他拍了女儿的头一下,说,“你这个小家伙,什么心都操。”
“君子一言,驷马难追。”莹莹不知啥时学到的大人话,振振有辞地说。
我憋不住笑了,说:“晓戈,你的小姑娘真可爱。”
从机场返回市区的路上,关颖闷闷地坐着,一言不发。我望了望车窗外,一架波音747呼啸着从头顶上掠过。晓戈也许就坐在上面,我默默地想。
“妈妈,你怎么了?”莹莹将头依偎在关颖的怀里,轻声问。
“妈妈有点累了。”她闭上眼睛,一点也打不起精神来。
这时,莹莹悄悄俯在我耳边说:“叶阿姨,昨晚妈妈和爸爸又打架了,吵得可凶了,把我都给吓哭了。”
我的心一冷,想:“这个晓戈真不懂情理,怎么能这样对待自己的妻子呢。”
“的士”开到了省实验幼儿园门前,莹莹下了车,朝我们摆摆手,说:“叶阿姨,妈妈再见。”就连蹦带跳地跑了进去。
“关颖,心放宽点,不要想得那么多。”我劝慰她。
她呜呜地哭了,说:“叶卉,活着真没意思,要是没有莹莹,我早去死了。”
“你怎么能这么想!”我惊愕地说。
“可这活的滋味比死了还要难受,你知道吗?一个男人有妻子,却惦记着别的女人,我简直忍受不了!”
听了关颖的话,我的心也像针扎了一样,在滴血。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关颖想必把我和赵楠的关系看作铁板一块了。这其中的苦衷,谁能知晓呢?赵楠在搞女人方面,只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只不过我们原本的关系就不好,所以承受的能力大一些罢了。
车子到了美协,我下了车,付了车费并嘱咐将关颖送到家门口。
她感激地握了握我的手,说:“叶卉,你是个大好人。”
“谢谢。过奖了。”我帮她把车门关上,目送她远去。
没想到关颖会这样信任我,我心里好感动。
我刚迈进楼门,梦怡就大声对我说:“叶姐,你让我好等呃。”
“是吗?”我冲她开玩笑地说,“等我是假,想探探消息是真吧。”
“叶姐,你坏。”她攥起小拳头使劲捶了我一下。
“哎,说正经的,那份举办全省美术大展的通知打印了吗?”
“报告秘书长同志,敝人已经完成任务,请领导过目。”她故作姿态地将打印稿拿给我。
我粗略地看过一遍,改了几个错别字,签名让她拿去付印。
她走了几步,又扭过头来小声问:“他爱人去机场了吗?”
“你这个小丫头,人家去不去,关你什么事。我可告诉你,在这方面可不许搞‘自由化’呀。”
我板起面孔,心说,一个陶翎艺就把关颖气个半疯,你再踩上一脚,还不得出人命呀。
“你都说的什么呀。我不过随便问问,又没说什么。”她拿起稿子,嘟嘟囔囔地走了。
她还没走一分钟,又鬼精灵似的转了回来,把头探进门说:“我差点忘告诉你啦,省宣传部的杨耀处长让你给回个电话。”
“糟了。”我用手拍了拍脑袋。唉,晓戈人都飞走了,可我欠杨耀的那幅画还没来得及给他送去。于是,我又匆匆给他挂通了电话。
“杨处长,十分抱歉,我本想前天就把画给您送去,可这两天我们美协忙画展都昏了头,一时又脱不开身,真不好意思。这样吧,等明天,我抽空去您那儿一趟。”
“小叶呀,光画饼,可不能充饥哟。”
“没错儿,画就存在我这呢,我向毛主席保证。”
“好吧,一言为定。明天下午,我在办公室等你。”
我放下电话,长长地舒了一口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