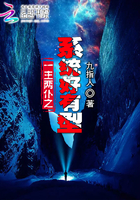王春林王春林,山西大学教授。
一、关于国学的概念界定
国学这一概念的形成,按照朱维铮先生的说法,是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现代文化开始形成的时候。朱先生认为:"1900年之前,中国没有"国学"一说,只有跟西学相对的中学,跟新学相对的旧学。"国学"和"国粹"的概念都来自日本。据我所知,"国学"概念最早是1902年引进的。最早被中国人所用是在1903年,梁启超、章太炎给黄遵宪写信,约他一起来办《国学报》。黄遵宪指出中国没有"国学",原因之一是中日情况不一样。中国人开始讲"国粹"也是在1903年,出现在章太炎在上海西牢里写的《癸卯狱中自记》,意为自己担负了弘扬汉族文化精粹的使命。有一个叫宋恕的学者,看到"国粹"这个概念就批判,他说,既然有粹就有糟,就有糠,那么国糠是什么?既然讲国粹,为什么不讲国糠?这在当时有巨大的影响,后来章太炎就不讲了。中国只有一个"国故"。1910年章太炎出版《国故论衡》。"五四"以后,重新回顾传统文化就叫"国故"。"[1]很显然,在古代的中国,其实是不存在所谓国学问题的。只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当"西学东渐"逐渐地成为一种可谓是汹涌澎湃的思想文化潮流的时候,才有了国学问题的正式提出。正所谓像正反、大小、左右等都是一种共生关系一样,所谓的国学,其实也是与西学共生的。没有西学,又何来国学?而西学进入中国,却又直接地催生了中国的现代性,所谓的中国现代文化也就是在西学的影响之下,才逐渐地萌芽并发展成形的。这样看来,国学这个概念,从它诞生的那个时候开始,就天然地具有一种与西学分庭抗礼的意味。
就我个人的视野所及,关于国学的定义,目前有代表性的有两种。
第一,将国学理解为中国的传统文化或者更进一步地窄化为所谓的"六艺之学"。刘梦溪先生所持有的便是这样一种看法:"说到底是国学有宽窄两重涵义,宽的就是胡适所说的,凡研究一切过去历史文化的学问,即研究"国故学"的,都可以简称为国学。但后来大家普遍接受的国学的涵义,是指中国的固有学术。但这也还是比较宽的涵义。国学的窄一些的涵义,我多次说过,应与经学和小学联系在一起。换言之,国学应该如马一浮所说,是指"六艺之学",亦即"六经"(《乐经》不传,剩下"五经")。《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四子书",是"五经"的通俗课本,也可以看作是通向"五经"的桥梁。国学的泛化,只能伤害国学。"[2]可以说,刘梦溪先生其实更多的还是在国学概念刚刚被提出时的那种意义上理解看待这一概念的。
第二,对国学的具体内涵进行了很大的拓展,将"五四"之后发端的中国现代学术与现代文化都包容了进来。著名现代文学研究专家王富仁就是这一方面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在王先生看来:"中国学术经过长期的发展,已经有了巨大的变化。"五四"以前的中国文化和"五四"以后发展起来的中国新文化,都属于中国文化的范畴,都应该进行认真的研究。原来的"国学"概念已经不能概括全部的中国学术,因此也不再适应当前中国学术事业的发展。"新国学"就是适应当代中国学术发展的需要提出来的,它视中国文化为一个结构整体,是包括中国古代学术和中国现当代学术在内的中国学术的总称。现在,我们的学术格局变得前所未有的完整,但当更为完整时,必须警惕"一门独大"——如现在提倡的读经等所谓的"国学",分裂就有可能出现,历史总经历着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过程,"新国学"就可避免分裂的过程,因为"新国学"倡导中华文化的整体观念,说胡适很行,同样也不否认鲁迅的伟大,各种文化的对立不要看得那么重,每个部分都是不可缺少的,现在多数学术都是压制别人的,先把别人压低再把自己抬高,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弊病之一。而"新国学"强调的就是:政治、经济、文化是一个整体,谁也缺少不了谁。"新国学"还是一种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一个人既可以喜欢陶渊明、李白,也可以喜欢鲁迅、沈从文,承认各个学科的价值,有助于我们吸收丰富的知识,同时能够充分发挥每个人多方面的文化潜力。"[3]实际上,也正是为了更好地实现自己的这样一种思想理念,所以才有了由王富仁先生担纲主编的不定期刊物《新国学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陆续问世。这本刊物的编辑出版,完全可以被看作是对王富仁新国学理念的贯彻与践行。
对于王富仁先生要把中国现代文化与现代学术努力地纳入到国学体系当中的行为动机,我想自己还是能够理解的。我以为,其中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就是高等学校长期以来形成的所谓学科体制的压力。具体到汉语言文学来说,一种约定俗成的等级化情形就是,古代文学与语言学是最高级的学科,现当代文学与世界文学则是次一等的学科,而诸如写作学之类,就更是等而下之的了。很可能正是出于有效突破这样一种不合理学科体制的缘故,作为知名现代文学研究专家的王富仁先生才试图通过所谓新国学概念的提出,通过对于传统国学内涵的拓展,进而达到提高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地位的根本目标。然而,王富仁先生的初衷虽然值得肯定,但在我看来,为达此目标而肆意地扩大国学概念内涵的行为却又是大可不必的。原因非常简单,如果按照王富仁先生的意思来理解国学的话,那么国学事实上也就成了一个包含全部中国文化在内的语词,其大而无当的特征是十分明显的。实际的情形是,当一个概念变得大而无当几乎无所不包的时候,这个概念的有效性也就应该受到怀疑了。就国学这个概念而言,我们必须充分地注意到它与西学的共生性。如果脱离了这样的一个生成语境,那这个概念存在的意义也就的确不存在了。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王富仁先生没有必要非得改造借用国学这个概念,他的那样一种学术思想,离开了国学的概念其实也完全能够讲清楚的。因此,我认为,我们最好还是应该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意义上来使用国学的概念。好在最具权威性的《现代汉语词典》中,也是这样解释的。《现代汉语词典》中说,所谓国学,有两层意思,一是指"我国传统的学术文化,包括哲学、历史学、考古学、文学、语言学等"。二是指"古代指国家设立的学校,如太学、国子监"[4]。很显然,我们这里所具体谈论的,只能是第一种意义上的国学。
二、国学在20世纪遭受的两次重创
如果我们把国学具体地理解界定为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的话,那么,便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整个20世纪,国学曾经先后遭受过两次巨大的重创。第一次的重创就是来自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猛烈撞击。从根本上说,新文化运动之所以得以成形,就是受到了西方文化直接影响的缘故。如果没有陈独秀、胡适、鲁迅、李大钊等一批先知先觉的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以一种主动寻求的姿态积极介绍引进西方文化,那么,中国现代性的起源就是难以想象的,中国现代文化的形成也同样是不可能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出现并最终完成这样一种现代性的社会转型,是所谓天时地利人和的一种结果,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一个非常简单的道理,当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民族都先后经历并完成现代性的转换的时候,中华民族肯定不可能置身于其外的。因此,虽然中国社会历史的现代性转型,的确招致了来自于文化保守主义者的强烈阻挠与反对,但这样一个过程最后还是完成了。之所以强调新文化运动的发生标志着中国现代性的发生,意味着中国现代文化的终于成形,就是因为"五四"之后出现的中国现代文化与传统的中国文化存在着本质性的差异。这种本质性的差异,实际上也就意味着中国现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出现了一条巨大的文化鸿沟。那么,对于这样一条文化鸿沟的存在,我们应该采取怎样的评价态度呢?我们注意到,其实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所谓寻根文学形成的时候,就已经有论者将这种文化鸿沟形象地称之为"文化的断裂带"(郑义语),其中一种否定新文化运动的企图表现得十分明显。值得引起我们高度注意的是,这样的一种思想倾向,在有着越来越多的学者大力倡扬国学的今天,已经拥有了众多的认同者。我认为,对于这样一种思想倾向,我们必须保持足够的警惕性。我们必须看到,现代性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的兴起,是一种历史发展的必然逻辑结果。很显然,当整个世界都发生现代性转型的时候,中国肯定不可能自外于世界历史的总体演进趋势。在这样的意义上,任何一种怀疑否定新文化运动的行为都是我们应该坚决抵制反对的,我们必须不容置疑地捍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正当性。在我看来,只有在这样的一个前提之下,才可以讨论国学在"五四"时期遭受重创的问题。由于现代性发生之前的中国,完全处于传统文化的笼罩之下,可以说是国学的一统天下。现代性要想在古老的中华大地立足生根,所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怎样有效地"攻击"传统文化,从国学那儿为现代文化的生存争得必需的发展空间。这样,以毫不妥协的方式坚决激烈地反传统,"打倒孔家店"也就成了陈独秀、胡适、鲁迅这一批现代知识分子必然的人生选择。这一批知识分子可谓是时代的"一时之选",是具有相当"攻击力"的时代精英。在他们强有力的批判"攻击"之下,国学之遭受重创当然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20世纪,国学之遭受第二次重创,是在所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关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文学,我们注意到,洪子诚先生有这样一段叙述:"《纪要》(指《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和另外的一些重要文章、讲话,全面阐述了这一派别进行"文艺革命"的纲领和策略。《纪要》攻击"建国以来"的文艺界,"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30年代文艺的结合"。它重申了毛泽东在"批示"中的判断,对50年代以来的文学现状,作了这样的估计:"十几年来,真正歌颂工农兵的英雄人物,为工农兵服务的好的或者基本好的作品也有,但是不多,不少是中间状态的作品,还有一批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毒草。"因此,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在对"旧文艺"批判的同时,"纪要"指出,要创造"开创人类新纪元的、最光辉灿烂的新文艺";作为这一实验,要"搞出样板"。"[5]虽然洪子诚先生集中讨论的是"文化大革命"文学的问题,但其中的一些话语对于我们从整体上理解"文化大革命"还是极有帮助的。这就是"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彻底搞掉这条黑线""与"在对"旧文艺"批判的同时,《纪要》指出,要创造"开创人类新纪元的、最光辉灿烂的新文艺""这样两句。这两句话明显地表露出了"文化大革命"所要达到的两个目标,其一就是全面否定文艺界在"文化大革命"前所取得的大多数成果,其二则是要在摧毁了一切旧文化的根基之后,在一片空白之上创造所谓无产阶级的新文化与新文艺。道理非常简单,如果说"文化大革命"中的激进派们连"左联"成立以来已有数十年积累历史的中国现代左翼文学都要全盘否定的话,那么,他们对于其他的中外文化遗产的否定态度也就可想而知了。实际的情形也确实如此,弥漫于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正是一种可谓是异常极端的文化虚无主义态度。所谓的不破不立、"破四旧,立四新",所谓的批判打倒一切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所谓的"批林批孔",可以说,所有的这一切都只能被看作是文化虚无主义思想的一种极端体现。因此,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其实质就只能被理解为是要"大革文化命"。既然所有的中外文化遗产都处于被质疑被批判否定的状况,那么,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之集中体现的国学的被全盘否定,也就自在情理之中了。我们注意到,学界近年来还出现了一种将"文化大革命"与"五四"相提并论,且试图将二者共同加以全盘否定的怪异论调。的确,如果只是从它们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所采取的批判否定的表层态度来看,二者之间似乎真的存在着若干相似之处,但是,我们一定要清醒地认识到,"五四"之意味着中国现代性转型的发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文化建设性任务,其与后来"文化大革命"的那样一种破坏一切人类文化遗产的极端文化虚无主义态度是绝不可同日而语的。因此,将二者笼统地混为一谈并加以否定,其实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对于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有足够清醒的认识。然而,虽然我们反对将"文化大革命"与"五四"简单地归并谈论否定,但是,从国学的角度来看,说国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受了较之于"五四"时期更为沉重的打击,的确是一种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