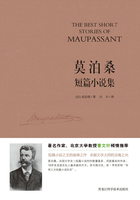“我走了,这些仓库里的瓦片、房舍、家务谁来照应呢?”苔青坐在平山对面,小口啜了一点鸡汤,不好意思地低垂着头,时不时抬头扫一眼平山,那眼神里又是欣喜又是迟疑和拒绝。平山心底略略地有些清楚,但也不好意思探问,只细致地观察苔青的长相,虽然已经过了最好的韶华,但仍能看出当年鼻子秀挺,眉目楚楚的隽秀之貌。
“这么说,一定要招愿意上门的了。”平山平淡地问。
苔青低头不语。
“为什么不招一个本地呢?”
“本地的风俗‘好子不上门’,上门女婿总让人低看一眼,愿意上门的,我也实在看不上……让您见笑了!”
平山下午还想到外面转转,所以,只简简单单喝了点鸡汤,没有饮酒。平山说,晚上再饮。
用完饭,平山拿了相机,折出门,穿过巷子,沿小街一路溜达。其中几家大宅大院都开辟出来做了小博物馆、陈列室之类的,其中一家称为“印馆”,平山觉得有趣,就踏了进去。
展厅不大,原来本地风景名胜都让全国有些影响的书法金石家题字刻篆,其墨宝碑铭篆刻手迹都保留下来,用透明有机玻璃装箱,布置成一个个展台,珍藏于这间宅子里。平山一个个展台看过去,琢磨那些风神各异的篆刻,查看对这些雅称的解释。譬如“幽巷晚照”,即是石瓦弄晴日傍晚的景象,此篆刻用的是冲刀法,线条爽利健劲,看了下面的注释,清清楚楚地写着三个字:卢润言。原来他是本地产出的书法家,注释里满是长串的溢美之词。平山看着,心里竟然有些说不清楚的酸意。
馆后是一个小小的花园,堆着些亭台楼阁,假山长廊,种着些梅兰竹菊,芭蕉樱桃。平山觅得一处僻静的角落,在亭子里的栏杆靠椅上坐下,拿出手机,拨通了临远的电话。
距离远,信号受影响,临远叽里呱啦说了一大堆,平山听得很累,好歹,平山还是搞明白了。大概的意思就是:石苔青这女孩子不错,漂亮,能干,懂事,孝顺,做媳妇肯定差不了;石苔青是在杭州读的大学,博物馆学专业,毕业后本来可以留城市,自己坚持回的家乡,可惜了;石苔青六岁娘就离家出走了,据说是受不了石瓦全倾家荡产收藏瓦片的怪癖,石苔青和爹相依为命长大,对爹感情深着呢;石苔青大学毕业回家后,趁着省里支持民营力量创办博物馆的东风,经政府牵线搭桥,各方努力,终于在景区开创了“瓦全旧馆”;石苔青和卢润言是邻居,从小跟着学书法,两人有过师生恋,但因为回家乡,这感情没了结果;石苔青迫切需要成个美满的家,这是石瓦全今生唯一的心愿,他觉得对不起女儿;石瓦全已年近七十,为了瓦片,一生辛劳,得了绝症,来日无多……
最后,临远把话说白了,他长叹一声:“平山啊,咱多年兄弟一场,我看你生意做得也不如意,整年晃荡在外边也不是个事儿,找个能过日子的女子成家吧,真的。苔青真的挺适合你,她拓你卖,把生意做大了,挺好挺实在的。哥就说到这里了,当然啦,各人的感觉不一样,还得你自己体会,自己决定!”说完,就撂了电话。
平山在花园里坐到傍晚,游人散尽,天气突然好转,天空露出澄明的气象,一缕粉红色的晚霞横抹在西天,辉映得廊檐上的瓦片更加的深沉肃穆。
这是人生一个重大的决定。可是,平山已经不再是年轻时候的平山了,他知道自己很难在这两天就做出决定来。毕竟,对于苔青,他还所知甚少。这女子的性情究竟如何,容不容易相处,他,一个外乡人能否进到她的心里去,她是否能温柔地待他,他都还一无所知。他现在能做的,只是度过这两天孤独的时光,有个不错的女人陪伴,让假期里有个好心情。至于那些瓦片,壮大生意,呵呵,都太沉重,太遥远了,那是另一个世界,和他易平山相去甚远的世界,他现在还不想考虑,不想走进这扇厚重的现实的大门里去。
这样拿妥了主意,平山就一路踱着回去了。隆冬水乡的薄暮,天空青苍苍的,说不清楚的萧索,四下里渐渐让人感到寒意。
平山走在回石宅的路上,手机来了短消息,是苔青提醒他回去吃晚饭。多像小时候母亲喊他回家吃饭啊,平山的心底涌起了淡淡的暖意。
晚上的菜稍稍丰盛了一些,除了本地池塘里养出来的花鳖,更有自家腌制的盐水鸡,小街摊贩上售卖的狗肉,本地的湖羊。另外,还炒了藕片和绿豆芽。石瓦全的家酿米酒也上了桌,倒在青瓷小盏里,嗅得出清冽的香味。
平山脱了外套,单就在蓝色衬衫外罩了一件鸡心领灰底提花羊绒衫,拉了苔青坐在身边。这米酒看似香甜,后劲却很大。平山似乎回到了家,只管放心喝,开怀喝。喝到八分,微微醉了,平山嘴里的话就多了起来:“苔青,你看,我这上门女婿还……合适?以后,咱也……搞个……天仙配,你织布来我种田,你写字来我卖字……好不好?卖到广州……卖到北京,让全世界的人都来看我们家苔青拓的印写的字!哦,滴水,是滴水写的字。我易平山的太太写的字……苔青,好不好?”
“太太”,苔青不知道在城里晃荡的男人,张嘴老婆、太太自来熟一般,听了这两字,还真就心动了一下。这何尝不是苔青多年来的期盼。自打见过润言太太以后,自从听润言向邻居介绍新人“这是我太太”以后,苔青也盼望着,有一天,有个气宇轩昂的男人能拉着她的手向朋友介绍,“这是我太太石苔青。”难道多年辛苦等来的就是眼前这个男人吗?就是这个既能陪伴她住在滴水宅院,又能帮她一起打点“瓦全旧馆”和拓字生意的人吗?就是这个看上去气度儒雅游历颇广的男人吗?苔青也喝了酒,脸本来已经有些红,如今变成酡红了,心里的戒备与疑虑也渐渐地消散开去。
苔青的闺房原来就在阁楼创作室的隔壁,是二十多平米的一间雅室。靠墙一张两米宽的旧式雕花大床,床侧立着老式四门黑漆衣橱,门上漆着些梅兰竹菊,衣橱旁边置一个红漆花架,搁置一盆兰花。窗下一张红漆带围栏的老式桌子,桌前一把普通的藤椅,很旧了,里面铺一个紫红色的锦缎坐褥。桌上陈列着女孩用的护肤品,一个小小的木质相架,是幼年和父亲、母亲在一起的渗黄的照片。床上罩着玫红色纱帐,本见得有些土气,但因窗前便是楼道,室内采光不足,有些阴暗,所以,反倒增添了些明媚的亮色,见得柔软温馨。床上是明丽的大紫锦缎被褥和睡枕。屋里大概少有男人走动,空气里是阴柔清寡的味道。苔青平素的妆扮应该相当简素,除了女人该有的一点温馨,城市女人通常的脂粉气,竟然嗅不着一丝。甚至一般女人闺房该有的香水、发膏散发出来的香芬气息,也了无踪影。
平山酒喝得酣了,心里嘴里热热的,进门只想拉了女人到床上消受一番,他觉得这屋里的布置、摆设似曾相识。看苔青进门先坐到藤椅里,只好自己坐到床边,拿眼睛蒙眬地看看女人,一边自言自语道“我……今晚不回去了”,一边再看女人的反应。苔青只坐在椅子里,没有吱声。平山的心里一阵窃喜,认为那便是默认了。那就不用急着来,慢慢地、静静地坐着,也好。
窗外是一米宽的楼道,木制的栏杆,栏杆外面是天井,只看到对面阁楼的屋顶,覆压着粼粼的黑瓦。屋顶上面,是冬雨过后澄明透亮的夜空。月亮爬上来了,清水里捞上来的首饰一般,蓝幽幽,滑光光,分外清洁。
平山站到窗前,对着月亮看。他想起中秋在珠江边的那个夜晚,他也这样对着月亮,那一刻,他的手臂上挂着何晓芬明净光滑的手,他对着月亮喊:“何晓芬,你在哪里——”他回头看椅子里的苔青,凝目许久。苔青站起身来,走到他的身边去,伸出双手,抱住他的手臂,和他一起,对着窗外的月亮,静静的,没有言语。四周一片静寂,平山听到自己酒后喉咙里发出的粗粗的喘息声,就像小时候,在饭桌上听父亲喝完酒和母亲唠嗑的光景。那时候,父亲也和自己一样,也没干出什么事业,家里也没什么像样的经济来源,但是,一家人都过得很安心。这种感觉,在颠沛流离的经商岁月中,已经久违了。而眼下,他抬头看月亮的片刻,手臂上分明感觉到一个女人所带来的安定和温暖。他自言自语道:“啊,原来你在这里呀……”苔青抬头看他,他忧伤地笑了笑,俯下头亲吻起来。
醒来,麻雀停在栏杆上叫唤。平山坐在床头,就想摸一包烟出来点上。单身在外边晃荡,渐渐养成了抽烟的习惯,无论身在何处,与其说喷吐出来的是烟雾,不如说呼出来的是忧愁和寂寥。平山无意识地摸出了烟,叼在嘴里,看一眼清清静静的闺房,又放了回去。
苔青还睡在他身边,侧脸朝外对着他。床的三面有着半高的围栏,漆成一幅幅怡红快绿的画屏,与浓紫的锦缎被褥颇对应。晨光把室内照得清清楚楚,小巷里游人的语喧也阵阵沁人纱窗,平山的酒醒了,目光所到之处,昨晚那种静谧温馨的家的氛围也消失了,平山心里孤落落的,一种说不清楚的隔膜。睡在他身边的这个女人,也是陌生的。昨晚的记忆,不过是聊斋故事里的一场艳遇。娶这个女人做太太,长期在远离城市的这乡下水乡的一角生活下去,对于他来说,显然不太可能。平山了解自己的一双脚,它们已经习惯于行踪不定,习惯于流浪江湖了。平山咂摸了一下嘴唇,没来得及及时点上一支烟的嘴唇无聊而饥饿。一种陌生不安的感觉,使他突然想念起城市来了,不错,他的确突然想离开了。
和苔青昨天晚上做了些什么,平山只觉得模糊不清,想不起来了。他想昨晚自己一定激情奔放,深深满足。但是,早上醒来,这种深深的隔膜感也是清晰而深人的。在长期的历练生涯中,对某一特定女人的持续而深远的依恋感消失殆尽,早晨起来,深入骨髓的孤独和荒凉却像四月的野草一样,在心灵的荒野上肆意横生,割除不尽。
本来,昨日,片刻,他以为已经找到了家园,找对了女人,但是,他拿起衣裤穿戴起来的此刻,分明看到自己忙于逃脱的狼狈,这熟悉的状态使他茫然无助、困惑不已。这种感觉是这样清晰而坚定,那就是,他不可能在这里生活下去。他的世界不在这里。城市再荒凉,片草不生,再艰难,腾挪挣扎,也是他该待着的地方。他已经习惯了城市浑浊的空气,浑浊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种虚无中的流浪姿态。如果苔青愿意跟自己离开这里,那尚且可以考虑。但是,这显然不可能。
平山穿戴好,突然又觉得有些抱歉。他回头俯下身,打算亲一下苔青,尽一个情郎的职责似的,没想到苔青正睁眼看着自己。男女之间,情事是不需要语言的。平山早上醒来的一系列动作里,他们之间的感情,温度回落到几点,彼此之间再有无眷恋,苔青不需要睁眼,嗅嗅空气就能知道。此刻,她也知道,他是急着要走了,这一走,不会再回来了。于是,她也坐了起来,麻利地穿好衣服,说:“吃了早饭再走吧!”
平山的心思被人察觉得清清楚楚,他未免觉得有些羞愧。“我请你到外边吃吧,早上烧烧弄弄挺麻烦的。”
苔青想,也好,就跟了他一起朝外走。跨过石门槛出了大门,平山回头看了看门上方“滴水穿石”四个大字。两人折到街面小吃店,点了葱花小笼,蘸着醋,热乎乎地吃下去,那种在外奔波流浪的熟悉的感觉又回来了。
出了风景区,是马路,两边排列着低矮的小楼房,八九十年代的建筑,破败简陋。沿着路面,是一些土里土气的店面,污糟糟的,有的垂着铝合金卷闸门,满是灰尘和泥浆的污痕。
平山回头看了看苔青。昨晚没睡好,大概平时也不怎么注重保养,脸色泛黄,眼底下竟有些浮肿,眼睛也暗淡着,没有神采。和昨日见到的苔青,显然不同了。平山知道自己不好。多年来,不知怎么的,已经形成了这种心态。很难用心珍惜一个女人。也许,他只配得上何晓芬。他需要何晓芬揪着他的耳朵,掏不出二十万投资项目的钱,就将他鄙弃地扔在一边,他才觉得,这眼前的女人永远挂在天上,他永远够不着,永远需要努力,以唤醒生命的激情。是的,何晓芬找不着了,他易平山何尝能够再重新觅着自己。
虽然深深地了解自己心理的病症,眼里流泻的仍旧是那个找不着自己的易平山的目光。再看看苔青的妆扮,再美丽贤淑,毕竟是乡下做派。自然,也算得一块好胚,要遇到真正珍惜又懂得的男人,由里到外地点拨调教,慢慢地育养。但究竟已经错过年纪,要是再早十年,哪怕五年,也是来得及的。这年纪,再是花了心思,毕竟花季已过,如果可巧碰到合适的人,也应该是紧张对付生娃育女这些人生繁重的要务去了。
这样一想,更没了一丝眷念。买了车票,平山急匆匆进了候车室,待找了位置坐定,才浮起一个微笑来,伸出手去跟苔青握手道别,连他自己都为自己的虚伪感到恶心:“苔青,那我这就走了!不定哪天想你的时候还会来看你的!我北京那边还有点生意要处理,你可自己保重!”
苔青一点也没有不舍的意思,女子心里清楚得很,这是平山稍稍讶异的地方。站在异乡的车站里,他恍惚又回到了许多年前。他的家人为他送行的情景。那时候的车站,就跟现在这乡下的车站差不多,那时候的小妹,也这么站在身边,用清朗的眼神看着他。那时候,他还未远游,对家还有浓浓的乡情和眷恋,还没有变得像现在这样,习惯于今夕不知何夕。真像是时光倒流,他又回来了一趟啊。他看到面目全非的自己。
他定定地看着石苔青,知道这一去,意味着从此飘零,不能停留,意味着家园梦想今后不要再提及,意味着他将孤独终老……他哪里是与女人分别啊,分别是和自己告别,和那个过去的传统的自己,来个彻彻底底的告别。
别了,苔青。
别了,平山。
(发表于《西湖》201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