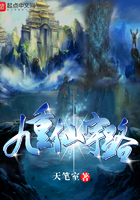一只专供提凉水的楠竹筒,总有饭碗大,约半人高。最上节打了洞,摘一张桐油树叶叠拢来便是塞子。一筒水也蛮重,我和珍珍轮着扛。
我们没留意去时怎样的一路顺风,回来却如过火焰山!毒日烤,石板炙,珍珍和我恰恰赤裸着双足,等于往锅底上跳。挑草丛落脚,可往往又叫刺扎得流血。珍珍一步一声“娘吔”地哭,我也跟着一步步“烫呀”地嚎,就这样哭哭喊喊死死活活挣扎到离街口不远的田湾水井时,已见夕阳西坠了。然而我们绝对不曾料到,竹筒里的水哪里还有半点凉意?简直如同烧热了的洗澡水。
我一时呆住了:这不宣告我们前功尽弃了么?珍珍却若无其事,从我手里接过竹筒,毫不留情地把那水倒得精光,然后灌进井水。
田湾水井的水从哪里流来的?那算什么好凉水?镇上人多半来此洗衣而已。
表伯娘早已望眼欲穿,一把抱住竹筒,哗地抽开叶塞咕嘟咕嘟如同救火如同开闸恨不能一泻千里!她感慨万千地说:“崽崽!有这几口水,你娘的病得好了。”
可是,“那水——”,我正欲道出珍珍的以假乱真,珍珍赶忙伸手在我屁股上狠狠揪了一把,丢过来个眼色,而后咬着嘴唇闷声一笑。珍珍长得并不十分标致,头发里兴许还有虱子。然而正是她那诡诡诈诈匿影藏形的几个鬼动作,似乎倒使我看清了她的了不起之处,而我这个“二表叔”显然是白当了。
《羊城晚报》1993.1.26
布鞋故事
勾腰往床下一看,不禁使人哑然:皮鞋、球鞋、雨鞋、太空鞋、旅游鞋、轻便鞋、保暖鞋、凉鞋、拖鞋……整整齐齐一字儿排开,宛如一队战车接受检阅。
老实说,我并不十分赏识这些鞋。尽管价格不低,款式不俗,跟得上时代潮流。
我只喜欢布鞋。
我也的确还有一双布鞋。
然而我却舍不得穿,穷年累月珍藏在箱子里,白布底子一尘不染,灯芯绒鞋面黑得放亮。
那是母亲留给我的一件她最后的精品。
我无论如何想不起来我究竟穿破了多少双母亲做的布鞋。婴幼儿时的猫头鞋虎头鞋固然已无印象,懂事以后不知怎的就更记不清了。只记得一双脚愈来愈叫母亲难以对付,从半年一双到一月一双直至十天半月,直弄得母亲提着我那些天通地漏的烂布鞋摇头不已地嗔怪:
“你看你那脚罗,硬是像把锉!”
我听了犹如得到最高褒扬,一蹦一跳笃笃笃老远地跑了。
母亲依然拿起剪刀,重新剪样。面料自然是一段新布,买来即可使用。底料是拆开的旧衣裤,但一定是白色的。此外便是糊好的棕壳及布壳。糊棕壳布壳少不了面浆。为了省粮母亲从园里挖来一些魔芋,刮碎了再熬。据说刮魔芋足以把手麻得如同蚂蚁咬。母亲却忍得:还一个劲儿地夸:
“魔芋好哩!它不塞针。”
当然,线和鞋绳同样缺一不可。我们家好像从来没缺过鞋绳,一挂挂酷似唱戏的髯口,我常常戴着好玩。其实那也是母亲用黄麻一绺一绺搓就,搓得她腿上一片紫红。搓满一大挂便用灰煮,再一次又一次地捶,洗,漂到雪白为止。
我最喜欢看母亲纳鞋底。那么厚,那么硬的鞋底,母亲只消将针在头发上擦擦,便轻而易举且又准确无误地一针穿透,纳出的针脚疏密匀整,横斜成行。特别是母亲一手一手拉过那长长的鞋绳所发出的声音,咝咝咝……沙!咝咝咝……沙!实在是情韵绵绵,听来恍如一支古老的歌谣。
有道是“洗手做鞋泥里穿”,一双经母亲千针万线做成的漂亮而干净的布鞋,一上脚不出三五天,准定被我踩得又脏又臭。
想想看,平时的上学,跑步,捉迷藏,打打闹闹,哪能不弄脏鞋子?对这些,母亲并不介意,大不了刷刷洗洗。
偏偏我们这班调皮鬼又想出一些专门鼓捣鞋子的游戏,使母亲委实招架不住。
这种游戏便是踩高跷——从山里砍来两根不粗不细的标杆笔直刚刚齐肩的扎木条,另找一副成钝角的半边枝丫做左右踏板,尔后用韧性极好的鸡屎藤将踏板牢牢捆在扎木条下端离地约五寸高度,就成。如果寻得两颗钉鞋上的泡泡钉钉在扎木条底部,高跷则更完美。
玩的时候,脚踩踏板,两手平伸握住扎木条,人即可离地行走,倘若熟练了还可以小跑。
踩高跷靠的是自己的胆量,其秘诀在于动而不乱。人踩在上面,只要不停地走,一般是掉不下来的。我甚至有本事从上街踩到下街直到学校,踩几里路而不下“马”。
这还算不得英雄。最有气概的莫过于踩高跷撞架。四只高跷两个人,或木条拉木条,或人撞人,或出其不意使个绊子。总之,不惜使出吃奶的力将对手撞下地来,便是胜利。双方常常战得难解难分。
这大约是顶壮丽的时刻,全然不顾谁是真正的牺牲者。只有回到家来才让母亲一眼识破:脚上的一双布鞋成了泥鞋不说,左右贴近扎木条的鞋面已经呲牙裂嘴,皮开肉绽!
这可把母亲惹恼了!操起一把柴刀朝我追来,扬言非教高跷碎尸万段,并且边追边叫:“你你——咋不长出蹄子来!”
事实上,追上了也只见一阵刀光剑影,唬得我抱住高跷不敢动弹。不过这一晚母亲又要熬夜,一豆油灯之下,将破损之处补了又补,不经意间次日还以为又是一双新鞋。
就在母亲飞针走线之时,我躺在暖暖和和的被窝里,多少有点悔恨交加而暗暗发誓:瞧明天吧,不爱惜着穿就不是你儿!
但是,一旦出了大门,往往又故态复萌。
那一天,我们要去区里参加秧歌比赛。镇上距区里二十几里,而且大半是黄泥巴路。按照老师布置,母亲特意为我备下一双新布鞋,让我揣着。另外替我拾掇一双草鞋以方便行走。
快到区里时,恰好有一片小树林,林中流出一线清泉。我们赶快洗脚,换上布鞋。此时,草鞋无疑成了累赘,也就随手藏进路边刺蓬里。
参加比赛的秧歌队还真不少,加上邻近赶来看热闹的人,把个区公所围得水泄不通。一时节,人声鼎沸,鼓乐喧天,彩旗飞扬,那才真叫盛况空前。
轮到我们了!
我们原本训练有素,大家信心十足。何况我们服装基本规整,清一色的布鞋,站出去煞是精神。锣鼓一响,不但秧歌舞步正统活泼,而且舞姿多变,跳着跳着,猛不防插一曲《解放区的天》,边唱边舞,别出一格。尤其我们有最拿手的十三步秧歌,先进后退,收步时两人一伍突然面对面立正,或互相敬礼或打揖或扮个鬼脸,逗得全场人乐不可支,掌声雷动。
最后,我们学校秧歌队独占鳌头,区长亲手奖给我们每人一匹五尺红绫。我们那份高兴劲儿,恨不能像小喜鹊一样长出翅膀,一下子飞回镇上向亲人报捷。
当我笃笃笃跑进大门往母亲面前一站,这才想起——该死!怎么就把刺蓬里的草鞋忘记得干干净净呢?这回可乖乖了,脚下的新布鞋简直一塌糊涂,比草鞋还不如。
我老老实实等着暴风骤雨。
可是,没想到,母亲一手接过红绫,看了又看,摸了又摸,居然变戏法般绾出一朵大红花系在我的腰上,根本没提什么布鞋不布鞋。
《羊城晚报》1993.3.15
亲戚
山里人热情好客,尤其挺喜欢认亲戚。尽管是不经意间走进姓氏相同的农家,主人立刻设酒杀鸡,殷勤款待。席间,便问你排至哪个班辈?应尊为叔公?还是兄妹相称?其氛围之和谐俨然早该是同一门庭的骨肉。
相传老老祖宗的七个儿子即将分赴他乡生息繁衍。临行前夕,老老祖宗设宴饯行,并且赋诗一首:昔年萧老有三妻,关郑吴王七子齐……告诫子子孙孙将来以此为凭确认血缘。
我对宗族观念一向表现淡漠。人之交往,贵在情深意笃,又何必以家族论亲疏?
然而有一回,我却破了先例。
那是十多年前,我以工作组员的身份来到大山顶上那个小小的村落。刚撂下行李,一位筋筋瘦瘦的老妪便前来打听:“县里来的同志姓黄不是?”我边答腔边寻思:老太太怕是告状来了!
“哈哈,去吃酒吧。她也姓黄,要跟你认亲戚呢!”生产队长愉快地加了注脚。他又往深一层诠释:我们这里姓黄的好比马角蛤蟆毛,山下河边那一大寨人也只她一个哩。
看来我注定要跟她走了。否则,难保她不为自己的势单力薄而忧伤。
她住在破旧的吊脚楼上。与吊脚楼成直角堂而皇之立着一栋正屋,是儿子媳妇的天地。两口子在大门外忙着什么,看见陌生人上门,双双白了我一眼,便操起家什搅得鸡飞狗跳。
吊脚楼上倒也热气腾腾,火坑里的柴火烧得蛮旺,三脚铁撑架上搁着菜锅,炒好了的腊肉香气扑鼻。我抬眼一望,正对火坑上的炕架下还挂着两只熏得黢黑的猪后腿。
“快叫舅公!”
还未坐稳,她就不问青红皂白给围在锅边的孙儿孙女定了调。小把戏们一齐吐了吐舌头。我倒觉得,她那张舒展不开的丝瓜瓤似的脸跟我的姑母何其相似。姑母曾经既逗我又考我:黑鸡婆,下白蛋;黑鼎罐,煮白饭。
她家用的当然也是鼎罐。
其实乡下人用铁鼎罐煮饭乃是习以为常,一是倚仗火势猛烈,再就是舀去米汤后提下来反复煨的工夫,使得那饭无菜可饱,远远胜过城里人的盘中佳肴。
这一顿我公然报销三大碗,相当于平时一天的饭量。我无法抗拒她慈祥的逼迫。
第二天,我被熟人邀至邻近寨子小住一晚。翌日回来,队长生气地指着山下,说:“昨天什么日子?唔?怎么可以乱跑?还不快去。”
昨天?糟了!我竟忘了昨天原是正月十五,老人家敢情是等我过节?我返身奔向吊脚楼,但见火坑旁冷冷清清,她面壁而坐,对着四方桌上好大一蒸钵菜暗暗垂泪。
元宵节是团圆的象征,在人们的传统习惯中分量不轻。而她,跟谁团聚?跟锅子鼎罐?火坑猪腿?霎时,我的良知仿佛让自己狠狠咬去一瓣。
“给!都是你的!”她把蒸钵朝我推来。
我决意豁出去了,这一大钵腊肘子一定得干掉,我非得吃到她破涕为笑不可。
……
光阴荏苒,转瞬月余,工作组奉命撤回。我不敢告诉她我要走,仅仅从河边公社供销社买来两斤白糖送到她家里。就这样草草了结了这门“亲缘”,竟连她的讳忌尊号也没问。
我明白,我的不辞而别未免不近人情。两斤白糖也谈不上有什么实际意义。能给她的生活增添多少甜?或者,反而会酿成更大的苦?
从那以后我一直惦着这事,心想应该抽空去看看她老人家才是。然而,一次我竟偶然邂遇她的外孙女,得知有关她的消息……
……老人家前几年就已离开人世。虽被装殓入棺,却因生庚八字与她终极的时辰相克,不能下葬。她儿子这方的人说,不妨到河边讨一棺地吧,毕竟她娘家是河边的。河边她女儿那方的人自然不肯,理由是她婆家本来在山上。一言以蔽之,无论哪一方土地都没有她葬身之处。最后,只准“寄葬”于荒山野岭,任风吹雨打达一年之久。
呜呼哀哉,我的亲戚!
我无端想起我姑母的下葬仪式,是夜,孝男孝女跪于柩前,聆听道士解去死者生前的罪孽。每解一结,道士先生把个令牌拍得炸响,令人心惊肉跳:“抛洒五谷之罪!啪!”“生儿育女之罪!啪!!”……
生儿育女果真有罪么?
《羊城晚报》1993.7.27
山村依然遥远
“清早起,雾沉沉,
雾雾沉沉不见人……”
这是山民们唱的《挖土歌》的起首两句。《挖土歌》唱了一辈又一辈,不管轮到谁,一张口都必须以此开头,足见老祖宗的衣钵可不是能随便乱砸的。
然而稍加考察似乎也顺理成章。
他们只能择水而居,自然是住在大山脚底。先人又不知为何偏偏把可耕之地拓在大山顶上,倘若不趁“雾雾沉沉”上山开工,那才真的要“锄禾日当午”。
乍看还以为他们真会苦中作乐。全村男男女女举锄挖地也就罢了,居然腾出两个人在前面鸣锣击鼓,并且边敲边唱,一时节,几十把锄头碰石头的闷响和着锣鼓的清脆以及唱腔的婉转,给静穆的大山平添几分热烈。
两个唱歌人一是老支书。一是小秘书。一老一少倒也配合默契,你两句他两句,大都合辙押韵,也还声情并茂。时而前唐后汉,时而三国水浒。时而故意盘根,时而互相挖苦。转换灵便,颇具蛊惑。
老支书年过花甲,一字不识,却能说古道今。唱歌时眯眼看远山,脖颈胀出青筋,吊起嗓来一点也不比小秘书逊色。
一日三歇九袋烟,除此而外锣声歌声是不能有半句停板的,一天下来并不轻松。挖地人当然更不存在瞬间的伸腰。皆因大家一条线地向前挖,谁要是手软偷懒,一锄没跟上伴,那他会顷刻落伍,留下的地会让他诚惶诚恐。
还逃不出唱歌人的掌心,当仁不让地编一段不点名的批评词,让其当众红红脸。
但更多的时候是正面鼓劲。比如我和建华。竟然也被老支书捕捉了新事物,大唱特唱什么“斯文不过城里干部,挖起地来如同猛虎……”
这就坑了我们!
本来我和建华已经招架不住,无端让老支书这么一夸,我们只好舍命算了!别人顶多汗流浃背,我们简直鲜血淋漓。等到宣布休息吃烟,我们往下一看,呀!刚刚脱下的外衣已经远远撂在山坡之下。这一口气不提防几乎揭去了半座山的皮。
焉知乐中有多苦!
到第四天,老支书谎称我们要开会学习,其实是怜悯我们手上的血泡。
我和建华也就顺水推舟。但是,闲坐?睡觉?都很自由,又都于心不忍。干脆,不妨为老支书也为我们自己改善一下生活——我们就住在他家。
平时的晚饭,天不断黑不得吃,山民们收工已近黄昏,再步行大约一小时,可以想象黑暗之中怎样的忙于赶炊。充其量不过是大米掺包谷,青菜和水煮,吃到嘴里,只觉是满口的包谷皮直塞牙,甚至尝不出都是些什么菜。
他们却习以为常。
所谓的“改善”并非大鱼大肉,那是城里人的术语。我们只能就汤下好面。米,我们舂了又舂,筛出来差不多像鱼齿。包谷,我们磨了又磨,尽量簸丢那些讨厌的硬壳。事实上,也不叫做糟蹋,他家的猪潲也该改善改善。
至于菜,很使我们为难了一阵子。找来找去,确确只有几棵要蔫不蔫的白菜。翻遍坛坛罐罐,也是清一色的酸辣椒。这样,我们不得不在烹饪上弄些手脚了。
关键在油,支书娘娘比较心疼的东西。她每回炒菜大约只舍得倒出几滴。我们可对不起了,哗地泼下一氹,然后将菜爆得哔哔剥剥。
我们是不是像造反?想到这一层顿觉心虚胆怯起来。我下意识地赶紧叫建华去门口放哨。我担心生活中的凑巧——怕他们提早收工。
谢天谢地,一切依旧。
“呵呵,今儿的饭菜好香!”老支书一端碗就狼吞虎咽。
这就对了!我们指望的就是这句话。可是,借着火光,我们窥见,支书娘娘无褒无贬,一口一口地填她的肚皮,而一张紫铜脸却拉得令人发怵。
我和建华可傻了眼。我们干了一件使主人大为不悦的错事。苦做苦吃,他们才安之若素。
还有什么可说?明儿一早乖乖去听挖土歌吧!
《羊城晚报》1994.11.2
山高·水长
坦白地说,自有生以来我还从没像今天这样焦躁、烦闷、忧心如焚。越想越觉得仿佛身陷囹圄,仿佛坠入万丈深渊而不能自拔。
两万五千块呀!对于仅靠微薄工薪维系全家生计的我,无异于天文数字。
拿着银行送来的催讨通知单,我真的走投无路了!
“谁叫你签字?啊?谁叫你签字?”老伴声声怨恨如五雷轰顶,轰得我晕头转向。
是呵,如果我不签字,肯定不会出现今天的败局。可是,我竟然签了!还自作多情加盖一方鲜红鲜红的印章,似乎生怕弄虚作假。
“你跟谁商量过?啊?跟谁商量过?”雷声隆隆,不绝于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