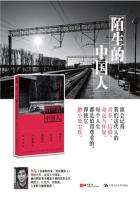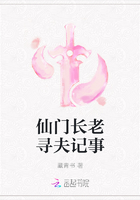越来越迫近暑假了,夏华常常掐着指头在心里计算着婷婷放暑假的日子。盼望着婷婷到来。已是六月里了,一天石三爷下山去了一趟公社,又给夏华捎来一封信。夏华拆开一看,只见署名是舒芸,很感诧异:婷婷的妈妈舒芸还从没给他来过信,她突然来信做什么?他赶紧从头看起。舒芸的来信写得很简短,说是请夏华一定回城去她家一趟,她想见见夏华,同夏华谈谈。谈什么呢?信上没细说。夏华看过信后,不由得在心里揣摸起来:舒芸当然知晓婷婷跟他的事儿的,这因为婷婷以往的信中曾告诉过他。妈妈对此没表示过什么异议,还说夏华是个好青年,非常感谢夏华对婷婷的照料和爱护。于是他想,婷婷妈这次来信请他去。一定是想亲自见见他这个未来的女婿了。
于是夏华决定回城一趟,同时也打算顺便去看一看建平和嫒嫒。他把这个决定告诉了蓉姑和石三爷。蓉姑和石三爷也说他是应该去的。蓉姑说:“华哥,你明天就去吧,桠湾窝的事有我帮你做呢。”
次日,夏华便高高兴兴地下山。当天便从九峰圩坐班车到县城,又从县城坐上火车,途中只用了一天多时间就再一次重回了故城。按照舒芸信中所说地址,很快就找了舒芸的家。
这是个地处近郊的住宅区,只见了绿树掩映,荷塘成趣,曲径遽深,篱落疏疏。一栋栋红色的屋瓦、豆绿色的墙面的独立小四合院落,座落有致地耸立在绿树曲径之间。其环境十分的幽雅宁静。实乃一处陶然颐养的好住处。虽说以往夏华从没来过这个地方,但也早就知道,这一角地方,是本市党政要员们的住宅区。今天有幸来到这里,夏华不禁在心里头想,昔日的婷婷家该是多么的显赫和风光呀!一想到这,他又不由得很有些忐忑不安起来。这心情的产生,一半是因为感于自己出身卑微,跨于这样的环境中,实在不相称。另一半地却是想到虽然自己是应婷婷的妈妈舒芸的邀请而上门的,可舒芸在信里又没有明确地认可他与婷婷的那层关系。夏华担心的是舒芸会爽快地接受他这个从遥远的深山老林里冒出来的“女婿”吗?一会见面时,自己该怎么称呼舒芸呢?能跟着婷婷的叫法叫她为“妈”么?这么叫岂非太唐突了吗?如果不叫“妈”,那么该叫什么呢?哎呀,夏华越想越不敢往下想了……夏华已经站在了舒芸的小四合院门首了。门关着,他不敢伸手敲门,想了又想。最后拿定了主意暂且先行叫“伯母”来着,然后视舒芸的态度和意思再改口。主意一旦拿定,夏华镇定了神思,伸手轻轻地有节奏地敲了几下门。
没一会儿,门慢慢打开了,从屋里出来了一个女人。这个女人鬓发有些花白,眼角处有着明显的鱼尾皱。年纪约在四十多岁到五十挂零之间。眼光庄严而冷漠。看上去虽然已近风烛暮年,但从她那庄严而冷漠的眼光和气质上进一步观察,还足以让人感到身份的高贵和神圣。虽说眼角处明显地有了鱼尾皱,可是肌肤却还白皙,风韵犹存,在她身上,仍绰约显现出她当年年轻时的丰姿来。
不用细细端详,夏华一眼就看出,眼前的这个庄严而冷漠的女人就是舒芸——婷婷的妈妈。虽然年龄与婷婷有着明显的差异,但其脸像和体态都与婷婷酷似。夏华立即很有礼貌地说:
“您大概就是舒伯母吧。”
“我就是舒芸,请问,你是……”
“我叫夏华,接到您的信,便从九峰山赶来了。”
“哦,你就是夏华……快请进来。”舒芸一听面前这英武的小伙子就是夏华,不觉脸上泛起一丝不易让人觉察出来尴尬和迟疑的神色。但这也只是发生在十分之一秒的时间内,即刻便以一副热情的面孔出现,连忙高兴地把夏华引进小客厅。
跨进小客厅。夏华又在舒芸的指点下,坐到靠墙的一个绿绒小沙发里。夏华还真是出世以来第一次走进了这样的一个显赫的官宦人家。他在小沙发里一落坐,不由得仔细打量起这间客厅里的陈设和摆布来。
其实这所谓的小客厅的陈设和摆布也并不算豪华显赫。正面墙面上挂着的是一幅装裱得还算得上讲究的中堂,两侧墙面便是几帧名人书画条幅。中堂下方的两侧是两个古色古香的红木几儿,一个上面是放的一盆根雕的梅花盆景。一个上面搁着个玻璃金鱼缸,清晰可见几尾好看的大尾巴金鱼正在水中嬉游。客厅的一边摆着一张微呈半圆形的长沙发,上罩着一个绿绒面大布外套。进门的这边墙边便是两个也罩着绿绒布套的小型单人沙发,夏华坐下的是其中的一个。两个小沙发中间隔着的是一个也是红木的做工也够得上比较考究的茶几儿。这些东西大都是半旧不新的,唯有窗户那方的一个墙角里的,那个小角柜上摆放那盆绢花和那台电扇,看来是新的。夏华细细地打量了一番后,便觉得这个小客厅显得很有些冷清和落寞。不过,尽管如此,小客厅也还是被女主人打扫得、收拾得窗明几净,一尘不染。涂着腊的地板光洁如洗。夏华自顾一身风尘仆仆,脚上的半旧塑料凉鞋上虽未沾上泥土,但他总觉得与脚下的这光洁如洗的地板很不匹配。此时,他真有些后悔进门时没脱掉它,光着脚板走进来就好了。他想着想着,便不觉就有此不自在了起来。好在舒芸并没介意这些,引夏华进到客厅落坐后,便热情地又是给夏华擦脸,又是沏茶削苹果和往茶几上摆点心。嘴里几乎是不停地说:“婷婷全搭帮你照顾了那么长的一年了,我真不知该如何谢你啊!”
舒芸的热情与和蔼,使夏华倍感亲切,可她这不停口地感谢夏华,却又叫夏华难为情的。他捧着舒芸递给他的一杯香茶,喝也不是,搁下也不是,连舌头都似乎变得直了,被迫陪着舒芸一个劲地重复着回敬道:“您别这样说,其实婷婷也吃了不少苦头的哩!”
用餐的时候。舒芸对夏华的款待更是热情不过,八大碟菜,几乎摆满一张小圆桌。其中好几道菜,夏华是连名字都叫不出来,他从娘肚子里钻出来。至今还从未曾受到过如此隆重的款待。席间,舒芸一边问起夏华在九峰山的劳动和生活情况,一边一个劲儿地劝酒劝菜。夏华受宠若惊,越发不自在,很别扭的。
从见面起到吃完饭的这足有好几个钟头的时间里,舒芸在与夏华谈话中,还一直只字未曾提及婷婷与夏华的关系的话语,夏华于受宠若惊之中不能不同时隐隐感觉到。眼前的舒伯母(当然迄今为止还只能称“伯母”的)对他这个按理该说是准女婿的人,并没有丝毫亲情的流露和表示,似乎只是把他当作一个当以涌泉相报的恩人款待一般,而且似乎在热情中总透着一种经过了掩饰的虚伪来,夏华的一颗心不由得一直悬着放不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