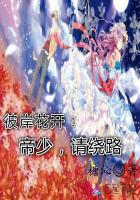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罗丹应征参加了国民自卫队。他想像着向柏林胜利挺进的场面,但却被派到后备军团,任命为下士,原因是他能写会念。露丝则靠给军队缝衬衣挣钱来维持全家的生活。转年冬天,双方签署了停战协议,他被作为病残处理,离开了军队。
当他回到家里,发现妈妈已因天花和饥饿而卧床不起,爸爸的视力大为恶化,仅能勉强走路。为了全家人能吃上饭,罗丹不得不再次辞别家人和年仅5岁的儿子,到中立的布鲁塞尔的卡里埃·贝勒斯的工作室去工作。卡里埃是法国雕塑家,注重形式优美但缺少创造精神,作品有《爱情与友谊》《朱庇特与月亮女神》等。他因给一些大人物塑胸像而出了名,订货单滚滚而来,他自己应付不过来,就雇佣了些助手,按他的风格进行雕塑,然后在作品上刻上他自己的名字。这件令人痛苦的工作罗丹在战前已干了三年,迫于生计,他不得不继续下去,因为卡里埃付的工资比别处都要高。
1871年3月,巴黎市民不堪忍受对德战争的失败以及随之而来的饥荒,组织了巴黎公社起来反抗,希望重演1793年那次成功的革命。于是在巴黎公社社员和拿破仑三世的凡尔塞军队之间爆发了一场血腥的巷战。
传到布鲁塞尔的消息令人毛骨悚然。罗丹听说饥馑比德军围困巴黎时更为严重,更有谣言说巴黎已被夷为平地。罗丹想冲回家去看看,但当时不允许任何人进入巴黎。
罗丹终于从一封辗转托人带来的信中知道了家人的消息,家里的人还活着,他的那些塑像也被露丝保存得安然无恙。但是饥饿正在折磨着全家人,妈妈已奄奄一息。
痛苦和失望折磨着罗丹,他的工资只够他维持生活的,没有什么钱可以寄回去,全家人的饥饿终于使他想出了一个办法,他在自己刚刚塑完的一个女性塑像底座上刻上了卡里埃·贝勒斯的名字。如果说他是个伪造者的话,从某种意义上讲,卡里埃·贝勒斯更是个伪造者,然而卡里埃·贝勒斯的名字却比罗丹的值钱。
他把这尊塑像偷偷拿出去卖了75个法郎,将钱寄到家里去。然而,他也因此被解雇了。
罗丹像发高烧似地在布鲁塞尔转来转去,不知该干什么好。然而他发现到处走动增加了他的食欲,于是他干脆整天坐在屋子里冥思苦想。就在他愁眉不展的时候,他在卡里埃·贝勒斯工作室里的同伴约瑟夫·范·拉斯布尔找到了他,邀他合伙做雕塑买卖——罗丹雕塑,而范·拉斯布尔找买主。罗丹如捞到了救命稻草一样,开始拚命地工作。在范·拉斯布尔的建议下,罗丹把露丝从巴黎带来的《塌鼻人》送交1872年布鲁塞尔沙龙。作品被接受了——这是他第一件被沙龙接受的展品,尽管不是在法国。但是,这个雕像并没有引起什么注意。他决定塑一件大型作品,但他既无金钱又无时间,充满激情的创作仿佛离他越来越遥远。他心里充满了悲哀,变得越来越烦躁、苦闷。
善解人意的范·拉斯布尔建议他出去走走,并赞助了他100法郎。于是,他只身游历了荷兰和意大利,朝拜了他心仪已久的两位先辈——伦勃朗和米开朗琪罗的作品。这次游历使罗丹重又寻到了创作的激情和为艺术而压倒一切的决心。
在阿姆斯特丹国家博物馆,他尽情地欣赏着那些他从未见过的伦勃朗的佳作。伦勃朗所生活的那个时代曾使他蒙受耻辱,他被宣布是个破产者,是个失败的画家,然而他依然不折不挠地作画。伦勃朗没有逃避人与命运之间的悲惨斗争,他揭示了生活的腐朽,揭示了死亡和毁灭的必然——而毁灭常常比死亡降临得更早。最后,这位画家逐渐变得只关心人物的内心,并把精力集中到刻划人物的面部。在他的画中,人物的脸常常只在一束微弱的光线下在黑暗中显现出来。在古典主义绘画大师中,伦勃朗对光的捕捉及运用是最好的。他的绘画技法对后来的画家起到了重要的影响。
伦勃朗的作品使罗丹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设想。几年来,他终于又一次感到一种压倒一切的冲动,促使他投入新的创作。
而在意大利的佛罗伦萨,米开朗琪罗的原作又给罗丹以前所未有的震动。他在《大卫》及五个未完成的囚徒之间转来转去,完全给迷住了。米开朗琪罗是文艺复兴时期的巨匠,他一直工作到89岁,日以继夜地雕刻肉体也是心灵的史诗。他早期的杰作是《大卫》和《摩西》。大卫是圣经旧约里的人物,年轻时是一个牧羊人,依赖他的英勇把非利士军中的巨人哥利亚用石子击杀,为以色列人除了外患。在他和哥利亚决战之前,所罗王赐给他盔甲,但他穿不惯,脱去了,所以米开朗琪罗塑的大卫是全裸的。他立得很直,骄傲又泰然,身体的重量放在右脚上,头转向左侧,通体弥漫着少年的精力和无畏。摩西是率领以色列人走出埃及的民族英雄。他接受神谕,把戒律传给他的子民,为这个流亡的民族制定了道德、法典、礼仪、生息的节奏及文化的框架。他的像有如一道生动的风景,卷发如跃动的焰苗,而长须在胸,卷腾如急湍,两眼如炬,头顶两角,巨伟而威猛,是一个呵护并鞭策一个民族站起来的神灵形象。这两座雕像充满激情,而且造型完美。后世的浪漫主义者醉心于这里的奔放,而古典主义者折服于造形的精粹。
到了晚年,米开朗琪罗已不再满足于这两种平衡,宗教热忱最终打破了古典形式。为了达到尽情表现的目的,作品的完整与否已不是他所考虑的。中年时雕的五座囚徒都未完成,似乎他有意不去完成,使这些埋在大理石中的男性身躯成为心灵在物质中挣扎的象征。而80岁以后,他的两座“圣母哀子”像都不曾完成,有的部分已经加了精细的打磨,而有的部分还在毛胚状态。后人很难评说这粗糙的石面是有意保留的呢?还是无意留下的。因为对比之下,粗糙与模糊产生一种“不可说”的悲剧效果。
更让罗丹感到触动的是,米开朗琪罗好像已经忘却了雕像的社会功能、外在形式,忘却要放置在什么地方——神从神龛走下来,英雄从基座走下来。于是人们看到他们额头上的阴郁,颊边的泪痕,胸前的伤口,脚底的肿泡。人们会像一个母亲抱住他们,抚摸受难的肉躯,而这肉躯即是他们痛苦的灵魂。对罗丹来说,米开朗琪罗是一个雕刻家,更是一个打石头的圣徒,他在大理石里凿出哲学与诗句。
米开朗琪罗的作品使罗丹激动万分,他感到自己必须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作品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推动他马上返回比利时,回到他的工作室去。
罗丹崇仰米开朗琪罗,但崇仰和因袭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在对大师作品的迷醉中,罗丹并没有丧失自我,他要塑出独属于罗丹的东西。18个月后,罗丹的《青铜时代》在布鲁塞尔完成了。它同《大卫》一样,是个站立的年轻人的塑像。但他不是英雄,而是一个刚刚萌醒的青年。这个同真人一般大小的塑像,头微仰,双臂自然地举起,右腿微曲,眼睛还没完全睁开,尚未看到外面的世界,没有看到敌人与爱人、花丛与陷阱。他的四肢已经丰满,已拥有足够的力量和热情,但在迈出第一步、踏上征途之前,仿佛还不免有些迟疑和彷徨。这是人类苏醒的姿势,是人类踏上征途前的心态。
《青铜时代》被布鲁塞尔沙龙接受了,然而却由于其过于真实而被诬为是用真人的身体浇铸而成。1877年秋,罗丹返回了阔别六年的巴黎,站在凯旋门下,罗丹异常激动,他想像着自己的作品能为祖国所接受。
然而,在巴黎,《青铜时代》受到了同样的遭遇。巴黎一家报社重复了布鲁塞尔报刊的诽谤,指责这尊像是用活人的身体浇铸出来的,并攻击这尊像“庸俗、放肆、下流”。
一时间,这个“用真人浇铸出来的”雕像成了人们争先恐后观看的对象。在展览厅里,罗丹几乎被大喊大叫的人挤倒,然而人们来到这儿只不过是想见识见识这个伤风败俗的人体像。罗丹渴望得到公众的承认,但得到的却是辱骂。他成了骗子,成了欺世盗名的人。沙龙评选团被这一轰动一时的丑闻弄得十分尴尬,便命令把《青铜时代》搬出展室。
无端的毁谤使罗丹十分气愤。他一再解释和声明,甚至交出了模特儿和创作过程的照片,但遭到的是更多的数不清的麻烦。而与此同时,以马奈、德加等为首的印象派画家的第三次联展也正遭受猛烈的攻击。最后,在美术界朋友们的帮助下,美术院同意由五名雕塑家组成评审团,让罗丹在评审团面前即兴创作一个雕塑,以确认罗丹的真实功力。
这是罗丹多年来第一次进行即兴创作。他想起了那个叫佩皮诺的意大利人,想起了他那健美而典雅的走路姿势,于是他开始塑这个意大利人。他自如地塑着,人物的结构源源不断地从他的想像中涌现出来,他忘了还有个评选团在场,忘了时间,发疯似地创作着,直到把躯干和两腿塑完时才停了下来。茫然的心理和遭受委屈的感情都随着创作的激情消失了。这尊看似未完成的塑像叫《行走的人》:一具残躯,没有头,也没有两臂,迈着大步,毫无犹豫地勇往直前。好像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又好像全无目的。“走”,就是它永恒的姿势。走,走,带着无畏,带着振奋,也许也带着惶恐和不安——那是人的步伐,是全人类的步伐!
审判通过了。1880年,《青铜时代》和新塑的《施洗者约翰》一起被沙龙接受并展出。《施洗者约翰》获得了第三名雕塑奖。罗丹的作品第一次得到了公认。
《施洗者约翰》是以《圣经》中耶稣十二门徒之一约翰为原型的一尊立像。传说约翰是耶稣最喜爱的门徒,晚年被流放于拔摩岛。《圣经》中的《红翰福音》和《启示录》据称是他所作。
罗丹以每天十法郎的报酬雇佣了那个叫佩皮诺的意大利人为模特儿。他让佩皮诺光着身子在他的工作室里不停地走来走去,而他则紧张地观察以捕捉各种他需要的姿势。佩皮诺常常走得筋疲力尽,罗丹就不停地鼓励他:“你会成为一件杰作的,我们都需要耐心。”
一年以后,《施洗者约翰》才完成,然而他暂时还没有钱付给佩皮诺几百法郎的工钱。可佩皮诺像《青铜时代》的模特儿一样,为自身的复制品所迷而显得心甘情愿。
《施洗者约翰》也是一个裸体像,他高扬着头,张着嘴,任头发披散在脖子上,表情庄重而威严,充满着一种崇高的信念。他迈着大步,仿佛是从大自然中,从广阔无垠的荒原中走出,然而又远远超出了大自然的生命。他浑身都为信念所燃烧,人们仿佛能听见他在旷野中的呼喊。
《施洗者约翰》和《青铜时代》同是罗丹青年时期的代表作。《青铜时代》是人类刚刚醒,还带着出发前的犹豫,而《施洗者约翰》则是大无畏地向前走着了。这两尊塑像是雕塑家开始走上艺术道路并要大步流星披荆斩棘地开拓自己的事业的心态的表露,只有少壮派的艺术家才能雕出这样年轻振奋的作品。而他晚年,则雕塑不朽的《思想者》,沉郁忧虑地关注着人类的思想者,那也是晚年罗丹终其一生对社会对人类所倾注的关心和思考的结晶。
然而,《施洗者约翰》虽然不如《思想者》那般沉郁内敛,给人以思考的力量,却已开始体现了罗丹中年以后的作品中流露得越来越浓重的宗教情绪和悲剧感。一个在荒原上大步走着的人,一个在风雨中不断求索真理的人,它的孤独和悲壮给人以力量。1880年沙龙展览的成功,使罗丹声名远播。法国政府邀请他为正在拟建的装饰美术博物馆雕塑一个大门,题目由罗丹自选。罗丹选中了文艺复兴时期的大诗人但丁的《神曲》中的《地狱篇》为蓝本,打算建一座《地狱之门》。政府为此在大学街给罗丹拨了一间明亮而宽敞的大工作室。罗丹艺术生涯的鼎盛时期开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