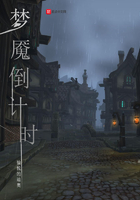生命总是充满着磨难。生活上的艰辛并不能摧毁罗丹追求艺术的决心,可精神上的重创却差一点断送了罗丹的艺术生涯——玛丽死了!他最亲爱的姐姐终于没能逃脱失恋的痛苦折磨,郁郁病故。22岁的罗丹无头像法接受这残酷的现实,他再也没有勇气去面对工作,再也无法进行热爱的雕塑了。玛丽虽然是一个普通的年轻女孩,但她在精神上与罗丹是相通的。她一直是他艺术追求上最有力的支持者,是他的知己、他的慰籍,是他在生活中惟一可以信赖的人。玛丽的死对罗丹来说是前所未有的重创,他无法再呆在家里,这里的一切都会引起有关玛丽的回忆。罗丹决定出家,他没有勇气去向勒考克辞行,他知道他肯定会发怒的。1862年的冬天,一个下雨的日子,罗丹开始了在圣雅克街上圣餐长老会的修道院里的修道士生活。修道院院长艾玛神父,是一位尊严的、享有学者盛名的年长教士。他那宽宽的额头、沉思的双眼和刚劲的下巴,具有罗马人严峻的特征,但当他微笑时,脸上好像焕发出某种光泽,显得神采奕奕。他同罗丹打过招呼后,问他:“你是位雕塑家吧,奥古斯特兄弟?”“神父,我只不过是个学生,”罗丹不安地动了一下说,“艺术对我来说已经无所谓了。”
艾玛神父睁大了眼睛:“如果上帝赐予一个人艺术才能,他就不能草率地将它抛弃。一个人可以同时为美和上帝服务。菲利波兄弟和巴托洛米欧兄弟就曾同时为两者服务,他们得到了荣誉和盛名。你慢慢就会知道你是不是适合当个教士,不管怎样,一个人不应当把出家看作是逃避现实,而应当看作是履行职责。”事实正如艾玛神父所预言,罗丹虽然努力遵守教规,希望在苦行和顺从中、在孤寂和祈祷中寻求安慰,但他心里越来越清楚他无论如何也摆脱不了雕塑制作的欲望。
他的苦闷被艾玛神父看在眼里,他给罗丹拿来了新版的但丁的《神曲》,上面有多雷的蚀刻画。多雷的蚀刻画有一种奇特的魔力。奥古斯特·罗丹坐在修道院的图书馆里,画着自己想像中的《神曲》,比多雷的画更优美,更富有感性,几个月来,他第一次感到满足。
艾玛神父看了一眼他的画,说道:“好!好!你没有白费时间。”他敏感地意识到罗丹需要用他的手进行创作,因此安排他到花园里去干活,并给他拿来粘土,罗丹非常感激和理解。就在这个花园里,罗丹给他所崇敬的艾玛神父塑了一个胸像——这是罗丹签了名的第一件作品。这个胸像没有美化艾玛神父,就像艾玛本人一样干而瘦弱、硬而优美、平凡而坚定、严肃而仁慈,瘠薄的面孔紧绷在突起的颧骨上,两颊被太多的忧患拉扯得隐落下去,额骨高而阔、眼睛大而明亮,流露出爱的凄悲神色。它显露出艾玛神父宗教感很深的性格,似乎他专为了走艰难坎坷的道路而来到人间的。当艾玛神父看到自己的胸像时,他说道:“这是个很好的塑像。它使我看到了我普普通通的长相,使我免于自负,但它又充满了感情,使我感到我是个人,真正的人。”
艾玛神父明白修道院不再适合罗丹呆了,罗丹的生命在他的艺术创作里,他劝罗丹还俗:“你现在需要的不是安慰,而是信仰和希望。”
几天之后,罗丹带着对艾玛神父的深深敬意离开了修道院,他在那里呆了一年光景。
不能忽视罗丹的这段修行生活,短促的修行生活培养了罗丹的宗教情操。激烈的宗教使他对生命、对艺术都看得更为严肃。宗教感对他以后的创作过程起着重要的影响,引导罗丹一次一次地倾向人生悲苦情感的体验,使罗丹的作品,从整体来看,是悲剧的内省。
献身教会有一定的象征意义,忽略这一点,就不能透彻地了解罗丹,也就不能充分了解西方文化许多关键的地方。中国人很容易嘲笑西方人的宗教信仰,嘲笑他们的天使长着鸟翅,神长着大胡子,其实应该说,西方人把人提升到神圣层次去,正像我们给云烟、林泉赋予崇高神秘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