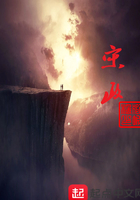雍肃殿里只燃着数盏灯火,光线略显昏暗。皇上将内臣、宫女悉数撵走,留下他一人,举一爵黄酒在手,脸上那分少年英主的豪气不复存在,些许的苦涩随目光流淌出来。凭窗远眺,想要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却发现今夜本是朔日,窗外唯有无边的黑暗。
“无月为朔,满月为望”,由朔到望,由望到朔,一月一次轮回,天道亘古不变,从无到有,从有到无,周而复始,生生不息。
等到下次满月,梦想或许成真,只是此时此刻,徒剩一声叹息。
朱祁铭匆匆入内,就见皇上猛然转过身来,未启齿而先含笑,脸色亲和如斯,令朱祁铭不敢卒信。
“三弟,免礼,快快入席。”
三弟?朱祁铭一凛,茫然中衣袖被人牵着,入席落座,淅沥的酒滴声随笑声飘入耳中。
“朕知道,太皇太后嘴上不说,想必心里定是盼朕叫你三弟,朕乐意叫你三弟。”
诧异定在脸上,身形似已凝固,但见近身处烛火摇曳,僵硬的身子直直立起。
“臣不敢越礼逾制!”
“坐坐坐,今日朕亲为你斟酒,全当是家宴,你再不可多礼。你如今孤身一人,而朕与你又共有一个皇祖母,自会视你如亲弟,此事便说定了,有旁人时咱们是君臣,私底下咱们是兄弟。”
被天子唤作三弟,无异于在年少的躯体上加了一道金钟罩!真是世事无常,不知不觉间,竟突然迎来了梦幻时刻。
经天子相邀,朱祁铭举爵近唇,半爵黄酒入喉,清爽的滋味沁心入脾。
“哦,朕已命人拟旨,封那个卢家村的卢方氏为一品夫人。其实朕并不想食言,拖了数月之久,只因朕有些犯难。封内夫人的定例仅限于紫禁城内,用在皇子、皇女乳母身上,而今你是朕的三弟,封卢方氏为一品夫人自然不算破例。”
想天子一言九鼎,既有许诺,便总有兑现的一天,拖延许久的真实原因未必如天子所言,在于对定例的考量上。不过,这份荣耀虽然迟来,但总算落在了方姨头上,有这道荣耀护身,愿方姨好人一生平安!
朱祁铭想要起身谢恩,却被皇上按住了手臂。
“授那个姓荀的庶民以员外郎虚衔,此事也议定了,届时朕命人一并前去宣旨。朕记得锦衣卫那两个百户好像一个姓牛,一个姓方,也不必授什么副千户的官职了,直接升任千户,调入羽林右卫任职。至于徐恭嘛,还得等等,朕一定善待于他。”
但见袖影一晃,皇上再次举爵相邀,朱祁铭双手捧爵,念一帮救命恩人总算有了着落,心中顿感释然,只是,皇上给了他们厚赏,而自己对皇上似乎还欠一份厚报。
“今日你在奉天殿立下大功,朕赏你黄金百两,珠宝、金绣、锦绮无数,朕命御用监着人领着你去看看,由着你挑。”
给了大赏,施下大恩,接下来总该谈点大事吧?一番觥筹交错之后,就见皇上脸色微沉。
“瓦剌太猖獗了!朕不愿再忍气吞声,朕要效法汉武帝,平定胡虏,让我大明的声威远播漠北!朕与一般勋戚、都督商议好了,招募民壮,训练虎贲之师,以三年为期,一举荡平鞑贼!”
朱祁铭胸中蓦然升腾起一股豪气,但只是片刻而已。想当年汉武帝十六岁登极,先是重用骑奴卫青,后拜十九岁的霍去病为骠骑大将军,三个血气方刚的年青人成就了一番不世伟业。再看如今大明的庙堂之上,除了天子年少,一眼望去,处处都是暮气沉沉,还有那帮养尊处优的太平将军占着高位,这种老而僵化的体制,岂会给卫青、霍去病那样的人以脱颖而出的机会!
何况,皇上无法乾纲独断,纵有慧眼,也难以力排众议。
那边皇上有些激愤,“可是,辅佐大臣处处掣肘,朕哪像个天子,简直就是一个须时时听命于他们的无知小儿!”
“陛下”
“叫皇兄,再不从命朕可是要生气的!”
“是!皇兄,待到明年,皇兄便可大婚,大婚之后就算成年了,天子成年亲政,这是水到渠成的事。”
“大婚?朕大婚也不是朕说了就能作数,何况即便大婚,朕也摆不脱某些人的阴影!”
阴影?朱祁铭骇然,想皇上对亲政的渴望该有多么强烈!但是,在可预见的将来,辅佐大臣的头衔是很难被摘掉的,或许只能听从于天命,待年迈的辅佐大臣先后故去,皇上才能迎来自己做主的崭新时代。
皇上自己做主?不,那也极难!
皇上脸上浮起笑色,“郕王怯弱,朕指望不上他,幸亏朕还有你这个三弟,你敢与帝师辩论,还敢只身赴奉天殿应战,足见你有非凡的胆识,朕知道,你做事胸有成算,当年那道周公瑾再世的名头绝非浪得虚名!孙周二人异姓者尚且亲如兄弟,朕与你本是自家兄弟,更应该同气连枝,朕期望你助朕一臂之力。”
圣意太深,分量太重,朱祁铭哪敢贸然应承什么?只是定在座上发怔。
“你成年后赴藩,此事已定,但朕不想让你赴藩,若无人掣肘,日后朕留你居京并非难事。”
能给的都给了,不能给的也在想办法给,君恩深似海!想皇上如此倚重自己,无非是源于朝廷之上真无人可用,百官无不唯三杨马首是瞻。可是,朱祁铭还需等待一个沉重的答案。
皇上面色转趋凝重,“当初,三叔王虽是因病而薨,但朕每每念及三叔王蒙冤一载有余,便深感愧疚,若非杨士奇、杨荣他们苦苦相逼,朕岂会为难自己的亲叔!”
此事终于从皇上口中说出来了,看来,王振所言非虚!朱祁铭猛然起身,就想先谢恩,领命一事留待日后再说。
突然,殿外响起小黄门的劝阻声,片刻之后,只见三杨先后入内。
杨士奇、杨荣直接无视朱祁铭的存在,只有杨溥朝他点头致意。
三杨在皇上面前排成一排,躬身施礼。
“陛下与勋戚议及招募民壮一事,消息传来,举朝哗然!敢问陛下,如今天下太平,何故要起兴兵之意?”杨荣微微垂首,面色与语气都有点咄咄逼人。
朱祁铭赶紧离席避到一旁,转身瞧见皇上略显不安地站起身来。
“瓦剌欺人太甚,朕忍无可忍!当年我太祖洪武皇帝从故元手中收复华夏江山;太宗永乐皇帝五伐漠北,令鞑贼闻风丧胆;皇考宣德皇帝御驾亲征,剿灭犯境的兀良哈贼人,朕的列祖列宗何曾惧过鞑贼!朕决不做蒙羞忍辱的懦弱昏君!”
杨荣跨前一步,皇上微微后退。
“陛下,不就是瓦剌使臣多来了近百人吗?他们未受教化,不知礼数规制,此为细枝末节的小事。兵者凶事,如今百姓富足,刚过了十余年的好日子,无不盼和平,大明怎能轻启战端!”
穷的时候说打不起仗;富的时候说要过好日子,不愿打仗,这是什么逻辑?朱祁铭不禁摇摇头。
那边皇上甩甩衣袖,“难不成要等到瓦剌打上门来了,大明才仓猝应战么!”
“陛下应做仁君,战端一启,生灵涂炭,非百姓之福。只要小心周旋,大明不难与瓦剌和平共处,再说,即便瓦剌真有一天兵临城下,可在京城四周坚壁清野,集结重兵固城而守,凭瓦剌那点兵力,自会无功而返。”杨荣道。
坚壁清野是正统朝两代文臣常挂在嘴上的所谓谋略,殊不知坚守京城,北境的黎明百姓怎么办?弃百姓而不顾,皇上又怎能称得上仁君?饱学之士如何称得上贤臣?而且,坚壁清野本身就是亡国之策,对此,朱祁铭早在镇边城时便已领悟,但他此刻不便妄议国事。
焦土抗战,受蹂躏的是自己的国土,遭殃的是自己的百姓,未战便先败三分。可惜,太平日子过久了,别人不打上门来,是唤不醒梦中人的,就算哪一天真被打醒了,多数人依然心存幻想,庙堂之上根本就凝聚不起坚定的战争意志,只能在不断的退让中走向衰亡。
唉,但愿皇上是汉武帝那样的英主!朱祁铭暗叹一声,就想辞去。
“陛下。”杨士奇开了口,点出了问题的实质,“如今府库入不敷出,招募民壮招少了不济事,多招势必要增加赋税,就怕百姓不堪承受啊!”
不,应该是小民不堪承受才是!大明很富,但小民很穷,这是大问题。明代士大夫享受傜赋优免政策,免的是徭役,优的是田赋,并非全免,而是按品秩免去家中若干丁口的田赋。其实,天下万官多是大地主,加上勋戚、皇室宗亲,只要这些人拿出一成的财富,足以养活一支庞大的军队,灭瓦剌并不难,但他们不仅不肯破财,还对预期中的加赋万般抵触。
他们倒是有办法将增加的税赋转嫁到小民头上,但这个时候他们不敢,小民太穷了!小民造反那可是要了士大夫的命,所谓“天街踏尽公卿骨”,穷人造反必将一切等级秩序全给砸个稀巴烂!而异族入侵就不一样了,只要肯放下面子,可易主而侍,士大夫还是士大夫,豪户还是豪户,只不过换了个皇帝而已,当年崖山灭宋者,不就是宋之降将么?
于是,老百姓不堪加赋就成了一个真实的谎言!
还是圣人说得好,不患寡而患不均,可惜孔子心目中的大同社会只停留于理想之中,难以实现,故而如今的大明虽富甲天下,但可用于战争的财力恐怕比瓦剌多不了多少,何况瓦剌能够“因粮于敌”。
面对三杨的苦口婆心,皇上似乎还不想妥协,“朕自有主意。”
杨士奇深沉的脸上略现诧异之色,“治国并非儿戏,如此大事,不经廷议,何以施行!若陛下笃意如此,臣请致仕!”言毕取下头上的乌纱帽。
杨荣、杨溥摘了帽子,附和道:“臣请致仕。”
三杨若不明不白地挂冠而去,他这个天子还怎么当?皇上一脸的沮丧,“朕闲来无事,找几个人议议此事也不行吗!”
杨溥终于站出来当和事佬了,劝杨士奇、杨荣二人离去。
杨荣这才狠狠瞪了朱祁铭几眼,转向皇上道:“帝王大节莫先于讲学,讲学之要莫过于经筵,明日宫中即有经筵,请陛下早些歇息,免得到时候误了时辰。”
三杨走了,皇上瞬间失控,一脚踹翻膳案,“哗”的一声,杯盘碗筷洒了一地。
朱祁铭适时告退,出门后,回首一望,就见王振进了雍肃殿,朱祁铭有些恍惚,觉得王振的背影怎么看都像是黄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