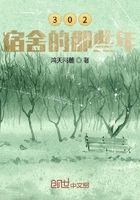一阵炮火,有一颗榴弹落在房顶上,震得屋顶窸窸掉土。黄正诚吐着嘴里的尘土,一阵阵寒战像蚂蚁般在他背上爬。“敌人快要进屋了!”他朝话筒里喊完最后一句话,推推架在鼻梁上的金丝眼镜,恶狠狠地朝少将参谋主任顾铁翻了一眼,低声说:“完了!我们快走吧。”顾铁递上来一件士兵服。黄正诚哀叹一声,微微打着寒战,接过士兵服。
枪声渐渐稀落,火炮的轰鸣已经停止。
周希汉火急火燎地询问着:“捉到黄正诚没有?”
吴效闵回答:“没有。据俘虏讲黄正诚被炸死了。”
“不可能。”周希汉说,“你们大炮、炸药响的时候,我还听见黄正诚和罗列在报话机上说话呢。”
“我们一定好好搜索。”
敌副旅长戴涛、参谋主任顾铁已束手就擒。摆在旅部大院里的四门“蒋先生”,一“言”未发,呆呆地望着它们的新主人。战士们拍拍山炮的脑袋,打趣地问俘虏:“这么好的家伙怎不放啊?”俘虏也不掩饰:“你们一下子扑上来,还往哪儿放?”
战士们到处搜索,把一些穿马靴、指挥官模样的俘虏都讯问遍了,就是找不到黄正诚。东方已经露出鱼肚白,被炸毁的村落飘着一缕缕残烟。部队已经撤出战场。吴效闵带着几个参谋,来到俘虏集中的一片小树林。一夜鏖战,俘虏们个个蓬头垢面,东倒西歪地斜靠在树底下,有的还呆呆地望着陈堰村,眼泪在脸上淌出两道白印儿。十几架敌机吊丧似的在陈堰村上空盘旋了一会儿,飞走了。
吴效闵想,黄正诚不死的话,他能插翅飞走不成?他又一遍遍审视着俘虏的面孔。
有人胆怯了,朝别的俘虏背后挪动。
“你是干什么的?”吴效闵盯住一个上身穿士兵服,下着呢裤子,脚穿马靴的人。
“书记官,我是书记官。”那人扶了扶眼镜,低着头,忽然解释:“这裤子和靴子是去年我在西安结婚时朋友送的。”
“是蒋介石送的吧?”
“不不……”
“你是黄正诚!”
黄正诚情知无法再隐瞒,缓缓站起来,推推眼镜,沮丧地说:“我要见你们的陈赓将军。”
“我去和他谈谈。”陈赓在派人送给黄正诚两条烟和一件衬衣,又派两位科长和黄正诚交谈后,做出决定。
“你不要去,我们把他找来,你教训教训他就是了。”想到黄正诚那股傲慢劲,两位科长心里都有气。
“你们别这么‘革命’好不好?在官雀、陈堰把他的部队全部歼灭,他也被俘了,教训够大的了。现在是要按照党中央、毛主席的俘虏政策,宽待他、教育他的时候,我必须亲自去和他谈谈。”
“司令员,他穿着大皮鞋,踢你一脚,或是举起凳子……我们跟你去。”
“你们别跟。”
“叫警卫员跟着你。”
“不用。”
两位科长还是悄悄跟在后面,以防不测。
陈赓走进小院,推开房门,看见黄正诚坐在那儿,身子后仰,一动不动地默默呆想。他的领口敞开着,两腿交叉,眼睛瞪着屋顶,撅着嘴唇,吸着一支香烟。
黄正诚看见进来的是陈赓,那目光在十分之一秒内起了变化。起先是感到突然,然后明白了,呼地站起来,站得笔直。
“你坐下来谈。”陈赓用手示意。
“老大哥不坐,我不能坐!”
“都坐下,都坐下。”陈赓先坐下了,“你有什么问题需要我帮助解决吗?”
黄正诚僵硬地挺直身子,做了个深呼吸,说道:“我们这个部队在那边是很有名望的,胡先生当过这个师的师长。请贵军不要发布这个新闻,以免使胡先生过于难堪。”
“谁叫他进攻我们呢?还有什么问题要解决?”
“我的内人在西安,能否把我的情况告诉她?”
“我们尽量设法帮助你办这件事。你把她的住址姓名写下来。”
“谢谢老大哥。”黄正诚深深吐了一口气,双手凹成钵形,将信将疑。
随着每一下呼吸,屋里的紧张气氛逐渐减少了。
“这个仗不是我们要打,是蒋介石坚持法西斯独裁,主动挑起来的。”陈赓转过话题。
“老大哥,这话我可接受不了。”黄正诚微微弯了弯腰,做了个完全不符合军人身份的举动,喃喃说道,“他那么大年纪了,还要搞法西斯独裁干什么?”
“我跟你讲讲他的历史。”陈赓耐着性子,口气却特别坚决,“黄埔军校是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蒋介石那个时候伪装革命,靠黄埔军校起了家,很快就背叛了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抛弃了国民党中的左派力量,对在东征和北伐中出过大力的共产党人实行血腥的大屠杀……”
黄正诚有点不自在,似信非信,茫然无措,不住地抬头、闭眼、张嘴、翘鼻子,从嘴里抽出烟卷,闷头思索着。
“就拿你们来说吧,你们为什么到山西来?这一带本来是我们从日本人手里夺回来的抗日根据地。”
“我是个军人,我只知道服从命令……”
“听命于蒋介石,出此不义之师,助纣为虐,也该扪心自问了!”
“老大哥说得有理,请容我三思。”黄正诚脸孔抽动了一下,想笑一笑。看来,他还猜不透这位闻名于黄埔的“老大哥”何以提到蒋介石便如此动怒。
“就这样吧。我们请你到我们民主根据地的腹地去住一住,看一看。那里人民当家作主的情况和共产党所实施的政策,然后再同蒋管区比较比较,我相信你会得出正确结论的。”
往回走的路上,陈赓和戴其萼随便交谈着:“你平时喜欢读鲁迅的着作,看来你还没有读透。鲁迅把中国社会看透了,像阿Q都有精神胜利法,黄正诚他是国民党的上层,脑袋里的封建余毒肯定比阿Q多,他搞点精神胜利法算得了什么?值得你们那么大惊小怪?叫我说,他不表现精神胜利法才是怪事哩!如果他一开始就说,‘你们的一切都好,国民党军队真笨。’这能是真心话吗?黄正诚开始不服输是合乎规律的。他讲的是真心话,这比说假话好。了解了他的真实思想,我们才好教育嘛。”
他又嘱咐着:“写报告时,他怎么说你们就怎么写,你们自己的分析和估计不要混杂在一起。”他望着远处的山峦,若有所思,自言自语道:“真理在我们手中,为什么要放着真理不用,搞一些假情况来自己欺骗自己呢?”
中街战斗失利了
人们在庆贺胜利。慰问团的陈漫远在门口一露面,就被陈赓瞅见。
他跳下炕,把老早就很熟悉的陈漫远拉进屋,哈哈大笑着对大家说:“看,来了个大胖子。他是贺老总派来指挥我们的,我们以后要听他指挥!”
陈漫远被闹了个大红脸,捅了陈赓一拳,“我哪敢指挥你?贺司令员派我来慰问你们,向你们学习……”
陈赓抱住陈漫远的腰,夸张地量了量,继续开着玩笑:“你拿什么慰劳我们,就拿这身膘?”
“老陈,你别胡来,快指挥部队吧。”
陈赓连忙双手合十,闭起双眼,前后摇晃了几下,念起“经”来:“阿弥陀佛,托马克思在天之灵,保佑我们歼灭这两个师。歼灭敌人之后,我一定请你去杏花村喝一杯!”
“好,我祝你打胜仗。”陈漫远不愿打扰陈赓指挥,说完就离开了作战室。
攻击中街村守敌的部署正在筹划。
门刚刚关上,陈赓就向所属部队发布命令:由第十、第十一旅担任主攻;独二旅沿汾河西岸阻击阎援兵及榴弹炮团;其余部队分别阻击由汾阳、介休、平遥出动的阎援兵,围歼被包围在中街村的敌四十六师和七十一师。
“司令员,总攻时间到了!”作战参谋提醒陈赓。
陈赓看看表,说道:“部队的表不准,你上房顶,举火为号!”
参谋抱来一捆干柴,堆在屋顶的平台上。平时,老乡都用屋顶当晒场。干柴一着大,火苗噼噼剥剥地升腾起来,四周的部队都看见了。
——敌人也看见了:监听台传来敌指挥官向阎锡山声嘶力竭地呼喊:“快,快!快派飞机来轰炸,陈赓指挥所就在万户村!”
“妈的,鼻子倒挺灵。”陈赓望了一眼报话机,又伏在地图上。
“我看咱们挪个地方吧。”谢富治政委试探地问。
“阎老西就几架破P-51,没轰炸机,拉不出硬屎,洒点尿没啥了不起。”
“现在正朝咱们炮轰呢。”谢富治还是担心。
“已经轰过两三天了,让它去!”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我看还是搬一搬吧。”
“要搬你搬。”陈赓脸色一沉,手臂在身后甩了一下,不高兴地说,“中街攻了两次没攻下来,部队正等着我们指挥,现在转移,这能鼓舞士气吗?”他稍稍平静下来,向过来配合作战的王震司令员投去求援的目光:“你说呢,老王?”
“这怎么能转移?就在这儿指挥!”王震头也没抬,用手掌遮住眼睛,朝窗外观察。
“报告司令员!”通讯参谋放下电话,告诉陈赓,“楚副旅长上前沿去了!”
飞机在头顶上啸叫,压倒了地面上所有的声音,震荡着人们的耳鼓。两架P-51型战斗机绕着陈赓指挥所俯冲,发出震耳欲聋的锯铁般的尖啸声,朝地面吐出一串子弹。这当儿,太阳还未升起,红霞似血。敌人的炮弹不时掀起一层层积雪,沙沙地落在指挥所的窗户上。从屋顶上震下来一只耗子,陈赓一脚把它踢到门口,它一骨碌又活了,蹿出门去。
陈赓指挥所在炮火里震动。
陈赓、王震紧握着电话机,指挥部队。
战斗进行得很不顺利。中街村四周都是开阔地,敌人凭借有利地形和坚固工事进行顽抗。解放军先后两次发起攻击,均未奏效。第二次进攻,损失更大。十一旅三十二团九连担负主攻中街村西北角的任务,本可利用东侧一条南北向的土坎作掩护,但团长把路引错了,置部队于中街正北敌人暗堡的侧射火力网,全连壮烈牺牲。
一天多了,陈赓滴水未进。警卫员弄了点面糊,还特意加了几粒核桃仁,用小搪瓷缸盛着,端给他。中街不能硬打,陈赓、王震意见一致,准备调出东南面的部队,让出一条生路,叫敌人跑,然后尾追歼其一部。
陈赓一手端着缸子,一手握着电话机,蹲在炕上,向部队传达撤退的命令。
这时,话筒里传来周希汉喑哑的嗓音。
“什么?”陈赓听不清楚,却有种不祥的预感。
“楚大明同志牺牲了!”周希汉泣不成声。为了不影响陈赓的指挥,他把悲痛一直隐藏在心里,想等战斗结束再告诉他。可是现在他终于忍不住,说了出来。
陈赓一听,把缸子重重地一蹾,呼地站起来,不由得一阵心酸,身体摇晃起来。很长时间,他的脑子里一片空白,两眼呆呆地直视着,一言不发,像是在倾听,一直倾听着。
在场的同志唏嘘不已,泪水落在那些长久没有刮的浓密的胡须里,谁也不说话。
陈赓的嘴唇战栗着。他清清喉咙,眨眨眼睛,几乎是用鼻音在说:“把他的遗体保护好,随部队回太岳安葬,要开隆重的追悼会。现在正在打仗,先不要向部队宣布,待战斗结束后,教育部队化悲痛为力量!”
中街战斗失利了。
敌人撤走以后,陈赓、王震决定将吕梁和四纵的旅团干部集中到中街进行现场总结。
干部们从第十一旅的进攻出发地、火力阵地开始现场观察,步行到中街北面,心情和天气一样阴冷,谁也不说话。有个幸存的小兵像孩子似的啼哭。陈赓看了他一眼,想说他几句,但觉得舌头很僵硬。小兵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把头埋起来,又哭了。陈赓感到脑袋像裂开了一样。事实证明我们的炮火并未摧毁敌人的主要火力点,也没发现敌人的三个侧射地堡。
九连的进攻地,一片静寂。没有呼吸,没有语言,没有生命,战士们的躯体布满了阵地。全连依然保持着进攻队形,每个战士都是朝前卧着,而没有一个向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