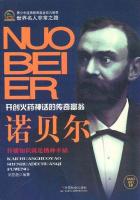他像看透了人们的心思,话锋一转,提出了大家关心的问题:“可是,有同志讲,我们一天可以走完的路程,为什么不走了,硬要选这个山腰露营呢?这是有着重大战略意义的。长征以来,我们干部团一直担负着中央机关首长的警卫任务。今天,毛主席和中央机关要在大硗碛一带宿营,准备明天过大雪山,在山下的达维镇与红四方面军的先头部队会合。我们今天在这里露营,明天行程100里,就可以到达懋功宿营,让出达维的房子给党中央、毛主席住宿。这是革命的需要,也是我们干部团的神圣职责。”
雪岭像回音壁,使微细的声音变得响亮起来了。人们议论着,赞同着。
“同志们!”陈赓洪亮的声音使大家安静下来,“更严峻的考验还在后头,夹金山的山神土地还会使出更残酷的手段来对付我们。怎么办呢,没什么了不起的!”他把右手一挥,好像要把整个夹金山劈成两半:“我,还有宋政委,在这里向全团挑战:谁英雄,谁好汉,雪山顶峰比高低!”
一阵掌声盖住了他的话。
散会以后,各营把队伍拉到各自的宿营地。
所谓宿营地,就是杂草丛生的荒草坪。除了一部分伤病员住进那座小石板房以外,团部领导也和大家一样露天宿营。有马的,就着马背拉开了帐篷;没有马的,三个一伙,两个一对,背靠背坐在草地上算是摊开了“床铺”。
寒星闪烁。大家把随身带的单衣、单裤、皮褂子都穿在身上,再裹上一条被单或毯子,横下心来睡觉。尽管雪山之夜奇寒无比,因为实在疲劳,许多人一上“床铺”就酣睡入梦了。
次日凌晨两点,陈赓命令:整好行装,马上开饭,继续前进。
走了半个小时,山风呼呼由远而近,呛得人透不过气。人在积雪中行进,上面是雪的陡壁,下面是雪的深渊。风带着雪花,不时扑打在脸上。这还是积雪带。到了凝冰带,犀利的山风像雄狮猛兽一样怒吼咆哮,卷着冰碴雪片,打在脸上身上,真像滚油泼、刀子割。有人披的毯子或裹的雨衣,被无情地撕烂卷走;有的同志稍不留神,连人带物一齐抛下山去;有的同志身体虚弱,加上高山缺氧,倒下去再也爬不起来……陈赓不时发出“不准停留”的口令,宋任穷也在大声鼓动:“同志们,拉起手来,跨过雪山,就是胜利!”风雪,吞没一个又一个红军。陈赓最担心个子矮小的小号兵。小号兵的草鞋已经冻成了两个大冰坨,头发梢结出冰霜。他脸皮白了,嘴唇乌了,头重脚轻地往下倒。陈赓急忙背起他,往山顶上爬……
到了山顶,风雪逐渐平息。陈赓大舒了口气,都像醉翁一般,倒在雪地里,又饥又渴。萧劲光提议吃“冰激凌”,全体赞成。陈赓用漱口杯舀了一大杯白雪,往嘴里填了一口。
突然山下有人背着枪走动,有人开起枪。陈赓捅捅苏醒的号兵:“快,吹号联络一下!”
山下的枪声停止了。一面红旗在摇。
6月14日,一、四方面军在达维镇会师。红军战士拥抱跳跃,不少人激动得流下了眼泪。晚上,在村外的大喇嘛寺坡地上举行了盛大集会。这可忙坏了陈赓。一、四方面军的干部他都熟悉,他忙着为两个方面军的干部介绍情况,引见中央首长。坚毅和幽默感在他身上浑然一体,使人感到他特别亲近,有时也使局面变得滑稽可笑。
首长讲话之后,会餐开始了。每桌8个人,4个菜。大碗热气腾腾的鸡和肉,大锅的汤和大罐的酒。这都是四方面军李先念的三十军从地主手里没收的。这是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次“盛宴”。几碗菜一瞬间使吞下肚去,大家又眼巴巴地东张西望,几乎桌桌如此。这时,陈赓却像变戏法似的端着两盘菜过来了,边走边炫耀他的“战利品”,大概这是他溜到伙房里说了一堆好话磨来的。大家毫不客气,围上去把他的菜“缴获”了。他没有办法,只好转身又钻到伙房去。不一会儿,他又弄了两大碗菜端出来,喜不自胜地跑到大家中间:“嘿,看吧,这是什么?”话音未落,手上的菜又被一个突然袭击扫荡一空。他措手不及,只好又跑回伙房……
欢乐是短促的,就像雪山的夏夜。当干部团路经两河口时,张国焘很怕露出他肥胖的身体,但是闷热的天气使他不得不解开衣服。他坐在喇嘛庙的神像下面,一面舒舒服服地喷着烟,一面不时向这神圣的角落的凳子下吐唾沫。
“你怎么又钻到这里来啦,陈赓?”张国焘亲热中含着狡猾。
“张主席,这不叫钻……”陈赓笑着纠正了张国焘的话,“我服从组织调动。”
“噢,你组织观念很强!”张国焘叫了一声,接着就转换话题问陈赓,“你在一、四方面军都干过,你觉得两个方面军有何差别呀?”
陈赓想避开这个敏感的问题。张国焘望望陈赓,等待他的回答,拿手帕擦着脑门上的汗。
陈赓想到四方面军戴的八角帽比一方面军的圆顶帽略大一点,就说:“四方面军是大脑袋,一方面军是小脑袋。”
张国焘擦净了脑门上的汗,做出倾听的样子,然而陈赓的回答使他很扫兴。他继续追问:“这是表面现象。我是问你政治上、军事上!”
“我说不清楚。”陈赓竭力回避。
“说不清楚?”张国焘提高了嗓门,恼怒超过了惊讶,“你个团长连这都说不清楚,还能带兵?”
“张主席,你别抓我小辫子。”陈赓急了,涨红了脸,“我说了恐怕你也不同意。”
“你说你说。”
“一方面军打仗勇敢,群众纪律好,政治工作好;四方面军打仗也勇敢,就是群众纪律差点……”
“噢?”张国焘揉碎了烟蒂,刻薄地微笑,“群众纪律不好,我的部队为什么人多?”
陈赓不语。
张国焘忽然表现出极大的宽容。一个新的念头使他的脸发出了光彩,他露出牙齿笑起来,猛地转过身子说:“你在我那里干的是师长,跑了一趟上海,回到这里怎么又成了团长?这样的冤情,你怎么也不向中央反映反映?”
他把“也”字咬得特别响。
陈赓知道他暗指的什么,忍不住说了一句:“该反映的当然反映!”他转身要走。
“你回四方面军还可以当师长嘛。”张国焘向陈赓远去的背影喊着……
此时,红军战士们都在为过草地准备着。他们把青稞麦割下晒干炒熟又捣成面,把羊皮缝成背心,用羊皮做成鞋子。
救了周恩来
长征的路越走越苦。
恶劣的环境使干部变得更爱发火,彭德怀脾气更躁。此刻,他在三军团指挥部里踱来踱去,皱起了眉头。他叹着气骂道:“这么多人,我就找不到一个合适的人!”
三军政委杨尚昆也不住地用指头敲击桌面。
他们在为周恩来的病情担忧。自过雪山以来,周恩来身体一直不好,经常咳嗽。尽管他自己不说,警卫员都知道他相当虚弱。他们想方设法让他多休息,而他总是按习惯工作到凌晨2点。他经常不上床铺睡觉,而是趴在桌子上打个盹儿,醒来又继续工作。他终于倒下了,高烧40度,一连几天不退烧,神志昏迷,说胡话,医生诊断是肝脓肿。毛儿盖会议后,党中央决定红军分左右两路北上,周恩来、洛甫和毛泽东都分在右路。这时周恩来除了继续担任军委副主席外,还担任了红一方面军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恰在这时,他的病情更加严重了,危在旦夕。在这个节骨眼上,原来抬担架的同志又都一个个病倒了。彭德怀和杨尚昆当机立断,扔掉2门迫击炮(当时红军总共才有8门这样的炮),腾出了40名战士,专门负责抬周恩来和其他几位重病号。犯愁的是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担架队长:这个人必须有高度的政治责任心,能吃苦;同时要有点医学护理知识。这在红军里头实在难找。
正在彭德怀、杨尚昆焦急万分的时候,陈赓跨进房门就喊:“我来当担架队长!”
彭德怀瞪起眼睛:“都什么时候了,你还瞎开玩笑!”
“怎么是开玩笑呢?”陈赓站定,“我就是来当担架队长的!”
彭德怀很不客气地上下打量起陈赓,好像从来不曾碰见过他一般。陈赓不动声色地忍受着彭德怀的注视。当彭德怀的目光停留在他腿上时,他的嘴唇微微抖动了一下。
彭德怀意外地大笑起来:“你是个瘸子!还是先保住你自己吧!”
他恳求的目光转向杨尚昆。杨尚昆摇摇头:“干部团的担子就够重的啦,再当担架队长……”
“你们放心,”陈赓拍拍胸脯说,“我陈赓没有多大本领,可对革命还是心地赤诚。只要我的心脏还在跳动,就一定把周副主席安全抬到目的地。”
两位领导仍不肯松口。彭德怀擦着了一根火柴,继续盯着陈赓。
“我还有个最大的优点你们还没发现!”陈赓说,“我当过医生!”
“在哪?”
“在上海,我挂过牌子开过医院,除了拔牙、接生,别的我都会!”
尽管有些夸张,他的话显然起了作用。彭德怀还有些怀疑:“你那是冒牌医生!”
“不管冒牌不冒牌,”陈赓继续说,“我还住过两次医院,俗话说久病成医嘛……”
杨尚昆点点头:“瘸子里拔将军,就叫他当吧!”
8月21日,以陈赓为队长的担架队,抬着周恩来等重病号上路了。草地每天必定下雨,陈赓经常手举着一块旧油布,紧紧地跟随在担架旁,保护着周恩来。
虚弱的躯体抵挡不住病毒的侵蚀,周恩来的体温又升了上去,昏迷,说胡话。邓颖超赶来了,她身体也很不好。毛泽东赶来了,他抓住担架杆,望着周恩来苍白干燥的嘴唇和那一把老人似的胡须,习惯地迅速解开纽扣。他朝后面的人挥挥手:“赶快叫傅连暲同志来!”
“主席,傅医生在左路军,恐怕一时赶不到。”
“一方面军那个‘戴胡子’呢?”
“已经派人去找了,到现在还没回来!”
“哎呀,再这样烧下去他会死的!”毛泽东摸摸军毯下面那只滚烫的手。
“主席,我有个土办法,试一试吧!”陈赓请示着,“雪可以降温。”
“茫茫四野,到哪里去找呢?”
“主席,你看那里有座小山,草地风雨无常,小山背阴处肯定有积雪。”
“你这个判断正确,快派人去取。骑我的马去,快!”
陈赓找来两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布置道:“你们俩马上出发,在前面那座小山等着,我们一到,就把雪用油布兜来,多兜些!”
残雪带来了希望。陈赓用油布做成个冰袋,装上雪,搁在周恩来烫手的前额。呻吟的周恩来渐渐平静下来。
等到医生“戴胡子”赶到的时候,他给周恩来量了体温,欣慰地吁了口气:“要不是及时降温,恐怕……”
周恩来的胡须动了一下,他那因为凝上水珠而变成白色的眉毛皱起来了。他迟疑了一会儿,睁开眼。
“周副主席,你醒了?”陈赓双手合十,如念经一般,“感谢马克思在天之灵!”
在眩晕的天空里,周恩来的目光找到了陈赓。周恩来喃喃说道:“东征时,你曾经救过蒋介石,长征路上你又救了我。”
陈赓笑了,但很快敛起笑容,做了个十分遗憾的动作,说:“假如那时我知道我们的蒋校长竟如此反动,就不会从战场上把他背下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