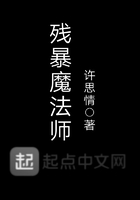当站在珍宝斋的二庭,站在无数奇兵宝剑之间时,段卿忽然又信奉起了腹有诗书胆气豪的说法,开始视金钱如粪土了。在被标价牌上一个个数不清的零晃花了眼之后,他立马就将钱是男人胆这种可笑说法抛之脑后,再也不信了。原本以为拿了赏格,便一夜暴富,在宛城也能勉强算个中产,但进了珍宝斋之后,才发现自己依然是个彻彻底底的穷人。
段卿想着,穷文富武的老话说的果然有道理。如果在数学上真有天赋,在得到启蒙之后,法师们只需要一卷草稿纸和一只鹅毛笔,就已经别无他求。而对于剑灵,如果没有殷实的家底,连一柄趁手的兵器都买不起。从前段卿并不觉得一柄好剑有多重要,但在握过破晓之后,就不再这么想了,回想起那一日的灵力解放,那一剑劈碎半座高塔的闪光,有多少能归功于自己,又有多少要归功于破晓剑的“名剑之灵”呢。
当然,这里的文武之说是千年之前的说法了。黄金年代以来,自从剑灵完成了自我启蒙,开始探求自己的内心意志之后,那些最顶尖的剑灵里,倒至少有一半看上去比法师们更当得起一个“文”字。那些口吐锦绣的诗仙,慷慨悲歌的文豪,常常也是用剑的高手。当今秦国第一剑灵赵梦鲤,便是最大的诗社离社社首。当年濠河之上,赵梦鲤弹名剑,赋长歌,诗万首,酒千觞。那一役,赵梦鲤一柄惊雷剑杀得人头滚滚,血染长河,群雄胆寒,得了个“酒豪诗仙剑圣”的名号。
段卿平日里穷日子过惯了,走在街上买不起的东西远多于买得起的。现在也一样,站在宝剑面前,心痒难忍,却只能看不能摸的感觉,和当年站在包子铺面前,腹中饥饿,却只能吞口水真是一模一样。看一眼去三庭的门,段卿叹一口气,转身回到了一庭。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在见识过神兵之后,就再难对一庭的这一堆凡铁产生兴趣。在挑拣一番之后,段卿选中了一套剑盾。
剑盾剑灵的传统可以追溯到茹毛饮血的原始年代。虽然经过了十万年的进化,但他们的作战方式在本质上并没有改变——一手利剑,一手坚盾,攻防一体。他们不像肩扛一人高塔盾的守护剑灵一样坚如磐石,也不如只握一柄长剑的传统剑灵一样飘逸灵秀,但剑盾剑灵在攻防两端都有所表现,尤其在孤军作战时尤其出色。不过只有低等级的剑灵才会在意自己所用的武器类型,那些最顶级的精英们已经跳出了这种粗浅的划分方式,凡人定下的标准早已不足以描述他们的战斗方式。段卿也许会告诉别人自己是个剑盾剑灵,而那些九段之上的剑灵们往往只需要报出自己的名字就行了。
段卿过去并不会用盾。他费尽心思为自己打了一柄铁剑,但从未想过为自己置办一面盾牌——这太奢侈了。为了攒够一柄长剑用料的铁,段卿干了一个月的白工,如果要攒够一面盾用料的铁,恐怕要白干上一年。不过在珍宝斋里,决定兵器价格的主要因素已经不是用料的多少,而是材料的性质与锻造的技巧。在这些方面,与那柄配套的剑相比,盾牌用料的范围更宽松,打造难度也要低得多。这个剑盾套装中,价格的大头在那柄剑上,这面盾算是个添头。
这套剑盾通体白色,其间缀着些蓝色条纹。盾牌中有一道凹槽,和剑的宽度相当,可以当作简易的剑鞘来使用。整套装备用一根熟牛皮背负在背后,取下来时,这根熟牛皮带可以收紧,一圈一圈得缠绕在手臂上,又可以充当盾牌的固定带。这一套剑盾作价一千五百银,不过它看上去可不仅仅只值这么点:盾牌表面刷的一层封漆让它看上去价值百倍。
这种封漆学名叫做“褪魔漆”,据说对魔法有一定抑制作用,不过这也就只能当作广告词听一听了。这种漆最大的特点就是漂亮,色泽通透润泽,光亮丰满,而且极其坚固耐磨,即使刀砍斧凿也轻易不会损坏。它让一千五百银的装备看上去至少值得五千银。人年少之时总有些爱慕虚荣,愿意为一些表面的浮华掏腰包,段卿自然也不例外,很快便拍板买下了这一套剑盾。
推开珍宝斋的门,外面已是傍晚,段卿不知不觉得在这里消磨掉了整个下午。太阳已经西沉,越过远方的地平线,能看到一团金黄的火球在跳动。在城市中看落日还欠几分意思,一定要在茫茫沙漠之中,落日才能显现出它最庄严的一面。段卿见惯了这些,只顾躲在屋子拉出的阴影里走路,他走的很急,心中有一个确切的目的地。虽然段卿说自己没有家人,也没有朋友,但在这诺大的宛城生活了这么些年,总有些人会稍稍关心他。段卿不愿意在自己困难的时候麻烦他们,但总会愿意在得意之时和他们分享。
在走过一条极偏的小巷时,在一个荒弃的角落中,段卿忽然发现了一个奇怪的人。他穿着与神官类似的长袍兜帽,但又有明显的不同,让人一眼就能看出区别。他背对着段卿,看不见正脸,那件长袍的背部上并没有绣上圣殿惯用的圣纹,取而代之的是一轮抽象的太阳。巷中的墙破了一块,掉了两三块砖,落日在这里投下一小片光线。那人踮着脚站在这仅有的落日余晖中,双手斜着向上伸展,掌心向外。他极力得伸展着自己的身躯,像旧时代的法师一样想要更接近天空。他迎着阳光仰起头,兜帽落了下来,露出一头黑色的长发。段卿听见他用信徒祈祷一样的语气念到:“赞美太阳!”令人意外的,这声音听起来格外清脆好听,是个女孩子。
听到这句赞美太阳,段卿就明白了,她是“万灵归一会”的教徒。这是一个********,现在是不折不扣的异端,它的起源可以直接追溯到旧年代。
在先贤辈出的黄金时代,诞生了无数大师巨匠,那些信奉神明的祭祀主教们也不例外。“第一先知”带领着他的信徒们开始了宗教改革,不过对宗教进行改造要比在其他方面困难的多,第一先知首先试图在神殿内部推行改革,试图删减一些已经不合时宜的教条,但受到了史无前例的巨大阻力。除了直接负责传教的底层教士之外,整个教廷都在反对他。最终第一先知主动脱离了教会,自立门户,开始独立传教。在其后的一百年中,新教会因为摆脱了人格神崇拜,从而显现出极大的制度优势和澎湃活力,随着越来越多的新牧师新圣骑士们灵力觉醒,他们已经能和旧教会分庭抗礼。
新旧教会的矛盾积蓄至这个时间点,最终爆发,一场圣战席卷整个大陆,三十年间死伤无数,生灵涂炭。很多小的公国国土整片沦丧,陈粮惨遭劫掠,新禾颗粒无收,土地上负载的人民一半死在战场,一半死于饥荒。大的帝国也无一例外均遭受重创,死于三十年战争的皇帝便有十余。最终在血泊中,旧神陨落,新神登基,大陆的形式被彻底洗盘。一个大帝国彻底崩裂,无数小的公国组成了联邦,又经过几十年的兼并和发展,最终形成了现在的局面。宗教这颗最顽固的钉子被拔除之后,历史的战车以更快的速度滚滚向前,将整片大陆带向了新时代。
在战争中败北的旧教会四分五裂,碎了一地,大部分消散在历史尘埃里,再也搅不出一点浪花,不过也有少部分艰难地存活到现在。其中依然在秘密传教的,只剩下三个,被合称为“日月星三邪教”,将太阳当作真神赞美的“万灵归一会”自然便是其中之一。
这些知识全部来源于神殿的官修历史,它所采用的史料可以保证绝无错误,但未必反应了历史的全貌。剑灵可以不练剑,但不可以不读书;读书可以不读哲学,但一定要读历史;读历史可以不读野史,但一定要读正史。神殿修的版本经过无数人的检阅,每一个细小的偏差都被找了出来,一一删改之后,已经再难在史料上进行苛责了。不过同一段史料,不同的人能得出不同的结论,段卿也有自己的思考。
然而这些目前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段卿的面前站着一个异教徒,全帝国统一赏格五百银,如果亲自押送至当地的教堂,还管一顿丰盛的大餐。段卿做过一单这种生意,尝过甜头,更何况入手了新装备,心中跃跃欲试,不介意再做一单。他一边蹑手蹑脚地靠近,一边小心翼翼地抽出了长剑。不过新装备缺少磨合,显得生涩,剑锋在摩擦盾里的剑鞘时,发出了刺耳的交鸣声。那名万灵归一会的教徒此时也完成了一整套赞美太阳的礼节,听见异响,转过身来,正看见持剑靠近的段卿。
夕阳又降了一寸,傍晚的光显得更加柔和。昏黄的光线从少女背后射来,将她的容貌掩藏在阴影之中。头发因为转身的动作而扬起,长袍的裙摆也被风撑开,一闪而逝得,露出了一双漆皮小鞋,还有一对洁白的脚踝。少女在夕阳下好似一个黑色的剪影,剪影的周围是一团明亮的夕光。这一切美得像一幅画一样,这是段卿第一次近距离领略到异性的魅力。
少女回头看见段卿,向后一跃,站在了阴影里,动作轻盈得像猫一样。等段卿适应了光线,少女已经拉起了兜帽,她低着头,只能看见一个小巧秀气的下巴。接着,少女抬起右脚,用鞋尖在地面上轻敲两下,一柄细长的刺剑便从神袍中掉了下来,右脚向后一磕,这柄刺剑在空中画了个圈,轻巧得落在她的手上。少女将剑挽出个剑花,最后斜横在胸前,做出戒备的姿势。
双方已经摆开了架势,段卿便也就不再着急。站定了向少女说话:“我已经叫了人,他们在来的路上,你已经逃不掉了,束手就擒吧,只要你能放弃异端信仰,神殿不会难为你的。”
“是吗?”少女不为所动,反而将剑尖指向了段卿。她笑一声,反问了一句。这句话既像是在否定段卿已经叫了人,又像是在否定神殿会如此仁慈,“我敢穿着祭袍站在这里,自然也有同伴接应,我们看谁的帮手来的更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