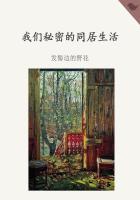礼拜五晚上我在狄安家过夜。他帮我重写了之前的代码,又教我怎么往后写。还拿他之前一个项目做示例,告诉我写样式要注意哪些细节,怎么写比较简便,如何重用代码,减少耦合。大晚上,两个人都在写代码,他坐电脑桌前,我趴在他床上。外面黑漆漆的,屋里灯光亮着,窗帘拉上。肚子饿了,他洗桃子给我吃。现在正是吃桃子的时候,他在小区门口买了些。小区门口的桃子比超市的便宜,虽说小贩子的秤都会缺斤少两,但口味远比超市里的新鲜。他买桃子都挑硬的买,软的放不久,容易烂掉。他很会过日子。晚上睡觉时,他让我睡里面,天气渐热,我们就盖的一条被。我睡了一晚,夜里嫌热,腿露在外面碰到墙壁,太凉了,差点感冒,后来都睡外面。他就把方桌往床边靠靠,怕我半夜从床上掉下去。但方桌太小,有天晚上我真咕咚一声从床上滚下来,撞到脚趾头,肿了两天,后来每次睡觉他都把我往里面拉。
礼拜六早上,狄安很早起床,煮了番茄鸡蛋面,等我醒了,端到床边叫我吃。为了顾及我的苏北口味,他特意放了点盐。现在我知道,他经常吃面一来是他们北方的风俗习惯,二来是面食对肠胃好。他之前减肥时节食过度,伤了肠胃,医生叫他以后主食尽量以软和的面食为主,少吃硬的冷的辛辣刺激的东西。吃完面,他去洗碗,我刷牙洗脸接着写程序。他给我买了只新牙刷。时间过得很快,现在五月,六月末要期末考试,六月中旬就会停课准备复习,六月初软概项目就要期末答辩,我得赶紧把代码写完。狄安一边洗碗一边说:“中午咱们吃饺子吧。”我以为他要出去吃饺子,或者到学校食堂吃饺子,心想难得吃一回饺子换换口味也不错,就说好。他说:“等下我去菜市场买馅和饺子皮。”我愣了下,问:“自己包?”
狄安跟我不同。我从初中就一直住宿在学校,吃喝都是学校食堂,从没真正独立生活过,洗衣服会,但煮饭烧菜都不会。硬要我做是可以的,之前暑假里爸爸病发,妈妈在医院照顾爸爸,姐姐要上班,每天就我回家做饭烧菜,带去医院给妈妈吃。但只能勉强充饥,很不好吃。烧饭时总搞不清楚米和水的比例,常常把饭煮成粥。炒菜时菜一下锅,锅里的油就爆起来,烫到手,拿着铲子远远地翻腾几下倒了水煮煮,等中间的汤水沸起来了就盛,经常没有熟透。但我一般只炒蔬菜,反正生的也能吃,无所谓。那段日子我爸病着,躺在医院,我妈情绪不好,也不管吃的,就勉强过日子了。唉,那么辛苦的日子,真不想再回忆。反正包饺子这么麻烦的事,我不会。狄安这几年一直独立生活,很会照顾自己,洗衣做饭什么都行。他去附近菜市场买了肉馅、香菇、芹菜、娃娃菜、香菜、榨菜、饺子皮回来,教我包饺子。但他毕竟是个大学生,不是家庭主妇,要买什么都直接称了付钱,也懒得多问两家比比价钱,更不会像我妈那样跟小贩子说,阿姨呀,我买你这么多菜,送我两根葱吧,你这葱看起来很嫩哩。
狄安把肉馅倒在锅里,是卖肉的人用绞肉机绞好的肉末,把香菇、芹菜、娃娃菜用烧开的热水烫一烫,先切成条,再切成丁,然后碾成末。切板放在方桌上,我跪在地板上,头低着,切不到几分钟就觉得脖子痛。狄安说:“你干嘛低着头切菜。”我说不低着头万一切到手指头怎么办。他接过菜刀就跟敲键盘盲打一样切着,说:“你把指甲往里面弯,用手指关节挡着刀不就行了。”我摇摇头不敢想,觉得不看刀的话,我会把整个手指关节都切下来,太恐怖。
切好丁,换我来碾末。他提醒我,要多碾几遍,翻来覆去碾得碎碎的。我手握菜刀在切板上碾过来碾过去,使了吃奶的力气,每一刀都像是砍在切板上,胳膊都酸了,左右手换来换去。他叫我不要这么用力,芹菜没那么硬,稍微用一点力就好。我真是一点都不懂厨房里的这点事。碾成末,用纱布包起来,挤掉水分。狄安说,不把水分挤掉的话,饺子皮会被撑破。把这些脱了水的丁末倒进锅里,和了生姜末,倒上盐、酱油、麻油,用文火炒熟。我没炒过饺子馅,力气使大了,好些馅末掉在地上。他叫我轻一点,然后跟我妈一样,用勺子把上面没脏的馅盛起来,倒在锅里,下面脏了的就拿抹布抹了,扔进垃圾桶。炒了一刻钟,肉末炒得发白,生姜末和娃娃菜是黄色的,芹菜是绿色的,香菇是灰色的,视觉效果倒不错。因为拌了麻油,屋里一股浓浓的香味。
狄安买的饺子皮是圆形的,我没见过,我们老家吃饺子都是方形的皮。他说他们过年都吃饺子,方形的圆形的都有,圆形的包起来容易。把饺子馅盛到饺子皮中间,不能多,小半勺就好,多了会撑破,然后把饺子皮对折起来,双手的虎口分别夹住半圆形的两边,往中间一压,要压紧一点,压不紧的话就用筷子沾点水,不然下了锅要破掉,要露馅。包好的饺子要分开放,粘在一起不好下锅。
狄安真的很细心,细心到我一度幻想他要真是我哥该多好。我妈在生我前怀过一个男胎,照过B超,都成形了,后来意外流产。要是那个男孩生下来,就是我亲哥了。但如果他真生下来,只怕也没有我。
在家时奶奶也教我包过饺子。我们苏北人过年不吃饺子,但头伏会吃,就是三伏天刚开始的时候,差不多是六月末七月初要放暑假的那几天。天热,没胃口,饺子沾了醋吃,开胃。但奶奶教我包饺子时,我总耐不住性子,觉得厨房里的这点事有女人做就好了,男人下厨做什么。可这会儿跟狄安学着包饺子,觉得很温馨。
包饺子时,狄安的电脑放着TAYLOR SWIFT的歌。狄安跟我喜好不同,他不喜欢LADY GAGA的舞曲,觉得太吵了,耳朵都要聋掉。他喜欢乡村音乐,推荐我听TAYLOR SWIFT。我只听过她的《LOVE STORY》,觉得不错,风格很别致。狄安说,她的风格就是乡村音乐。他给我听TAYLOR SWIFT的《OUR SONG》,问我有没有听到开头那段木吉他和小提琴的旋律,是不是很悠扬。他说,乡村音乐的曲调都很轻快流畅,配乐几乎都是弦乐,歌手嗓音很明显,不比电子舞曲,歌手的声音都被电子音盖住。电子舞曲的歌词都没什么意思,主要听曲调,乡村音乐的歌词一般都是叙事,比如这首,就是TAYLOR SWIFT跟男朋友交往的一些小细节,很温情。
狄安把饺子下锅时,电脑的歌又放到那首《OUR SONG》,TAYLOR SWIFT的声音很清澈,她唱着:晚上你敲我的窗户,我跟你偷偷溜出去,三更半夜我们讲电话,妈妈也不知道,第一次约会忘记亲吻,回家后跟上帝祈祷,可不可以重来一次。这种恋爱的感觉我早忘了。跟刀刀分开三个多月,他给我充的话费全用掉,我们之间再没瓜葛。听这种情歌,不自觉就想谈恋爱。要是身边这个人没跟李文超在一起那该多好,我一定要跟他恋爱,他太体贴太温柔,是个好男人。真羡慕李文超,比我早遇上狄安。不然以我跟狄安如此相近的生活经历,他应该更喜欢我,我比李文超乖多了。
吃饺子的汤料是狄安自创的,把香菜洗了切成小段,榨菜丝也切成小段放在碗里,倒上酱油、醋、麻油,浇上饺子的面汤。他问我要不要加点辣椒油,加点辣比较开胃。我说我不吃辣。
“你不是肠胃不好,不能吃辣吗。”我问。
他笑笑说:“我不吃,李文超有时候吃。他很喜欢吃饺子。”
狄安无意中提醒我,我们之间还有个李文超。但这也不是什么值得心酸的事,他没打算欺骗我,他经常跟李文超在网上视频聊天,有时李文超也跟我说两句。狄安说他很久没吃饺子,一直想吃,一个人懒得做,嫌麻烦,两个人一块吃比较有胃口。锅里的饺子热腾腾地沸起来,白嫩嫩的。等熟透了,浮在水面上,他先给我盛。他知道我胃口小,只给我盛了小半碗,给自己盛了大半碗,剩下的盛在盘子里,端到小方桌上。他包的饺子口都很紧实,我包的饺子口都有点散开,捏得不紧。他说头一回包饺子没露馅已经很不错,叫我趁热吃。
大学以来我几乎都在学校食堂吃,食堂的饭菜虽然干净便宜,口味也不错,但永远是那些菜色不会变,连摆菜的窗口都是固定的,卖番茄炒蛋的永远卖番茄炒蛋,卖燃面的永远卖燃面,你想吃什么,都不用仔细看,下意识就能走到对应的窗口去。刚来交大时还觉得新鲜,吃过一学期就腻了,夏天胃口不好,更吃不下,隔三差五就要换个食堂吃。有同学干脆每个礼拜一次,三五个人一块出去吃,改善伙食。我平时很少回浦东,怕回去了又要被爸妈说,就算回去也没什么好吃的,能偶尔来狄安这边吃吃现炒的小锅家常菜,已经很满足。
狄安家的窗帘是深蓝色的,外面天气好,窗帘只拉了一半,阳光透过那一半蓝色的窗帘,照在我们身上,有隐隐约约的蓝。我们坐在小方桌旁吃着热腾腾的饺子,芹菜,娃娃菜,香菇,肉末,香菜,榨菜,嚼在嘴里特别香。电脑里放着TAYLOR SWIFT的《LOVE STORY》,听着木吉他的弦乐声。可以说,这是我这学期最美好的一天,有家的归属感,有人陪在身边一起生活很温暖。
但这一切很快被毁掉。美好的都是短暂的。从前在图书馆,陈煦研究炒股,教我看股票K线图,我看到许多股票慢慢涨到一个高峰,然后很快跌下去。我一个行外人不懂金融证券,但多少听闻股票的风险,劝陈煦不要炒股。没想到生活也会有这样急转直下的波折。上一秒还在天上,下一秒就掉到人间。不,是上一秒还在人间,下一秒就掉到地狱。
姐姐发短信过来。以为她又要问我生活费够不够,要不要给我打点钱。她每个月都会问。但我通常都回她,够。然后细细算了告诉她,这学期的助学金我已经拿到,助学贷款也发下来,家教的钱也能补贴一些。谁知姐姐发来的居然是:“爸爸早上去查血常规,复发了,已经住院。我在加班。下午你去医院看看。”眼前蓦地黑了一下,揉了揉眼睛,把短信重看了遍,然后心脏剧烈地跳动起来,呼吸急促。
昨天上午妈妈给我打电话,问我周末回不回家。我不想听他们唠叨,撒谎说最近有考试,要准备复习。下午还要去陕西南路给王瑞琪做家教,一来一回太辛苦。她就只叮嘱我,好好复习,饿了就去吃饭,注意身体。她在电话里跟我讲,两个礼拜前爸爸去查血常规,结果正常,说今天也要去查,我也没在意,以为会正常。都正常了快一年,怎么就复发了呢。我气,气得发抖。我气什么,气老天爷待我不公平?不,我不信宗教,不确信老天爷是不是存在,就算他存在,我也不敢气他。我算什么,哪有资格?气妈妈没好好照顾爸爸?不,妈妈每天起早摸黑这么辛苦,已经把爸爸照顾得很好。气爸爸自己不争气,没好好保养自己?不,他吃东西都很小心,累了就休息,从不出门,就只在家里来回走走当锻炼。气自己?是,气自己没钱,连爸爸生病复发了都没办法,拿不出钱来给他治病,只能在这儿气自己。
狄安问我怎么了。我把短信给他看。他说:“吃完去看看你爸。”他很体贴,说我妈忙着照顾爸爸,肯定没怎么吃,用塑料饭盒装了满满一盒饺子,还用塑料袋倒了些醋,给我包好让我带过去。医院应该有微波炉,饺子热一热,把醋倒在上面就好吃。我脑子里一片空白,再也尝不出饺子的味道,匆忙吃完就走。他送我去地铁站,路上反复提醒我,不要难过,尤其不要当着爸妈的面难过,他们压力大,情绪不好,你要稳着自己,不能慌。我说我知道,但我手在发抖,因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尤其不知道爸爸这回还能不能熬过来。刷卡进站前,狄安拍拍我肩膀,给我鼓气似的,叫我路上小心,家教完了早点回来。
我坐地铁到蓝村路站,出了地铁站再走一站路,到浦东仁济医院。仁济医院是浦东一家综合性大医院,家里平常感冒咳嗽都不会来这种大医院,远,贵,爸妈都没医保,不能报销,如今也是没法子,命要紧。一路上我的脸色完全垮下来。我想到前两年我爸住院的光景,永远都是仁济医院住院大楼十四楼血液科病房,六个人一间,常常是一人住院一家子都来照顾。得了血液病,要么死,要么治愈了复发,从来没有痊愈的,病房里的就这两个结果。去年我爸复发时,同病房里有个跟我一样年纪的男孩子,白血病,住院两个月不到就死了。唯一庆幸的是,我爸前两回住院排病房排了好几天,这次刚好有人出院,赶紧住进去。宁可多花两天的钱,也要争取到床位,不然治疗太麻烦,我爸这病不能拖。
医院门口人来人往,有卖花的,有卖水果的,更多的是排成队的出租车,他们等着初愈的病人出院。我爸前两回出院都是我扶着上出租车的,身子虚弱得不行,根本不可能坐公交车,太折腾。住院两个月,见了太阳都不适应,眼睛疼,一进车子就躺在后座。不知这回运气是不是还那么好,能出院。
医院的温度比外头阴凉许多,人声嘈杂,永远一股厚重的药水味。周末人多,急诊室的输液区坐满了感冒咳嗽的大人小孩在吊点滴。仁济医院是浦东最大的医院,谁有个大小毛病都会来这边看。当年我爸一开始是去社区小医院看的,小医院查了查,说他们看不了,建议转来这。
住院大楼在急诊室后面,有个过道可以穿过去。住院大楼的墙壁是棕红色的,跟交大的教学楼一样。但学校的墙壁让人觉得年轻热情,这边的墙壁只叫人觉得压抑。挤上电梯,来到十四楼,就像来到太平间,比急诊室还要阴冷,墙壁上快要渗出水来,有股寒气透到了骨子里,汗毛都竖起来。也没什么声音,很安静。服务台有三个护士在值班,她们穿着白色制服,小声聊天。我走到爸爸的病房,病房有通气的窗户和阳台,空气还好些。病房很大一间,有二三十平方,六张病床。左边三张床,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头子,跟他老太太挤着一张床在午睡,旁边放了个椅子搁腿。一个跟我爸年岁差不多的中年男人,似乎要出院了,也没人照看,面色红润,扶着床边走来走去,当是锻炼腿脚。还有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在最里面,躺在床上休息,一旁的女人应该是他妈妈,在给他削苹果,床上挂着许多输液袋子。右边三张床都是中年男人,都在输液,有个是老妈在照顾,有个是老爸在照顾,我爸在最靠门一张床,妈妈趴在床头睡了。她听见我脚步声,醒了,擦了擦嘴边的口水问我有没有吃饭。她脸色很憔悴,比躺在床上的爸爸还憔悴,苍白色。我说我吃了,把狄安包的饺子拿出来,说是在食堂买的,比外面便宜。她真饿了,也不热一下,也没倒醋,怕病房里别人闻到不喜欢,就直接用手抓着吃起来。她吃了两个又走出去,到服务台那边,很小声地说:“护士小姐,不好意思,我老公的盐水吊完了,麻烦护士小姐帮忙换一下盐水,12号床,靠门的。”
护士很尽职,在电脑上看了看,确认了下:“12号床,徐卫国,对吧。”到药水房里找了找,拿了盐水袋子,推了小推车过来,给我爸换盐水。调点滴速度时,护士跟我妈说:“要是他觉得不舒服就把这个调慢一点。这袋吊完今天就结束了,可能小便比较多,他要小便就拿便盆给他,尽量不要下床,不要让他动身。”我妈低头说谢谢护士小姐。不管哪位护士,我妈都称呼小姐。有时爸爸身体不舒服,吊了点滴有不良反应,或者心电图不正常,就算我妈再不放心,她都会先说一句,护士小姐,不好意思,能不能麻烦来看一下。她甚至会下意识地弯一下腰。
她头发又白了,从耳边垂下来,挂在饭盒上。我让她吃完去睡会儿,走廊上有长椅,她可以躺着睡,我来照顾爸爸。她说不用,问我下午什么时候去做家教。我说两点多过去。她让我先在这边看着,她回去拿点东西,顺便找水产市场的管理说说,下半年摊位不租了,看能不能把摊位的钱退回来。按规矩摊位都是整年租的,一年一付,现在出这种事也没办法,市场里也晓得情况,管理应该会通人情。
水产市场的摊位是爸妈的老本,走到这一步,也是家里没别的办法。妈妈忙活了一上午,来来回回好几次,安排爸爸住院,给医院交钱,回去拿生活用品。姐姐要加班,这些事就她一个人干,她不放心爸爸,忙得连吃饭的功夫也没,吃饺子时狼吞虎咽的,水也不喝,刚吃完就要回水产市场。临走时还不忘提醒我,给人家做家教不要迟到,考试复习要抓紧,爸爸不要你担心。
妈妈回去后,由我照看爸爸,他睡醒了,脸色不大好,蜡黄色,手臂上戳着一根针管,吊着一袋淡黄色的药水。床尾夹了个单子,上面是今天要吊的盐水,都划掉了。除了氯化钠注射液是生理盐水外,别的我都看不懂。床头的柜子放着心电图探测仪,上面数字和线条一跳一跳的,心率脉搏血压都有,但我看不懂。有个小夹子夹在我爸右手的食指上。护士说,每隔一小时就要换个手指,不然血液不流通,手指要麻掉。我不晓得刚刚妈妈有没有换,就给他换到左手的中指。
我问他怎么样。他含含糊糊地点点头,说要喝水。我拿杯子给他倒了水,拿了根吸管给他吸,这是我妈想出来的法子,这样我爸就不用起身,水也不会从他嘴角流出来。喝完水,他要小便。他手上吊着盐水,心电图一直在测,不好动,我拉上帘子,病房里每个病床旁边都有一圈帘子,掀开被子,拿了尿壶,给他脱了裤子,就一条睡裤,扶他侧过身来,把他的生殖器放在尿壶口,照顾他在床上小便。
当我在他的小便里看到一些红色液体时,心里的恐惧无限放大,但我很快稳定情绪,就当没看见似的,等他小便完了,给他穿上裤子,扶他躺好。但我心里明白,过不了多久我爸身上各处都会出现淤血,红一块紫一块,大便小便都会内出血。用的那些药和手术都有副作用,会大小便失禁,到时候病床上都是红的黄的脏东西。医院附近的超市有卖成人纸尿布,妈妈买了许多,到时就给爸爸垫在屁股和裤裆,脏了就换。那时就不给爸爸穿裤子了,盖被子就好,不然照顾起来不方便。
“前两天小便就看见有红的。估计这回要复发。”爸爸叹气,“躲不掉啊,躲不掉。躲到哪儿就是躲不掉。该死的就是要死。躲不掉!”
我没接话,去卫生间倒掉小便,把尿壶冲洗了下,调整好呼吸才出来,坐在床边给他捏捏腿脚。用药之后,他身体就渐渐虚掉。护士说他躺在床上不好动,肌肉会萎缩,有空给他按摩按摩。我爸的脚跟我妈的手一样,成天泡在苏打水里,皮开肉绽,脚趾甲里黑乎乎的,脏得很,还有脚气,臭。我倒了盆热水,撒了点花露水,给他洗脚,脚指头一个个擦干净,免得护士医生闻到异味。去年前年他病发的时候我几乎每天都干这事。总想着,万一他真要死掉,好歹我做儿子的尽了份孝心,不会太难过。
“小生,你过来,爸爸有话跟你说。”他有些吃力地跟我招手,我坐到床头,他说,“爸爸生这个毛病,自己晓得没得救。前两回东借西借的借钱看病,还没还掉,没还掉就算了,老问人家借钱,自己也不好意思。我跟你妈妈商量了,准备把摊位卖掉,拿钱看病。能治多久就治多久,没钱治了就回东台,看看你爷爷奶奶,死在家里,怎么都不能死在上海。”他缓了口气接着说,“小生,爸爸这回复发,你要有心理准备,要是爸爸死掉,你不能哭,爷爷奶奶快八十岁了,年纪大了,你要照应他们。你妈妈这两年这么辛苦,是爸爸对不起她,你要照应你妈妈。你姐姐年纪也不小了,叫你叔叔伯伯在村里帮忙看看有没有适合的小青年,我们家这个破落穷酸样子,不挑剔门面,也不要聘礼,人老实稳重就行。等爸爸死掉,家里就你一个男的,你二十岁,不小了,爸爸二十岁的时候都出去赚钱养家了,你要好好读书,家里以后就全靠你了。”
他说完这些,咳嗽了两声,要喝水,我喂他喝了点,他喝了水就睡了,累得很。病来如山倒,说得正是我爸。前一刻还好好的,其实也没算多好,但至少能走能行,下一刻就躺在病床上要人照顾,连大小便都不能自理。想起前两年他那半死不活的样子,不能接受那样的日子再来一回,情愿他早点死掉,有个解脱。可当他亲口说出那些回家等死的话来,我心里又揪起来,他怎么能死,他死了家里怎么办,我跟姐姐怎么办,妈妈怎么办,还有爷爷奶奶,叫他们白发人送黑发人吗。
原以为日子会这样波澜不惊地过下去,哪晓得又来这晴天霹雳。想不通为什么那些好事从没轮过我,偏偏这些祸事总撞在我身上?
等爸爸睡了,我站在阳台走廊上吹风,不想闻房间里的那股病殃殃的气息,尤其那个老头子,都七八十了还得血液病,饭都不能吃,我看他绝对熬不过一个月。一个月,我爸能熬过去吗。血液病有多恐怖别人不晓得我还不晓得?我趴在阳台上,风吹在我脸上,吹起我头发,却没一丝惬意。高中课间休息时,我跟意询常趴在阳台上吹风,聊哪所大学的哪个专业比较有前途。那是我们紧张的学习生活里唯一放松的时候。现在没有了,以后也不会有了。每时每刻神经紧绷。我朝楼下看,十四楼算很高,下面的人一点一点的很小,有股想跳下去一了百了的冲动。听说正常人从四楼跳下去就会死,十四楼,够我死三回。我的人生已经明摆着没有希望,还活着做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