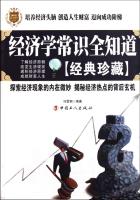厉以宁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可偏偏祸不单行。抄家的红卫兵、剃阴阳头的“刮刮匠”,勒令他带高帽子游街的“闯将”,隔离审查、监督劳动的“太平洋义务警察”……形形色色的斗争队伍从四面八方向厉以宁气势汹汹地杀来,厉以宁“四面楚歌”。面对着无数的侮辱与诽谤,正直单纯的厉以宁无言以对,欲哭无泪。他茫然直视,两眼发黑,像发寒热一样颤抖。一阵阵的刺痛在脑中盘旋。血痕印上他惨白的面颊,一种猝发的疾病降临在厉以宁身上,他开始眩晕,甚至休克……
“九一三”事件之后,形势逐渐好转,而厉以宁却如同惊弓之鸟,激烈的阶级斗争使他无所适从,惟一的心灵慰藉就是经济学。幸好他还拥有众多热情的支持者,他们把厉以宁保护起来,使他能够在一个小书库的角落里读书。由于经济系副主任的坚持,资料室继续订购世界各国文献资料,即使在动乱的年代也没有中断过。厉以宁继续阅读、演算、思考,情绪逐渐振奋,健康却日益恶化。但他从不说,也不顾,一心投身于研究。白天在资料室的小书库一角,夜晚在煤油灯下(北大常常停电),厉以宁不知疲倦地攀登着。
黑暗的日子里终于出现了曙光——一直关心北京大学工作的周恩来总理抽出空来排除帮派的干扰,而邓小平的复出则是一个科学有救的信号。人们总有一天会把应得的荣誉献给这位学识渊博、为祖国的繁荣鞠躬尽瘁的著名经济学者。
1976年10月初的一个夜晚,厉以宁的同事们激动地把好消息告诉给厉以宁一家:“四人帮”垮台了!
厉以宁激动得一下子坐到沙发上,恨恨地说:“最坏的东西就是他们四个!最最坏的就是那个妖精!”从未骂过人的经济学家平生第一次骂出声音来:“混蛋!”接着,厉以宁拉住老伴的手,示意女儿叫醒已经沉睡了的厉伟,四人走到东墙前面,在毛主席和周总理的照片前用颤抖的手举起酒杯,一饮而尽。一股暖流瞬时流遍了每个人的全身,放眼看去,美丽的北大校园似乎也恢复了往日的勃勃生机,又展示出了美丽如画的风景。厉以宁终于展开了紧锁的眉头,模仿着老伴的腔调说:“你这个书呆子算了吧!你搞不过人家。你搞科学,可人家是搞……搞阴谋的!哈哈……”一家四口都满面泪痕地笑了……
人们所走的道路各不相同。有些人小心翼翼地左顾右盼,随波逐流,任凭风浪摆布;而有些人则要亲自创造条件,看不惯现存的一切,要干涉人世间的不平,对周围环境从不屈服,总想制服它并加以改造。显然,厉以宁属于后一种人。他在理论上是一位思想家,在实践上则是一名战士。尽管他命运多舛,但却总是岿然不动,然后把握机会再反攻。厉以宁的一生充满了大起大落和意想不到的转折,外来的和自我的肉体与精神的折磨、迫害使得他试图逃遁于世界之外,而且他曾经近乎成功地逃避在对外国经济史的研究中,但最终他还是没有藏匿下去。在诚实的经济学探索中,厉以宁逐步接受了辩证唯物论。近20年的帮派体系的打击迫害以及命运冷酷无情的捉弄没有将厉以宁打倒,他成功地抗击了“四人帮”对他直接或间接的威逼与利诱。严酷的磨难使他变得更加坚强,更欲奋进。厉以宁恢复了健康,迈着自信的步伐走向祖国经济建设的前沿。
改革开放之后的奔忙
人们开始了解厉以宁,多是由于厉以宁在1978年以后在中国经济学界系统地介绍与评价了当代西方经济学说。可谁曾想过,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厉以宁读过多少本英文、德文版的经济学专著,摘录过多少篇当代经济学的论文?60年代末70年代初,厉以宁就注意到新凯恩斯主义的兴起,他是国内最先研究西方经济学非均衡理论的人。80年代以来,他与陈岱孙教授等合作,为北大经济系的研究生开设过“西方经济学名著选读”与“西方国际金融理论名著选读”两个系列的读书课,每个系列就有10多本书,每一本书厉以宁都做过一定的研究,能提出自己的看法。这样广博的知识,如此深厚的功底,在中国当代六七十岁左右的经济学者中也实属罕见!
大批量的密集的读书与写作过程对于厉以宁来说,是一种与人类精神食粮会合、消化的过程,即使是在阅读英文资料时,他热爱中国、关注当代中国经济问题之心也是不泯灭的。厉以宁说,历史上每一个大经济学家都是由于研究本国经济的重大问题而成名的,一个中国经济学家的思想之根在中国。这种治学态度,使厉以宁得到了两方面的收益:一是读活了浩繁、翔实,甚至有些琐碎的经济史巨著;二是在认识外国经济问题的症结的同时也认识了中国的经济病。1978年夏,厉以宁在罗志如先生的指导下,以自己对英国经济的长期研究为基础,开始撰写《20世纪的英国经济——“英国病”研究》。
他发现,所谓“英国病”其实是由畸形的经济结构、人才的被埋没或者不得不转移到国外、国有企业效率低下、社会各阶层的离心离德和国际收支的恶化、财政赤字剧增等等现象的综合症。“英国病”其实在相当意义上也是“中国病”!厉以宁写道:“一个国家,如果本国人民中大多数人科学文化水平很低,愚昧、盲从、迷信,如果他们还受到封建专制意识的严重束缚,他们所处的环境又是扼杀一切科学文化成就的、缺乏民主的封建专制,家长式的、法西斯主义的统治,那么,当促使经济高涨的有利条件消失之后,它的经济一旦衰落,必然急转直下,趋于崩溃而不可收拾……”这不禁使人联想到“文化大革命”后期中国经济那种“崩溃而不可收拾”的危机,也唤起了改革图存的意识。
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中国人民真正带来了改革的春风,也为厉以宁带来了学术上金色的收获季节。长期积累的文献卡片用上了,在资料室与农村做的思想札记被重新整理了,他的一篇篇“旧稿”经过修改得以发表了,他的宏大的写作计划也终于可以实现了……
厉以宁有一个生活习惯,不论多忙,每天至少写1000字,并且通常是清晨一起床就将头天晚上打好的腹稿写出来。他的书案上总是有条不紊的——左上角是手头正在用的十几本中文、外文参考书竖直一排;右下边则静静地躺着未完成的手稿。他写文章,从不打草稿,清秀的文字直接写在稿子的方格里。写时铺一层复写纸,等交稿时,一份送出版社,一份自己保留。
改革开放之初,急需厉以宁写出有关中国经济改革、对外开放和发展的理论文章,写出能反映中国经济运行的矛盾与提供解答的对策的论文。面对这种时代的要求,他以前的生活积累够吗?他在西方经济学说方面的功底是否能在研究社会主义经济学时用得上呢?长期生活在书斋里的一介书生是否能够对经世济民的重大国策发表切中时弊的见解呢?
厉以宁显然不能回避这些挑战。1983年9月的一个晚上,当厉以宁为刚入学的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研究所的研究生做学术报告时,收到了从听众中递上来的一张字条,字条上问道:“您是否认为自己对中国经济实际已比较了解?您所熟悉的现代西方经济理论是否能与中国经济实际联系起来?”
厉以宁对此的回答是非常坦诚的:
“我长期生活在北大,我的主要活动是读书、教书,因此,比起从事实际经济管理工作的同志来,我对中国经济实际的了解是不够的,因此我这两年的研究生专业是‘现代西方国际金融理论’或‘比较经济学理论’。但是,经济学必须联系中国经济,不联系中国实际,经济学是没有出路的。其实,当代资本主义国家的一些经济学家是非常注意理论联系实际的,资产阶级总不会老是欺骗自己,养一批不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庸俗学者。现代经济学中某些与经济运行联系密切的理论,如利率弹性问题,货币管理的目标变量与中间变量问题,我们都应联系中国的实际加以研究。”
事实上,厉以宁对中国实际的认识是深刻的。这种深刻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长期的下放劳动,使他对民情有直接的把握;二是涉猎广博的理论研究使他能够发现中国经济中凭直觉难以发现的重大问题。因此,他的目光在大的问题上尤其敏锐,进而提出反映中国经济运行本质的重大理论问题,在思想上给从事实际工作的人以启迪。厉以宁是最早用现代经济学的理论研究中国就业问题的人,接着,又从就业问题转向中国的人力资源,再转向教育经济学、环境经济学的应用研究。他主持的中国教育经济学研究历时近8年,其成果经专家们鉴定,已经把我国的教育投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从1983年秋至1984年夏,厉以宁与其他几位经济学家一起参加了国家体改委关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设计。
半年多实践,使厉以宁接触到大量的有关企业、生产、价格、货币、外汇、财政收支、税收、利润、工资收入、补贴等方面的信息。与此同时,厉以宁把自己的理论研究重点定在社会主义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的结合上,并下决心写出一部自己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来。
1984年第2期的《经济研究》发表了厉以宁的论文《计划体制改革中宏观经济与微观经济协调问题的探讨》,成为厉以宁在这一阶段对宏微观结合研究的一个小结。与此同时,厉以宁在1985年为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所的研究生开了十多次讲座,讲座内容后来集结在1986年出版的《体制·目标·人:经济学面临的挑战》一书中。厉以宁在这本书中所提出的主要经济学新观点,形成了1986年出版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与1988年出版的《国民经济管理学》的理论基础。厉以宁关于体制的研究是以生产要素的重新配置为背景而展开的,生产要素中的人与财产要有效配置,就应有相应的市场机制,而这种市场机制必然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股份经济与市场体系。股份制就这样自然地被提来了。
1985年,中国经济学界的热点在宏观失衡及其控制上。厉以宁也主张宏观控制,但反对财政、金融与收入政策一齐紧缩,提出在中国目前,总需求大于总供给有其必然性,强行按住需求会扼杀企业。在这以后,他并未参加什么论战,而是埋头撰写自己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厉以宁对于笔战的态度历来是两条:一是“不还嘴”,别人写文章批评自己,自己从来不写应战的文章;二是不受干扰,精心编织自己的理论体系,争取让自己的书去影响读者,让社会评判。厉以宁曾这样告诫自己的学生们:“最值得去做的,是自己同自己商榷,自己同自己争辩。只有在学术观点上先说服了自己,才能说服别人。正如文学创作一样,只有作者自己感动了,才能感动读者。”“你写了一篇文章,不要急于拿出去让别人看,你自己应当成为第一个质疑者和商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