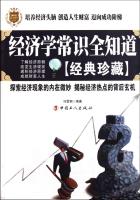厉以宁教授指出,生产要素供给者参与市场活动的机会是均等还是不均等,生产要素供给者是不是按照各自的效益取得了收入,这些都是判断收入分配差距是否合理的标准。这两个标准是不可缺少的,但是单凭这点还不够,还需要加上另一个判断标准,即把收入分配差距的存在是否引起社会的不安定看成是这种分配差距合理与否的标准。在这里,厉以宁教授提出以社会成员对自己的绝对收入以及与他人相比较的收入的满意度,作为衡量收入分配协调程度的标志。
社会成员对个人收入的满意度可以简称为个人绝对收入满意度,即个人作为生产要素供给者对于自己提供生产要素所得到的收入同期望值的对应程度。如果个人所得到的收入同期望值达到了对应或者大于期望值,个人就对自己的绝对收入感到满意。如果个人得到的收入少于期望值,即二者不对应,那么个人对自己的绝对收入就感到不满意;而且所得到的收入越是少于期望值,个人对自己的绝对收入的不满意程度就越大,或者说个人绝对收入满意度就越小。
社会成员对自己与对他人相比较的收入的满意度可以简称为个人相对收入满意度,即个人以自己所得到的收入同他人得到的收入的实际比率同期望比率的对应程度。如果这种实际的比率同期望比率达到了对应或者大于期望的比率,那么个人就对自己的相对收入感到满意。如果这种实际的比率小于期望的比率,即二者不对应,那么个人对自己的相对收入就感到不满意;实际比率越是小于期望比率,这种不满意程度就越大,或者说个人相对收入的满意度就越小。
社会是由众多成员所组成的,每个成员的个人绝对收入满意度和相对收入满意度都不会一样。在任何一种分配方式之下,社会成员的两种满意度之间的差异总是存在的,但某一个社会成员的个人绝对收入满意度低或个人相对收入满意度低并不会造成社会的不安定,而只有在相当数量的社会成员如此的时候,社会才会出现不安定。我们可以得到一定时点上的社会平均绝对收入满意度和社会平均相对收入满意度,然后根据两种满意度各自在影响社会安定方面所起作用的大小,得出社会平均综合收入满意度。如果这一数值降到临界值以下,社会就有可能出现不安定;社会平均综合收入满意度越是低于某一数值(临界值),社会的不安定程度就越大。
厉以宁教授最后总结了自己关于协调收入分配的观点:在机会均等与按效益分配的基础上保持合理的收入差距,使社会平均综合收入满意度保持在临界值之上,以维持社会的安定。政府则需要运用一定的宏观经济调节措施(如税收政策和扶贫政策)来防止收入分配差距的过大,否则社会经济的发展难免受到消极的影响。
那么对于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关系又该如何把握呢?要公平还是要效率?对此学术界争论已久。厉以宁教授的观点则非常明确: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厉以宁教授首先指出,将“公平”理解为收入分配的均等化显然是不正确的。一方面客观上不可能做到收入分配的均等化,另一方面收入分配均等化恰是分配不公平的表现,因为它抹煞了收入分配的合理差距。对“效率与公平”中的“公平”的正确理解应当是:机会均等条件下的竞争和收入分配的合理差距。如果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不均等,那就是不公平;如果收入差距超出了合理差距的限界,那同样是不公平。
然而,机会均等与收入分配的合理差距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其实现必须有一定的物质基础。收入差距的合理取决于生产力发展水平——收入偏低,就不可能有合理差距;效率低下,收入水平偏低,产品的供给不充裕,公平就无法实现。以公平等同于机会均等来说,假定效率不增长,生产力不发展,机会均等的实现就会遇到困难。厉以宁教授对此从两方面做了解释。
一方面,机会均等并不是可以脱离生产力水平而单独存在的。市场经济越发达,市场体系越完整,市场机制越健全,机会均等越有可能实现。生产力水平与市场经济的发达与否,市场体系的完整与否,市场机制的健全与否都是相互紧密联系的。比如说,在劳动力市场不完善的条件下,劳动力这一生产要素的供给者就很难做到在劳动力市场上的机会均等,从而他们之间的竞争也难以在机会均等的基础上进行,在资本市场上也是如此。机会的均等只能在市场体系发展过程中逐步实现。即使国家可以以法律、法规中规定市场参与者的机会均等(如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反垄断法等),但如果市场经济不发达、市场体系不完整、市场机制不健全,机会均等的实现也会受到各种各样的限制。因此,提高效率,发展生产力,完善市场体系应当被置于优先地位。
另一方面,机会均等的实现与市场参与者有没有足够的市场意识、市场规则意识、机会均等意识等有密切关系。如果生产要素供给者缺少这些意识,不知道怎样参与市场竞争,不了解遵守市场规则的必要性和怎样运用市场规则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也不懂得怎样对待市场竞争过程中所出现的种种问题,或者在机会均等的场合不知道珍惜这种机会,在机会不均等的场合也不争取改变这种状况,那么即使国家用法律、法规对机会均等作了明确的规定,也未必能保证机会均等的实现。而生产要素供给者的市场意识、市场规则意识、机会均等意识的具备,则是以生产力以及市场体系的发展为前提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提高效率,发展生产力,完善市场体系理应被置于优先地位。
至此,我们或许不该再对“效率优先”怀有什么疑问了。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自然也就容易理解了:在经济生活中,要把增加效率,提高生产力放在首位;同时要注意机会均等条件下收入分配的合理差距,不使贫富悬殊或者让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超出合理的界限。顺应厉以宁教授的思路,如果我们做到了“兼顾公平”,也就是实现了收入分配的协调。走向共同富裕走向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目标,我们经常关注的摆脱贫困、协调收入分配以及缩小地区间差距等问题,说到底都是为了实现共同富裕这一最终目标。然而共同富裕毕竟是一个过程,该过程中必然有人先富,有人后富,因此也就有个相互帮助、共同进步的问题。其中涉及一些经济学的伦理问题,厉以宁教授为我们做了精辟的论述。
厉以宁教授指出,如果把个人劳动与经营的能力和积极性这一因素撇开不谈,影响收入分配的大体上有三种力量:第一种力量是市场机制——个人提供的劳动数量与质量究竟能得到多少报酬,个人的经营收入的多少,以及个人的债券利息、股票的股息红利收入等究竟是增加还是减少,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全都与市场机制的作用有关;第二种力量是政府——一方面,政府制定工资标准与工资级差,这不仅直接影响全民所有制企事业单位和政府机构中工作人员的收入,而且也对非全民所有制单位的工资标准与工资级差发生影响,另一方面,政府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如对收入偏高者的收入征收收入调节税等,对低收入者实行救济、补助和扶植等;第三种力量则是不大被人们所注意的道德力量——它是超出市场机制与政府调节的力量之外的又一种可以影响收入分配的力量。如果说市场机制的力量主要对收入的初次分配发生作用,政府的力量既对收入的初次分配发生作用(如“事前调节”),又对收入的再分配发生作用(如“事后调节”),那么道德力量则对收入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的结果发生作用。它影响着个人间的收入转移、个人的某种自愿的缴纳和捐献等。
在道德力量的作用下,个人收入转移与个人自愿缴纳与捐献的范围是较广泛的。比如说,个人自愿为家乡建设捐赠,为残疾人福利组织捐赠,向灾区人民捐赠,向各种文化、体育、教育、卫生、宗教团体捐赠等等,都是非强制性的,这些行为都与道德力量的作用有关。此外,党员自愿将一部分收入作为党费缴纳,也属于收入转移或自愿缴纳的范围。
道德力量作用下的收入分配与个人的信念、社会责任心或对某种事业的感情有关,基本上不涉及政府的调节行为。也就是说,这是在政府收入调节之后,个人自愿把一部分收入转让出去的行为。当然,政府的收入调节政策可能在这方面有一定的影响,比如政府在收入调节政策中规定,个人向慈善机构的捐献列入免税范围之内,这样就鼓励了一些人向慈善机构捐献。但这种形式的捐献与政府调节力量的作用有关,厉以宁教授这里提出的道德力量则是纯粹出于个人的信念、社会责任心或对某种事业的感情的。这样我们可以肯定,社会上有这种信念、社会责任心或对某种事业有感情的人越多,个人自愿缴纳或捐献的数额就越多,道德力量对缩小社会上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也就越大。就目前看,社会上可能只有少数人自愿转移出一部分收入,从而对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影响很小;但从长期来看,随着社会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进展,道德力量对于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是会逐渐地(尽管是缓慢地)增大的。
要实现共同富裕,除了道德力量要发挥作用,先富者对后富者进行帮助也是相当重要的。先富地区对后富地区的示范作用固然是帮助的一种体现,但具体的帮助则更不可少。
先富者之所以能够先富起来,同这些地区和人民的努力有关,但同样不能忽略的是自然资源状况、地理位置和历史条件,以及政府的投资、信贷和某些优惠政策。在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定时期内,政府给经济特区、沿海地区和某些大中城市以较多的投资信贷,以及某些优惠政策,以保证这些地区的经济较迅速地发展,这是符合国民经济整体利益的。而这些地区先富起来以后,不应当忘记这一点,因此它们有责任给至今仍然贫困的地区以具体的帮助,使后者也能早日脱贫致富。只有贫困地区也跟着逐渐富裕起来,整个国民经济才能持续、稳定、协调地发展,先富的地区也才有可能继续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先富地区对后富地区的帮助实际上也是自己的经济得以继续发展的一种保证。
先富地区可以采取横向联合、技术转让、人才培训、资金融通等形式来帮助后富地区,使后富地区的资源得到合理的开发,使后富地区的收入水平提高,居民购买能力增大,这些都不仅仅有利于后富地区,而且同样有利于先富地区。政府在这方面也可以发挥一定的作用。比如制定有关的政策,鼓励先富地区的企业同后富地区的企业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进行经济技术协作,直到建立紧密型的企业集团;组织后富地区的多余劳动力输出到先富地区去从事一、二、三次产业的工作;还可以组织各方面的力量推行某一先富地区对某一后富地区的“对口扶植”活动等等。
厉以宁教授指出,先富者个人的示范作用是重要的,但仅靠示范和鼓励不足以使贫困户脱贫致富,而需要有具体的帮助措施。在这里,我们可以先把基于道德力量的作用而导致的个人自愿捐献等情况排除在外,专就捐献以外的帮助贫困户的形式来看,具体形式包括:个人传授生产和经营技术与经验,个人传递商品与劳务的市场信息,个人带动相邻各户或本乡本村居民集资建立集体企业(包括一、二、三次产业的企业)等。个人的这些帮助贫困户的行为尽管是分散的、自愿的,但政府仍然可以采取一些鼓励性的措施来加以支持。
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共同富裕始终是一个根本原则。1985年,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在改革中,我们始终坚持两条根本原则:一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占主体,一是共同富裕。”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与共同富裕二者紧密联系在一起。厉以宁教授对此做出了自己的诠释:正是在公有制经济占主体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实现共同富裕,而共同富裕的实现又将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平均主义导致普遍穷困,这当然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而少数人富,多数人穷,同样不符合社会主义原则。在我国经济发展与改革的过程中,通过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的先富来带动和帮助其余地区和人民致富,这一目标是完全可以实现的。这也正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
阅读后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