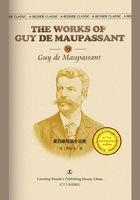这半年,也不知从哪儿吹来一阵风,说塔云电视台“文苑”栏目主持人吴无得了抑郁症,还有什么失眠症、暴食症……引得好些市民不由得特别重视起这档节目。一则想看看得了这么多病的人会变成什么样子,在本地,吴无好歹算得上一角儿了,当然也有人说她就是一花瓶;二则或是想不期撞上哪段节目特别是现场直播的节目因她这些病症突然出现什么乱子,目睹那一刻,好比收藏了错版的邮票或钱币,自然会稀奇好一阵子。
屏幕上的吴无依旧光彩照人,口舌生花。这不免令盯着她看的观众有些失望。电视机前一天天泛起很多争论,有人说她接受了心理治疗;有人说她是遭情敌诬陷;有人说她和某名流关系更密切了;有人说她做了乙商贾的地下情人;还有争论说她就要辞职了,就要结婚了,就要出国了,就要皈依佛门了,也有人说她信的是基督念的是《圣经》,林林总总。
时至今日,每周二晚上九点,吴无仍准时出现在塔云电视台文化频道“文苑”这个栏目,让我诧异的是,这些飞短流长的日子里,她整个人和她主持的节目竟然在众目睽睽中更见风华了。
一天,我在网上无意间进到“黑夜的爱女”的博客,接连着看了博主二十来篇博文,越看越觉得这“黑夜的爱女”极似吴无,只因网络浩渺,博主的档案又空白,不能完全断定。根据博文况味可以推测的是,博主也是常人眼中花瓶似的圈内人,也有诸如失眠之类的亚健康症状。借得网络一扇虚掩的窗子,可以让人看到一位外表光鲜内心困顿的女子在尘世中斑驳零碎的影像,亦不失为一场梦境般的邂逅。
沈复在《浮生六记》中观夏蚊、虫蚁皆有物外之趣,我在这个冬日的午后,共着和煦的暖阳看到一只花瓶的内里,想来也是流年中的一声唏嘘。
我所阅读的这二十来篇博文,有些整篇愁风苦雨,那些风那些雨或多或少映入观者心目,只有些许沁凉并无大碍;有些篇目琐碎散杂,却也符“见渺小之物必细察其纹理”的窥中之趣。总的说来全部博文因博主刻意隐去了一些私密,看来都有点摸头不知尾,不过,只要不把博主完全等同于我们这个城市的吴无或其他城市的罗无、王无、宋无……也就不会要求那些断章在通常意义上的完整和连贯了。
这二十来篇博文,长短不一,繁简不等,排列又有些凌乱,为方便有兴致一览者,我把“黑夜的爱女”长吁短叹之篇归为一札,名《无根的花枝》;把“黑夜的爱女”絮絮说事之章归一札,名《半瓶水》。这无根的花枝和半瓶水正好是花瓶里面的内容物,看惯了瓶外的奇花异朵,一窥这花瓶里面的内象兴许真还另有洞天。
无根的花枝
(一)
昨夜,又失眠了。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就与失眠这个魔鬼纠缠在了一起。黑暗中,它对我无比迷恋,它似乎看出了我对它也不能相舍,它的殷勤更加长驱直入了。它的舌尖舔着我的每一根神经,一更复一更,在所有夜深人静的时候,它用它的赖皮告诉我:只有它在陪伴我,只有它能抚慰我。
我的睡眠是干涸的河床上流失了的水资源。令人痛心的是,它得不到任何补给,它带走了我甜蜜的笑容、平和的态度甚至善良的心意,我不能再真正活泼地度日。没有人相信我有多么疲惫、多么虚脱,多么不堪一击。
可我还在征战。
当我的心灵披上戎装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我要夺取的是什么。往往被世俗所垂涎的,就成了我一时的目标。
旌旗已破如发丝,我的目光还在夕阳中矍铄。直到黄沙圆润了地平线,大漠中只剩得风在迂回,卸下铠甲的心才喃喃自语:我真的无意获取什么,别说与人相争,就是上天赐予我的一切,我也会如数奉还呀……
我总是在全身痛楚的那一刻才能放开眼界,放眼我过去和未来的日日夜夜,每一幅影像无不泛出旧照片的昏黄。昏黄,这是生命中多么缱绻的色彩,我迷恋的其实向来就不是光鲜和明艳。
失去睡眠,再不能进入梦的境界。那片柔软的土地,对我插起了“游人止步”的告示牌。我的每一天只能真实到不能再真实,坚硬得不能再坚硬,它们像雪地里的阳光,白惨惨地刺着我的双目,我想合上它们,可合上跟不合上又有什么两样?脑子里、眼睛里仍然是这无比真实而坚硬的白。
有些夜晚,我逃入他的怀抱,甚至想在性的岩洞里深居简出,不知晨昏,无论魏晋。
以这样的病残之躯待他,我不知带给他的究竟是火焰还是灰烬。如此,我又求他什么呢?我的心不是说过吗——
就是上天赐我的一切,我也会如数奉还。
(二)
我们越走越近,目光、呼吸、肌肤、习惯、声音……渐次都贴在了一起。原本两个世界的人,凭着错乱、狐疑、猥亵或许还有更不堪的缘由,生生要在这个时节拉扯出一段故事。
这个时节,正正经经的世界也许是一片了无生趣的墓地,我们就是悄然出游的两个魂灵。很多个夜晚,我们都在更为僻静的角落久久相视。面前的酒水也顾不得吸饮,只把对方静静地凝望,似乎要苦苦地辨认,你是不是我的前世,我是不是你的今生……
我们蜗居的这个隐秘而简陋的住所,似乎比许多一应俱全的人家多出一种气氛,每当倦鸟归林的时候,就把两个魂灵如两粒尘埃般从这个城市的皱褶里吸引出来,聚在一起,任他们在此过上一段升腾起人间烟火的时光。
我们在这里,没有任何作为,除了吃,便是睡。
时间从房顶流过、从窗前流过、从枕边流过,我都听到了那年华消逝的声音。他的起身每次都意味着从一个世界切换到另一个世界。我的回眸依然是沉坠,我不知道该怎么振作,我还在静听年华消逝。
刚开始,我会在日历本上,把我们同住在这里的日子画个圈,而现在,这样的圈好久没画了。
我不是忙得没这点闲暇,也不是散漫得没这点恒心,我是压根儿就把这些小动作搞忘了。
前天早上,离开那里之前,我试图把近来欠缺的圆圈补上,可是我已经记不清楚我们哪天在一起,哪天没在一起。我想回想一下,我的大脑却像一匹不肯吃回头草的马儿,倔犟着不肯转身换蹄。
(三)
很久没有做梦了,今天坐公车上班,车上,竟听得这样一段有关梦的谈论。
甲女对乙女说:“假若我在梦中遇见了他,并且跟他有了肌肤之亲、云雨之爱,你说,第二天我和他在现实中真正见了,他会感觉到什么吗?”
“不会,那是你的梦。”
“可我看他的眼神一定和以前有些不一样,我们之间毕竟有了一种关系,虽然无形,但它是存在的。”
“是啊。”
“我就在想,要是有谁能够掌控梦就好了。比如,我今天要找他办事,掌控梦的这个人就让他在头天晚上梦见我,跟我有肌肤之亲、云雨之爱,第二天,他见了我,或许会念及什么,而对我格外关照。但这一切都源于他的内心活动,我什么都没有付出,也什么都不知道,最终得了好处还不需要给他道声谢。”
“那要是你在梦中惹恼了他,不是反倒影响办事?”
“但他肯定也会暗自在意我,毕竟我们在梦中有过照会。这总比不被他注意好。”
“你看,我们每天醒和睡的时间几乎是相等的,醒着我们穿行在这个世界,梦中我们活动在另一个空间。我现在特别想这样:当我在梦中很美好的时候,我把它们当成现实来享受,当我在现实中很痛苦的时候,只把它们当成梦来体验。”
“对对对,我也要想这样。活着其实就是感受嘛……”
她们一路都谈着梦,我突然觉得这两位凡俗的女子竟像两位仙人。她们多么骄傲多么曼妙,梦好像是她们的后花园,她们生命的另一个世界,伸只脚就去了,抬只腿又回来了。
而我,被梦拒之千里之外的我,真正失去的还不只是这座后花园,我失去的是生命的另一个世界。
(四)
今年的时间似乎比以往的任何一年都过得快。以前,我总害怕黑夜的到来,现在,我害怕黎明的到来。没有人知道我陷在一块沼泽地里,只有我的身在告诉我的心:我们在沉陷,在沉陷……
若我有救
你可以伸手渡我
若我无救
你尽可冷眼看我
花自飘零水自流
……
这是我迷迷糊糊中在夜的最深处发出的求救信号,夹着泪光夹着笑靥的这个信号泥沙俱下,它在漆黑的天空中散开,烟花般绚丽了一时。
为什么要在生命的旅途中一次次自戕?我不明白,外在的我挑衅内在的我,灵魂和肉体同室操戈时,我是在等待救援还是在等待忘却?
一路走去,此行是不可生还的。
这是我唯一深信不疑的真理啊!我为什么还心存侥幸?
我放走了多少生命因子,我的所有年华都是一双凄迷的眼、一颗哽咽的心。
曾经,我在孤独中求得了安宁,那时我的躯体是一座城池,只为守护一盏烛光。那时,我是无争的,我相信苦难也必定踌躇在门外。那时,谁也不敲我的门。
为什么幡然醒悟了的我还会重蹈红尘?夜色裹挟了我,我看不到那是我自己。
纵使这样,我对世界最终剩下的情义也将是感激。我对我厌的人的感激甚于我对我怜的人的感激一如我对厌我的人的感激甚于我对怜我的人的感激,我对我身的感激甚于我对我心的感激,我对他对我残忍的感激甚于我对他对我宽宏的感激。
如此,漂泊的心终或可能在夜幕再次盛大开启时,静静凝固成一座孤寂而端庄的城。烛,消融得只剩下短短的一截了,我,也没有惶恐。
(五)
又有很长一段时间没写博文了。
我害怕面对那可以翻动的、哗哗作响的镜子。我的形容枯槁、我的面目遍布尘嚣,可是我看不到这么糟糕的事实,我看到的只是闷热的空气和弥散在闷热空气中的那滋味怪异的灭蚊片的幽魂,我们相互吞噬着,一夜又一夜,只待谁最后落得一堆尸骨。
在这个简陋的巢穴,我的心终究简陋得只剩下一张硬板床了。
(六)
他总是以同样的方式惹恼我,我也总是以同样的方式制造出一派不同凡响的回应。这对几乎没有任何变数的前因和后果,越来越分明地呈现出一种规律,就像化学试验室里,把一种试剂滴入一种物质,这种物质必然会因此而引发一场反应。
不同的是,昨天我的反应似乎由量变引起了质变,一时间,让我想倾力捣毁什么,彻底颠覆什么。我把身边能拿到的所有东西都朝他噼里啪啦地砸了去,包括那只玻璃壶。
事过之后,我发现他脸上有三处明显的伤痕,一处就在左眼内角之下,离他的眼睛仅差两三毫米。
是上天在保全这场游戏的最后一丝底线,还是谁在那一刻护佑着两颗卑微不堪的魂灵……
我总是在看见伤痕时才感觉到恐惧,而在我去抓去撕去撞击去打倒一切时却浑然不觉。我为什么要把自己推入险恶的旋涡,我为什么非要面对那些恶俗的捉弄和挑衅,而把自己武装得更加恶俗?也许当时我以为这样能给自己穿上一身铠甲,箭不穿,刀不入,事实上我为自己披上的是一件掠心夺肺的魔裳。
我知道,我正日复一日地失去着能让自己走出泥潭、免遭涂炭的一种精神和力量。我正如一粒尘埃在辗转着翻飞、沉坠,就为那些最不齿的缘由落入俗套的最低、最低之处。
他是什么样的人,我真的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了,然而清楚这些到底又有什么意义?如果说三年前我的闯入只是为了潜伏在一段尘事之底,未免太自欺欺人。当初,我何尝不是为了一声召唤应声而来。只可惜,真真幻幻、虚虚实实的错杂交替,让本来就混沌的我更加混沌了。
我终于感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孤寂,因为我和我自己几乎都分道扬镳了。我不知道我在做些什么,我还有期待吗?我还有挚爱吗?我还有欢笑和泪水吗?我竟不得而知。
天地间,我还是那个举目茫然的我。
(七)
还好,昨晚终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一会儿。虽然入睡的时间很晚,醒的时间又很早,连一个梦都没有镶进去。但窗外的雨不知是什么时候下起的,我由此推测,下雨那阵很可能正好是我睡着的时候。
这已经很好了。现在对我而言,睡眠就像盐对菜肴一样,只要真正能够撒入那么一小撮,我的整个精神状态就不会寡淡无味。
躺在床上,我想我这个人其实对什么都需求不多,就说最稀罕的睡眠吧,一夜能有两三个小时我就很满足了,有四五个小时就很欣慰了,有五六个小时就会受宠若惊地觉得受之有愧了。其他呢,饮食、财物、名誉、情欲……我真正的需求量更是少之又少,所以,我劳心又劳力赚来的一切,终归都将浪费。
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筑木屋栖居,他以自己为实验得出一个结论:人要维持生命维系快乐、幸福的成本是很低的,这于我是多么适宜。
我的生活是该由加法变为减法了。我真应该把欲望天空中的十个太阳射下九个。如此,我的心田才会长出嫩绿的草尖,风吹云起,月黑天高,草尖上的蚱蜢才会一伏一跃。
所以,对他的态度,我早也该做减法了,我何苦那么在意他对我是真是假,是虚还是实呢?
我要给他自由,我要给任何一个我曾约束过的人自由,包括我自己。
(八)
还有几天,除夕就要到了。
这一年,做了些什么?脑子里竟一片茫然。我不再像从前,深深地迷恋每一份获得,痛楚地惋惜每一份失落。我现在就像一座失灵的天平,已计较不出爱与恨、苦与乐了。什么东西,往心头的托盘上一搁,也就是一搁,顶多“当”地跌下去,除了一声机械的回响,再也没有什么锥心的痛。这些东西,哪怕积压已久,一旦取出,心灵托盘下的弹簧也只会嘣地弹跳回原位,晃荡两下,就空落得连空落也不见了。
从前的心,哀伤会痛,欢喜也会痛,多么清晰而精密的痛,它能证明我鲜活地活着。
这没有“痛”的如今,是我生命的偶然还是必然?
(九)
我们就要走到尽头了。
倘若在半年前甚至在两三个月前,与之分手言别,我还会怅然。现在,就这样让这个崎岖三年的故事戛然而止,我竟如此心平气静。一丝丝略带苦涩的庆幸细雨般凭空飘洒,让我在这浸透寒意的冬日渐地清冽。
我怎么会滑入那个幽暗的深谷?谷中的险恶和惊悸难道都不曾料想?
一开始尚知道有片雾霭笼罩在眼前,遮掩着晦涩、缥缈着嶙峋,时空恍若魔境。没有心惊,也没有胆寒,我故意化作伏地而行的野苔,越是沟深壑险,越要使尽苍翠把层岩晕染。
那时候,一切俗与邪都是我眼中的景致,我就是借着它们去看人生看世界看自己。俗小了,邪浅了,似乎还不能让我震颤。一度,我细致地体验着被磕着、划着、搏着的疼痛,那种心抖手抖泪光抖抖的场景,让我相信我还爱着别人爱着自己,我还爱着爱。
这三年,我对他的了解似乎深了一层,只可惜这浅浅的一层,也耗去我三年的光阴。我向来是这样的,什么都得靠时间去换,这种调换就像用金币换镍币,可我还是一误再误,甚至还要误下去。
所有故事的情节仍在不断地被重复,它的单调终使我犯了类似审美疲劳的审俗审邪疲劳症,很快,对于它们,对于我自己,对于曾经谙以为是的魔境,我都失去了揣摩、观察、体验、分析、记录的力气,我对这一切都困乏了。
我应该忘了它们。
我知道,对于而今的我来说,忘却什么几乎最不费工夫。我的记忆出了毛病,如果不凭借我当时写下的文字,很多事我都记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