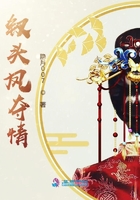林平之帮她把眼泪擦掉,又哄着说:“别哭了,晓梦,我错了。下次再不了,啊?”
庄晓梦不言不语。
林平之说:“我感觉还算比较谨慎的人,安洁是怎么知道你的手机号的呢?还找你谈判的?是不是有一天你跟我说过,曾经有人跟你打电话却不说话?”
庄晓梦想起来了,说:“是的,前几天就是这个号码打的电话,当时我不在意。”
林平之说:“我都给你说了,想从此对你不用再藏着掖着,你的心病也都解开了。虽然眼下你可能受不了,长远看,未必就不好。”
庄晓梦对他冷冰冰的。
他继续说:“答应我,别再为自己赌气了,行吗?”
庄晓梦说:“掏心窝子说,自从认识你一直到现在,我对你怎么样?”
林平之闷闷地说:“对我不错,我记得。”
庄晓梦:“你对我呢?如果你跟那个女人悄无声息,我不知道,那我还傻傻地幸福着,可现在呢,她的电话都打到我这了,你让我怎么办?你让我怎么办?”
林平之继续说:“现在就是这个社会,我只不过犯了所有男人都会犯的错,何必这么折腾呢?”
庄晓梦声嘶力竭地说:“不要找那些扯淡的理由了。”
林平之说:“我说这些不是为别的,主要是想让你别闹腾了,她给你打电话是让你难受,让你过不好,你老生她的气,不就中了她的计了?你想不明白啊?”
林平之气急败坏地给那个女人打电话,那边没人接,他就给她发短信,那边也不回。气得他在屋里团团转。
林平之说:“她这是自己过不好了,也不让别人过好,你不要把她当回事,好吗?”
庄晓梦说:“你把我的热情都烧完了,你就是我的火葬场。”
林平之说:“这话说的,怎么悲剧意味这么浓啊。”
随后,两人躺在床上不言不语。
以后的几天里,庄晓梦感觉自己脑子跟浆糊似的,别人说话她就支应一声,自己坐在那发愣。晚上老跟林之唠叨这个事情。她感觉林平之有一种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感觉了,但她还是感觉心里堵得慌。
一天晚上回去,庄晓梦说:“你还有什么事没给我说呢,都告诉我。”
林平之说:“这个你真没有必要追根究底的。打破砂锅问到底有什么好处呢,砂锅也就破了。”
庄晓梦说:“我就是死,也要明白我是怎么死的吧,不能糊里糊涂就死了。”
林平之沮丧地走到客厅,过了一会儿,又转回来对她说:“晓梦,你老这么闹腾我也受不了,就算判刑,我也有个替自己辩护的权力利吧?”
庄晓梦压抑地说:“你有辩护的权利,你说。”
林平之为自己鸣不平似的,说:“你的****里******藏着多少故事,我怎么知道呢?我就这么搞一下你就受不了了。”
听到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庄晓梦顿时说不出话来,一下子瘫在床上,她看到内心深处潜藏的那块到现在快要平复的伤疤,被一把刀重新剜了下来,然后裸露出血肉模糊的一片,血是一种喷涌的状态,而不仅仅是一滴一滴地滴答。
她感觉时间被拉得很长,然后缓缓地说:“历史是历史,背叛是背叛,能划等号吗?很多人都能接受一个人惨淡的历史,但是不能接受背叛,我难道能接受你的背叛吗?”
林平之恹恹地说:“我他妈够倒霉了,找老婆找了个二手货,我想哭都没地方,我招谁惹谁了。”
庄晓梦:“林平之,因为这事你打算拿捏我一辈子吗?”
林平之好像很生气,说不出话来,甩门出去了。
理智告诉她,林平之的天平在她身上,而没有在安洁身上,他没有给安洁什么希望。但她就是受不了、受不了,很多女人遇到的事情,她也遇到了,她就是受不了,失去理智、歇斯底里地受不了。
但是她心里并不是只有这一件事,她想的是,这辈子就这么完了!她对事业没有什么追求,自己只是个小小的经理,就像某些人说的,只是一颗小草,就生活在泥土中,被很多人踩着,别人也不会对自己的痛苦产生怜悯,因为看不到你,就是看到了对你也视而不见,这个就认了,毕竟这个世界上树少草多,自己没有成为一棵树的本事,虽然工作也不容易,但都是为了这个家,她几乎所有的努力、所有的付出都是围绕这个家来展开的,然而现在,婚姻支离破碎,她以后不再信任林平之了,这种理想生活也灰飞烟灭,林平之的态度又把她原来的伤给挖出来了,事情就怕凑到一块,受不了啊,受不了。
那自己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好像只有孩子了,孩子是不是一粒树的种子,还不明朗,还是未知数。就为了林平之这个事情而离婚吗?离婚就是彻底失败,为什么需要不断地向现实妥协?
美好的时光就这么翻卷着溜走了,自己也努力地想抓住,但也没抓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