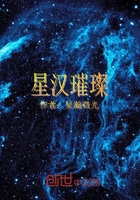澹台文清噗地一下笑了出来,勾着他的肩,邪魅问道:“怎么,你羡慕啊?”
“七公子!”小安子涨得脸通红。
“七弟!”澹台凤鸣略略提高了声音。
澹台文清摊了摊手,踱到一旁:“我是看大家都太严肃了,开个玩笑让你们轻松一下。既然你不喜欢,那就算了。”
“何婉仪不愧是花魁,门庭若市,每日慕名前来找她的人络绎不绝。”上官雅风道:“属下已安排人过滤她所有的客人,另外……”
正说到这里,忽见鹰满脸喜悦地从门外大步走了进来:“公子,葛副统领也来萦州了?”
澹台凤鸣一惊,蓦地转头望向上官雅风,眸光冷厉:“怎么回事?”
“这不可能!”上官雅风断然否认:“属下派他去波罗郡探查荣王,怎么可能出现在萦州?”
“你确定没有认错人?”上官雅风狐疑地问。
“属下与葛副领共事二载,朝夕相处,如今虽已阔别三年,又岂会认错?”鹰觉得这问题简直是污辱他的智商。
“既然不是鹰看错,那就必然是葛副领抗命,阳奉阴违为,秘密来萦了。”澹台文清冷笑。
“你没有把公子的行踪泄露给他吧?”陈风急了。
“怎么,”鹰一脸茫然:“这事不能告诉葛副领吗?”
“哎呀,到底有没有,你倒是痛快点啊!”小安子急得跺脚。
“他刚下船,应该没看到我……”鹰摇了摇头:“老爷从矿场传了紧级加密消息过来,我没敢耽搁,想着他来了萦州反正是有机会见面的,也就没过去跟他说话。”
“那就好……”上官雅风松了口气。
澹台凤鸣冷哼一声,淡淡地道:“若不是嗅到什么气息,他哪会从波罗郡赶到萦州来?”
“这么说……”小安子一惊:“公子来萦州之事已然曝露了?”
“那倒未必。”澹台凤鸣冷笑:“皇陵守卫森严,我又下了严令,祭祀期间没有钦命不得擅入。他们就算有所怀疑,没有确切的证据在手,也无法证实。想来葛易秘密来萦,必是前来确认真伪的。”
问题是,在对他的身份进行确认之后,仙阳教究竟想要做什么?
是小心掩饰行藏,以防被他揪住尾巴;还是索性孤注一掷,冒天下之大不讳,弑君攥位?
“那咱们要不要换个落脚点?”陈风问。
“萦州仙阳教耳目遍布,不管换到哪里,都是一样。”澹台凤鸣淡淡一笑:”不过,他既是秘密来萦,必不敢与咱们正面碰头。”
“对!”澹台文清笑着插言:“他就象是一只苍蝇,虽然惹人讨厌,倒尽胃口,却并不影响大局。四哥……”
“你说,”澹台凤鸣不理他,把目光转而望向鹰:“席翰林传了紧急加密消息过来?”
在这节骨眼上,矿场可不能再出事了!
鹰一惊,急忙从袖中取出一只蜡丸,恭敬地呈了上去:“蜡丸在此,请公子过目。”
小安子急忙上前两步,接过蜡丸转呈给澹台凤鸣。
澹台凤鸣捏碎蜡丸,拿出纸条,展开一看,顿时面色一沉,悖然大怒:“一群废物!”
“出什么事了?”他遇事从来不慌,如此盛怒极为鲜见,众人不觉面面相觑。
澹台文清急急凑了过来,瞄一眼纸条,不禁倒吸一口冷气:“仙阳教的奸细混入矿山,并且扬言炸毁钢厂!席大人请四哥从速赶回矿场,主持大局?”
“什么?”陈风等人相顾失色。
钢厂被毁事小,若是此事传扬出去,皇帝苦心积虑,掩盖了数年的计划必然曝露于天下。
那时,不但不能制肘乱党逆贼,反而授人以柄,及有可能引发一场空前的浩劫!
“阁主,葛统领求见。”婢女轻叩门扉,低声禀报。
云罗衣挑眉:“他亲自来了?”
葛易不请而入,睨着她邪魅一笑:“怎么,阁主不欢迎?”
云罗衣端坐不动,淡淡地道:“葛统领是教主跟前红人,小女子只是区区一个山西阁主,又岂敢怠慢?”
“阁主这么说就见外了……”葛易大笑,颇有些得意地道:“大家都是替教主办事,哪有什么红不红?若真要说红,葛某又哪有阁主雄霸一方,手握实权来得威风?”
他一边说话,一边向她靠近,伸手就要不着痕迹地搭上她的肩。
云罗衣杏眼一瞪,冷冷地道:“葛统领,这里可不是万花楼,本阁也不是倚门卖笑的娼……妇,请自重。”
葛易被她夹枪带棒一刺,顿时下不来台,讪讪地退了一步,拉了张椅子坐下。
“说吧……”云罗衣俏脸冷凝:“葛统领不请自到,不知有何贵干?”
“阁主真是贵人多忘事,”葛易干笑数声:“不是阁主亲自写密信入京,要求核实凤四和凤七的身份,并决定下一步行动计划?”
“这种小事,不需要劳动葛统领亲自前来吧?”云罗衣冷然质询。
他冒然前来,若是被凤四凤七撞个正着,既曝露行踪,又易引起他们警觉,实在是有百害而无一益之举!
“有没有必要,是教主决定,不是你我说了算,不是吗?”葛易收起笑,淡淡地刺了一句。
云罗衣一怔:“教主亲自下令命你前来?”
“教主闭关修炼七重阴阳决,教中事务由左护法全权负责。”葛易心里颇不是滋味,表面却装得云淡风轻。
“傅韶华?”云罗衣冷哼一声,没再吭声。
“阁主!”婢女忽地走了进来,低声禀报:“何香主求见。”
“她又来做什么?”话没落音,何婉仪已推门走了进来。
云罗衣十分不悦,乘机将怒气撒在她身上:“现在是怎样?全不把我这阁主看在眼里了?”
“阁主……”何婉仪被训得莫名其妙,瞠大了美目看着她。
“算了,”云罗衣揉了揉眉心:“说吧,什么事?”
“陈翔送了信来,凤四那伙人刚刚离开别院,往码头去了。”何婉仪急急地道:“属下特来请示,要如何处理?”
“他去码头干什么?”云罗衣沉吟道。
刚从席家炭场回来,总不能又往渡江往黔州去吧?
“莫非,他们察觉到了危险,想溜?”葛易神色阴鸷。
“据陈公子说,凤四一伙神色焦急,象是出了什么事?”
云罗衣冷声命令:“让人紧紧盯住凤四,务必查明原因,绝不能让他逃走!”
“还是我去吧……”葛易起身:“一则可以早点确认他的身份,二来也好相机行事。”
云罗衣点头:“有葛副领坐镇,本阁也可放心。”
“阁主放心吧。”葛易冷笑:“若他真是那人,这次就是咱们立功的好机会!”
“本阁等着你的好消息。”
夜幕笼罩着群山,一弯弦月挂在山边,给连绵起伏的山峦镀上一层浅灰色,一切都显得那么沉郁,苍凉。
澹台凤鸣一行人抵达矿场的时候,已是酉时三刻,距上一次爆炸刚好一个时辰。
随着轰地一声巨响,冲天而起的火光与浓烟如同礼花般漫洒了天际,给了他们当头棒喝。
澹台凤鸣的脸当即黑得如同锅底,就连澹台文清也不敢再插科打诨,凛着容,一脸严肃。
席翰林站在码头上,不停地抹着额上怎么擦也擦不完的冷汗,腿软得直打颤。
“说说吧,究竟怎么回事?”进入庄院后,澹台凤鸣并不进屋,直接在院子里开始质询。
“臣在黔南招募工匠,今日晌午才赶回矿山……”席翰林满头大汗。
“有几个时辰,难道还不够了解事情的全部经过?”澹台凤鸣目光有如鹰隼,锐利冷酷得让人心寒。
席翰林一震,急忙道:“属下查过了,跟之前仙阳教的奸细不一样的是,这次他们居然混到矿工中去了,还谎称找人。”
澹台凤鸣怔了怔,问:“他们要找谁?”
“周大橹,周家屯的渔民。”席翰林忙回道:“臣已反复讯问过他无数遍,他说不认识。现已押在厢房,公子是否在见他?”
“他为何不一次将钢厂全炸了,却隔一个时辰炸一座?”澹台凤鸣再问。
“呃……”席翰林抹着汗道:“那是因为他的同伙在突围时失踪了,他要逼我们帮他把那个同伙找出来。”
“一共有几名奸细?”澹台凤鸣冷声道:“逃走了几个?还有几个藏在山里?”
“一共有多少尚不得而知,”席翰林满脸惶恐,低声道:“但下到矿洞里找人的只有两个,确定为一男一女。男的武功极高,轻功更是神妙,侍卫好几次将他围住,都被他逃了出去。”
“轻功高妙?”澹台凤鸣心中一动,淡淡地问:“依你之见,雅风的轻功与之相较呢?”
“呃……”席翰林苦笑:“臣非武将,又未曾亲见,实在不好说,不好说啊。”
“那女的呢?可曾有人见过她什么模样?功夫如何?”澹台凤鸣点了点头,转而问了另一个问题。
“相貌很是普通,不象是学过武功,招术怪异之极,但出手就是致命招术,也不知是何来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