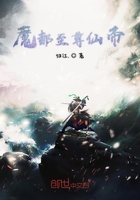迷离夜色,笼罩在旻国王宫后苑。隐约间,依稀可见千万间古色古香的琼楼玉宇,红墙绿瓦飞檐斗拱的交错其间。古木繁花、亭台楼阁、嶙峋山石、石子阶路……绵延数里的荷花池畔,荡漾着清幽漫漫,淡淡的水烟弥漫,勾勒着仙境般的梦幻凄美。
此时正值初夏时分,夜幕虽然障住了无限妍丽,却难湮没那株株俊秀、朵朵奇芳!清风缕缕一股芬芳四溢,风吹花落,铺地数层,唯见后庭清雪初降,甚是清丽。
月华铺落,斜倚阑干的一双人儿,素影清映,将醉景红苑点妆成一幅旖旎的山水画。
蓝衫少年仰头伸手掬一轮皓月如雪,妙音泠泠若美玉轻扣,感触淡语:“这景云殿,上次踏入,见到的还是坐于这廊中亭下的摄政王武寻芳。如今踏入,却只剩开得遍地的百卉如云。”
云卿青衫盈贵,立于阑干临风身旁,月华却撒了他满满一身。清玉面庞恰似好雪,又似琉璃绚烂:“怎的想起那人来?”他将投放在花苑中的眼神,转首投着她,狭长的丹凤眼上,却带了些许促狭:“还偏偏是旻国受人唾骂的野心家。”
兰临风闻言,欲言又止的唇,最终却只能抿住。而那抿成一条的直线,却似充满着某些难言的复杂与懊悔。
自四十年前旻国嫡长武寻乐继位三载却早夭去世,留下四岁遗孤武长龄。武寻芳便以王爷之身开始摄政。哪知武长龄长大却成了个浪荡庸主,以致后来****。说来可笑,昏君一生浪荡,却偏偏所生子嗣,不是早夭,便是失踪。这武寻芳不知从哪里查到游荡江湖的武承义乃是旻国遗孤,竟不惜使出千方百计逼武承义回来继位……
四十年匆匆而过,往事如烟。当年武寻芳那老家伙为了逼武承义继位,不惜使劲万般手段,甚至波及了自己。得知缘由的自己亲自前往旻国跟着老家伙斗起法来,甚至不惜将他的名声搞臭。
周公犹恐流言日,王莽谦恭未篡时。
这老家伙摄政四十年,偏偏还得了个“贤王”的名号。以她素来看待政治人物的经验,他恐怕也不过是舍了个虚名,却将全部美名尽得于身。据说,武寻芳摄政四十年,兄长早夭、侄子荒淫、还是王嗣难存等一系列接连发生,似乎是老天让他这个摄政王不得不摄。
难不成天下还能有这么巧的事?她一听武寻芳一系列摄政经历,自诩聪明、先入为主的判定——事出反常必有妖,诸多巧合,必是人为。
可是……兰临风看着此时景云殿繁花盛景的景象,眼中却含着点点荧光。不知道为何,即便当年武寻芳死在跟前,她都没有多少动容。可如今,却为何偏偏……望着眼前的山野别居,兰临风率先走了进去。
山野别居曾是武寻芳住了四十年的景云殿一处院落,这里面没有殿外华丽的沉香水榭,没有假山玉石,没有舞娘美婢;更没有笙箫急管,佳肴贵器。有的,只不过是一处沁心怡情的碧玉湖光,旁有一座小小竹楼,和一浑朴“沧浪亭”。
当那所熟识的竹楼和亭子映入眼帘时,耳边,似又想起那些曾经在沧浪亭下与武寻芳好一番谈古论今,以及这老家伙所说之言——
“既入政治,便绝无悔途,更无对错。左右不过胜负输赢的问题,还怕道德二字蒙上污点?”
“只要站在政治的巅峰,不管你本心如何,都必须是承受诽谤的载体。不过是有得必有失罢了。”
“洪荒不容,天地弃之,史上谁可败携芳名照千秋?”
“天何生我武寻芳?既生吾于乱世,又何让乱世生吾暮年之际?”
“……”
兰临风望着这夜中沧浪亭,神情中竟是鲜有的动容:“以武寻芳之慧,是否早已预料到今日?”
后面跟过来的聂云卿,却将自己身上的外套披在兰临风身上,嘴中说出来的话,却似有些酸:“这老家伙倒是好福气,让你念叨他至今。”
兰临风回头看着聂云卿在月华下的狭长凤眸,失笑道:“我念叨过这老家伙很多次吗?”
聂云卿看着兰临风毫无所觉的样子,简直是满脸惊疑:“怎么?你还未觉?不知道你在我看不到的地方如何。但在与我在一起的日子,至少也有五次了。”他将她身上的衣袍系紧了些,然后又道:“再加上今日,便是第六次了。”
兰临风骤然睁大了眼:“你竟记得这般清楚?”
聂云卿不假思索的接口:“你这一生,还未对某个人,如此念叨过。我如何能记不清?次数多得,我都忍不住嫉妒了。若不是看在他只是个故去的老家伙的份上,我都想将那人揪出来好好儿痛扁一顿。”
兰临风白了他一眼,失笑不已:“还真不像是你聂云卿做出来的事。”
哪知聂云卿却望着她,十分深情款款道:“跟你在一起的每一个时日、每一个片段、每一句话,我都恨不得记得一清二楚。”
夜幕笼罩中,兰临风带着血痕的脸,略微有些微红。可她不惯沉浸在那双清明的眸中,故转了话头道:“对于承义那些话,你怎样看?”
聂云卿轻笑,道:“你心底早已有数了,何必问我?若不是太过动容,也不会一路又走到这景云殿中,还进了这如今荒芜一片的山野别居。”他仰望星空浩瀚,繁星几许,眸中却充满迷蒙的岁月与落败的朝夕复道:“唉,在早些时候,我便觉得,承义跟我们这群人,多少不一样。这样的人哪……应当生活在另一个,梦一样的世界!”
兰临风和聂云卿对视一眼,同时从对方眼中看到自己眼中的复杂。
这个世界素来是如此的可笑——当你觉得它无比美好时,它却偏偏将一切丑恶通通扔到你面前,让你看清它的残酷。而当你认为它残酷时,它却偏偏要打破你自己所经历的认知,让你觉得自己不过是个笑话。
“临风!”在终于回到二人寝殿中的那一刻,刚想入殿就寝的兰临风忽然被聂云卿叫住了:“你信吗?总有人的存在,是为了打破固有的认知。不管是善恶、道德,或者是……感情!”
兰临风与聂云卿四目相对,似是要将对方那一双眼中的澄澈给望得清清楚楚。那曾经深藏如今却毫不掩饰的情感,恍如流云般直射人的内心。那一瞬间,她似乎感到心底莫名一颤,便直愣愣的往后退去。
她定了定心神,看着云卿没有外衣的身上,淡道:“夜深了,云卿,该回去休息了。”刚刚一只脚进了殿门,哪知一只胳膊却被他死死拉住。
她无奈收脚,却正好撞见了他深不可测的瞳仁中。下一刻,竟猝不及防的被拉入了那怀抱之中,紧紧箍住。
她刚想挣扎,却被他抱得越发紧了。她不由出声怒道:“聂云卿,你干什么?快放开我!”
“不放!”他的声却比她更高:“我告诉你,兰临风。自我心意埋下的那刻,便绝不容拒绝。不管你这个女人到底有多无心无情、没心没肺!”
闻听此言,兰临风挣扎的手蓦然停顿,脑海中却是那一日他自她殿中走出去的落寞身影。
不过好在,聂云卿似乎对她后面放弃挣扎的状态很满意。也只是抱了一会儿,便将满面空洞的她放开,只道了句:“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你去澳国吧!旻国有我。”便似怕她再说出什么话来,马上离开了!
兰临风望着那离去的背影,似有所失。张口欲言,却不知该说些什么。
终是被南殊的一席话影响了么?竟是不敢、不舍、不能,去再一次无情拒绝了么?
只是,这样下去,怎生是好?
本书由潇湘书院首发,请勿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