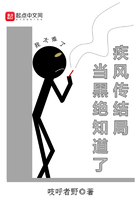九阿哥见她不但没有惊愕之色,甚至还陷入思量,用力叹了口气:“原以为十四弟此番建功回来,便是你与他的大婚之期。而今看来,还真是出乎意料。”
闵敏抬头看了一眼九阿哥,轻声道:“奴婢从未想过,万岁爷会把奴婢指给十四爷。”
九阿哥有些意外闵敏如此淡然。
闵敏接着说:“九爷如此机敏,难道未曾预料,奴婢身份如此尴尬,怎么可能简简单单跟了十四爷?”
九阿哥瞳孔轻颤,低头看着手中茶盏:“是啊,皇阿玛对你的信任,许多皇子都望尘莫及。想来你所知之事,也远甚我们兄弟。如今……如今尚未尘埃落定,果然是不能给你指婚的。”
闵敏叹了口气,觉得这个话题是真的聊不下去,抬头道:“十四爷这趟走的急,不知贝子可会差人过去?”
九阿哥吸了一口气,表达的也不知是对何事的叹息,他点点头。
闵敏道:“奴婢预备了些果脯小食,都是原来十四爷喜欢的,要劳烦贝子了。”
九阿哥点点头,示意她把东西拿来就好。
闵敏回到里屋,却撞见十三阿哥一副悠哉模样坐在里头,越发心思弥乱。只能先不理他,径直拿来东西交给九阿哥。
看他离开背影,闵敏立在原地,心里头五味陈杂。
她脑海里残留的那些对九阿哥的评价,似乎都没有什么好话。当然,这些评价本身就来路不正。就闵敏自己亲眼所见,八阿哥两次低迷时他的表现,十四阿哥在一废太子时候被重罚他也是一肚子火气,还有和四阿哥那种相爱相杀的微妙关系,让人越来越抑制不住归结到他义气重的性格特点上。不是说逢人只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吗?可是这个传说里的人精,总是给人一种掏心掏肺的实诚感。那种对康熙好恶的不避忌,对朝臣议论的置若罔闻。还有,明明自己也可以朝那个位子争一争的,却甘愿为他人做嫁衣裳,实在是不像一个精于计较的样子。
闵敏忽然对空气眨了眨眼,相爱相杀?为什么自己会用这个词来定义四阿哥和九阿哥之间的关系?只是早些年听九阿哥提过儿时两个人还算亲密的关系,或是潜意识里有了一些其他的观点?
闵敏用力摇了摇头,脑海里乱哄哄的念头闹得她心累。
在风里头总又呆了好一阵子,觉得心里头被九阿哥牵扯起来的各色思绪静下来,才转身回屋子里头去。
十三阿哥已经给自己倒了茶:“九哥过来,想必是给你传信的吧。”
闵敏给自己倒了杯茶,一仰脖都喝了,不小心被呛到,好一串咳嗽。
十三阿哥笑了:“瞧你这样子,应该是已经知道了。”
闵敏好容易才缓过来,侧头问:“十三爷说的是哪件事?”
十三阿哥道:“如此装傻,未免太无趣了。”
闵敏哼了一声:“难道十三爷过来,是要宽慰我万岁爷拒了十四爷的事情吗?”
十三阿哥也哼了一声:“你需要宽慰吗?”
闵敏反问:“为什么不需要呢?”
“你大概早就晓得,皇阿玛心里头对储位的打算。先前又提过可以为了你废除祖宗后宫不得干政的规矩,又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允了你和十四弟的婚事。你二人两地相思,春愁寂寞,真是不知几时方休了。”
闵敏看着十三阿哥,翻了个白眼:“十三爷,您有话不妨直说。”
十三阿哥喝了口水:“爷以为,跟了十四弟的念头,你可以断了。”
闵敏一惊,她似乎还记得,十三阿哥先前也曾劝过自己,要为自己和十四阿哥将来做打算,怎么今儿说出这样的话来。
十三阿哥又喝了口水,却说了另一件事情:“这一年多,你侍奉四哥文书的时日,竟比侍奉皇阿玛的时日更多些。大概除了西北战事和我这里的折子,就没别的呈到皇阿玛那里去了吧。“
闵敏知道他在暗示什么,作为一个知道历史结果的人,她什么意见都不想发表:“奴婢没有听错吧?难道十三爷是在暗示,若是雍亲王不点头,奴婢是没法许给十四爷的?”
十三阿哥早已习惯闵敏时不时全无规矩可言的回话,他倒不否认:“八哥和九哥还当皇阿玛暗自摇摆,全不如你洞若观火瞧得明白。”
闵敏道:“奴婢愚钝,不知十三爷说,八贝勒爷和九贝子以为皇上摇摆的,所为何事?”
十三阿哥道:“说起来,四哥早年和皇阿玛颇为生疏,倒是十四弟获封大将军王之后,和皇阿玛热络了起来。不论是地方政事还是西北军务,皇阿玛对四哥都多有仰仗,或许,这是谁都不曾想到的吧。”
闵敏的脑海中冷不防冒出来一个想法,不是说手握兵权还是最靠谱的吗?这个念头还没下去,另一件事情立即蹦了出来。是了,十四阿哥的军需后勤,都是年羹尧管的——这点,似乎四阿哥从未避讳让她知道。
闵敏忍不住回忆和四阿哥朝夕相对的那种生疏和冷漠,不由为他的面如止水生出胆寒的感觉。是的,她,洪鄂闵敏,虽然是假托三阿哥的名义入宫的探子。但是,仔细追究,她可是尚未发迹的年羹尧为四阿哥挑选的人。甚至是四阿哥和十三阿哥改变当差的行程,自己去亲自瞧过的人。按理来说,她入宫之后,耳目所见的一切动向,以此为凭的一切筹谋,往来奔走的一切行动,都应该为了这个主子。可是,不论是恢复记忆前的形同聋哑和明哲保身,还是恢复记忆之后一如往昔的事不关己,都是那么的不合常理。
她想,如果是九阿哥那种性情浓烈的人,大概早就使了绊子把自己除掉了。毕竟不能为己所用,又走在中枢机构,迟早是个祸害。四阿哥却迟迟没有动作,是因为不屑于做这样的事情,还是别的什么关系?那个神秘先生的声音再次在闵敏脑海中浮现,是啊,即便四阿哥日理万机运筹帷幄,下头的人也应该为他想到这一层。那么保持这种风平浪静的,是什么原因呢?
十三阿哥见闵敏虽不说话,脸上神色却是明灭转换,也不知心里揣摩些什么天大的事情,觉得有趣,忍不住想要打断她的那种深思熟虑:“你又在想些什么无用功的事情?”
闵敏翻了翻眼珠子,显然,她对十三阿哥打断自己的思路颇为不满:“既然是些无用功的事情,自然也没有必要说给爷听了,是不是呀?”
十三阿哥摇摇头:“罢了,算你有理。”
闵敏忽然觉得有些奇怪:“敢问十三爷今儿过来,该不会只是和奴婢唠嗑说些无用功的事情吧?”
十三阿哥笑了笑,从怀里掏了一沓信封出来:“喏。”
闵敏伸手接过,却忍不住有些晃神。是的,十三阿哥站队这件事已经铁板钉钉了,那么这些往来的密折,只怕四阿哥也心知肚明。难怪他会越来越招康熙的喜欢,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啊。“
“四哥并没有读过这些折子。”十三阿哥懒洋洋地瞟了她一眼,“已经没有必要。”
闵敏微微一愣,什么叫已经没有必要?
十三阿哥见她表情,又摇了摇头,依旧从后窗离开。
目送十三阿哥离去背影,闵敏幡然醒悟。
十三阿哥刚才毫无避忌的说,四阿哥没有读过这些折子。
但是,自己和十三阿哥的见面,应该也在康熙的耳目监视之下。
十三阿哥说话全无遮拦,只有一个原因。
那就是康熙身边的这些耳目监察,早已全是四阿哥的人了。
闵敏忽然起了一身冷汗,历史上似乎有传说,雍正有弑君篡位的嫌疑。
现在是五十九年,康熙做了几年的皇帝?雍正是哪一年登基的?
闵敏觉得头好疼,她完全想不起来,连一个大概,都想不起来。
大概是这日用脑过度,闵敏当天晚上就病倒了。强撑着身子把十三阿哥的密折给即将出京巡幸的康熙送过去,前脚出门后脚就晕倒在了御书房的门口。
这一次的病势来的实在是沉重,康熙巡幸畿甸出发在即,所以闵敏不可避免的无法随驾。昏昏沉沉里,似乎有人过来瞧过自己,但是实在是不记得了。
等到彻底醒过来,已经不知道是哪一天的夜里头。
闵敏勉强支起身子,只觉得眼皮沉重,头晕脑涨,分不清自己到底醒着或是昏着。
“你醒了?”
闵敏用力的眨了眨眼睛,定睛一看,在桌子边坐着的,居然是十三阿哥。
“姜薤白倒有些本事,他说了你今儿夜里头会醒,果然醒了。”
闵敏还没有完全缓过来,有气无力地开口:“十三爷吉祥,奴婢,奴婢……”
“罢了,都病成这样了,何必拘礼。”十三阿哥把一杯水递到闵敏嘴边,“况且,你在我的面前,不讲规矩的时候多了去了。”
闵敏侧过头,勉强抬起一只手,接过杯子,一饮而尽,喉咙口还是觉得干,可是又不好真的一点规矩不讲的差十三阿哥给自己倒水,拿着杯子的手便僵在半空。
十三阿哥摇了摇头,他伸手拿过杯子,倒满了水,再还给闵敏。
闵敏看了一眼十三阿哥,不再说话,还是一饮而尽。
就这样,也不知道喝了多少下去,才觉得嘴巴里湿润了点。
“姜薤白说了,你烧了好多天,醒过来必然是口渴难耐,多喝些水必然是好的。”十三阿哥把水壶和茶盏放回桌子上,又站到闵敏身边,端详了一番,道,“嗯,脸色也比刚才好些了。”
“十三爷,奴婢,这是病了多少天了?”闵敏犹疑着开口。
十三阿哥道:“打你昏倒在御书房门口算起,八天了。”
闵敏忍不住啊了一声,毫不掩饰自己的惊讶。
十三阿哥笑道:“总以为你身子瞧着单薄,但注意饮食养生,底子当是不错。真没想到,竟会上演这样一出病来如山倒。”
闵敏轻叹一口气,脸上不自觉的浮上了一丝难得见到的柔弱和无奈来。
十三阿哥也是头一次在闵敏的脸上看到这种表情,他瞳孔里有丝怪异的表情一闪而过。
闵敏觉得自己似乎看到了,可是又好像是眼花,她深吸一口气:“唉,奴婢也不知道。”
十三阿哥的表情正常的不能再正常了:“你这趟没能随驾,皇阿玛可是有些失望。”
闵敏尴尬地笑了笑:“奴婢又不是头一次没能伴驾。”
十三阿哥的脸色却有些微妙:“九哥看起来也有些失望。”
闵敏微微一愣:“奴婢每次伴驾出巡,都会做些有趣点心,九爷大约是因为这个失望吧。”
“是吗?”十三阿哥反问。
闵敏忽然想到什么:“十三爷,为何……你会在这里?”
十三阿哥脸色一顿:“你终于还是发现不妥了。”
闵敏轻轻揉了揉太阳穴,只觉得病中的脑子太不好使。
“皇阿玛吩咐的,姜薤白也是他钦点的。”
闵敏明白,无非还是因为自己知道的太多了。
“四哥也是这个意思,叫我亲自瞧着。”
闵敏瞪大了眼睛,四阿哥也是这个意思?
十三阿哥诡异一笑,不再想说下去的样子,门外也适时的传来叫门声:“周公公,奴才姜薤白给姑姑请脉。”
周公公?
闵敏不解的视线和十三阿哥的笑眼撞了个正着,一个尘封了许多许多年的名字,跟着一串记忆冒了头。
只是,闵敏是觉得真心累,浑身都累,里外都累,她是真的不想再琢磨那些个绕圈子的破事。
她闭上眼睛,不再说话,任由他们摆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