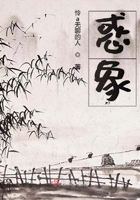我料想说动了她,她便是如何任性的一个人,可是每次一提起元端,她便止不住的柔肠牵动,止不住的心疼肆溢,那样的疼爱,又何需再去分辩呢?
所以,我单刀直入!
我便道:“薜姐姐,你任性了一辈子,只是我为了我的端端,不得不厚了脸皮,要教姐姐你起身来!”
德妃也走进塌前,笑道:“薜姐姐,想是我平时得罪了您啊?这样不待见我?”
薜氏闭了双眼,只是抽动着鼻翼与喉间。
我又推了推她,道:“起来了!姐姐!让杨司空给你瞧瞧,便不为别的,你舍得端端没娘亲心疼吗?你这样糟践自己,未来,若与她天要永隔,你教端端如何?”
薜氏听了我的话,她的身子抽了两抽,落泪道:“端儿何苦要投生这样的帝王家!何苦,何罪?!”
我与德妃皆听得全身一震,德妃不知白天乾清宫里发生的事,她还捺得住,我好奇心、心疼、心酸皆揪在一起……
何苦生在帝王家?
我与德妃岂不是要感叹:何罪身在帝王家了?!
薜氏夺下我手中的绢子,捂住了脸,哭了起来……
我与德妃被她那话一震,心有千千结,思索、痛苦,恰似被雷电一击,失了魂魄,木木的立住了。
“咳!咳!咳!咳……”薜氏咳了起来,我与德妃这才如梦初醒,前去看视她,她每一声咳都仿佛自丹田提起,到胸腔子里一堵,而后再从胸腔中迸出,一堵又一迸,每一迸之间,她皆需要大力呼吸,搜肠刮肚一般,还需要身子死死的一撑……
她的面色煞白,手指紧捂着绢下的嘴,鲜红的血色从绢子中浸出,冉荷大呼:“娘娘!娘娘!”
我大呼:“杨司空!杨司空!”
杨司空飞快的奔我身后,拿出银针,着急道:“微臣得等薜娘娘顺平这口气方敢下针帮她顺气!”
我抚着薜氏的胸,落泪道:“薜姐姐!薜姐姐……”
德妃也泪如泉涌:“娘娘,娘娘……”
良久,良久,薜氏终于咳平了,她闭上眼顺了好一会儿气,张开微弱的眼,对杨司空道:“与本宫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