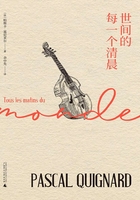泰塔和芬妮撤回来,升起在大山之上。下面的毁灭已经结束,雅里消失在灰烬和熔岩之下。当他们终于穿越苍穹,落下来回到他们的肉体里,因为被看到的和经历的一切震撼着,以至于连话也说不出来、甚至也不能动了。他们的手仍然握在一起,两个人相互注视着。芬妮的眼睛里充满了泪花,她开始默默地哭泣。
“结束了。”泰塔宽慰地告诉她。
“厄俄斯死了?”芬妮恳求道,“告诉我那不是一个幻觉。泰塔,请告诉我在神游中我见到的都是真的。”
“那是真的。对她来说,那是她死亡的唯一可能的方式,她毁灭在自己兴起的火山烈焰之中。”芬妮钻进泰塔的怀里,他用双臂搂着她。现在危险已经过去了,她的力气也消失殆尽了。她又是一个胆小的孩子了。他们坐在那里度过了一天的时光,长久地凝视着绿色的尼罗河。接着,当太阳落到了仍然高耸着漫天黑烟和尘雾的西方的雅里时,泰塔站了起来,背着她下山,走在回村庄的小路上。
人们都冲出来迎接他们,孩子们兴奋得尖叫,妇女们高兴得大叫。麦伦飞快地跑在人群的最前面,第一个来迎接他们。泰塔放下了芬妮,张开了双臂欢迎他。
“巫师!我们为你们的生命担心,”当他还在五十步远的地方,麦伦就大声喊道。“我应该对你们更有信心,我应该知道你们的魔法会获胜。尼罗河又流水了!”他用热情的拥抱一下子抓住泰塔。“你们给它恢复了生命,你们让我们的祖国重生。”他伸出另一只胳膊,将芬妮拉到他面前。“我们谁也不知道你们两位是如何创造的奇迹,可是埃及的子孙万代会为此感激你们的。”接下来他们被兴高采烈的人群围住,然后被簇拥着到达小山顶。歌唱声和笑声、跳舞和庆贺持续了一整夜。
在尼罗河的水位再一次回落,河水又被容纳在两岸的河堤之中时,已经是好几周之后了。即便如此,它仍然充满了银白色的浪花,滔滔的洪水顺着河底继续冲磨着巨大厚重的红色岩石片。听起来好像是一位巨人暴怒时咬牙切齿发出的声音。泰塔命令将山上的船只运下来,在岸边重新组装。
“如果你不让我们把它们带到山顶上,那浪涛的猛烈撞击就会将它们变成劈柴,”麦伦不得不承认,“可是那时我还和你争辩,我请求你的宽恕和谅解,巫师。”
“不必多虑。”泰塔微笑着回答。“不过事实上,多年以来我已经习惯于你像一匹未驯服的烈马一样,拒绝我提供给你的任何理智的判断。”
在河岸边的船只一重新组装完毕,他们就离开了卡卢卢这个古老的村子,在靠近船只的那个风景宜人、绿树成荫的地点建立了新营地。他们在这里等待着尼罗河河水能降至安全航行的水位。营地里仍然充满着喜庆的气氛。得知不会再被雅里军队进一步追击以及不必再担心厄俄斯的恶毒魔法,对每一个人来说,那都是欢乐的永恒来源。他们会很快开始他们最后的一段长途旅行,这是回到他们深深热爱和强烈思念的祖国的最后一段行程。一头巨大的雌河马,生活在纳卢巴勒湖的兽群之一,过分冒险地接近了尼罗河新开的河口,陷进了激流之中。即使它具有极大的力量,也不足以把自己从急流之中救出来。当它被抛到岩石上时,身体被划破和撕裂了。河马受到了致命的伤害,它拖着受伤的身体来到了正位于营地下面的岸上。五十名武装的士兵带着长矛、标枪和斧子向它冲过去,这头将死的野兽无法逃跑了。他们一杀死它,就开始分解它的尸体。
那天晚上,士兵们把成片的河马肉用它那柔软光滑的、雪白的腹部脂肪包裹好,放在五十处单独的炭火上烧烤,人们再一次尽情地享乐和跳舞,欢度了一个通宵。虽然他们全都拼命地吃,仍然有大量剩余的河马肉用于腌制和熏制——那够他们吃上几周的了。除此之外,尼罗河里盛产鲶鱼,它们被汹涌的河水击昏并且偏离了河道,所以从岸上很容易用鱼叉捕获,叉到的鱼有的比一个成人还重。他们还有几吨从雅里粮仓运来的高粱,泰塔同意其中一些可以用来发酵酿造啤酒。此时尼罗河河水已降至可以行船的水位了,他们都很强壮了,得到了充分的休息并渴望重新开始航行。甚至刚刚从伤势中恢复的希尔特也能在他的划船椅上就位。
尼罗河在他们去雅里国的旅途上就已经开始悄悄地出现细流变化了。每一处拐弯,每一处浅滩,每一处暗礁的出现都出人意料,因此泰塔不肯冒夜行之险。每一天晚上,他们都停泊在岸上,在岸上的荆棘丛中修建一个安全的围栏。在一整天被限制在狭窄的甲板上后,他们把马匹松开,放它们去吃青草,直到夜幕降临。麦伦带领一支狩猎队猎获他们所能找到的野生鸟兽。当天一黑,一行人马就被带入安全的围栏:围绕着荆棘丛的围墙,狮子在吼,豹子在穿梭不停地游动,它们是被马匹和新鲜的猎物肉吸引来的。
有那么多的人和马匹需要住处,围场内十分拥挤。然而,因为对他们的尊重和爱,泰塔和芬妮总是有一个虽小却不受干扰的专有场地。当他们独处在自己的安全领地时,谈话通常转向他们的祖国。虽然在她的前世,芬妮一度戴有上下王国的双重王冠,可现在她对埃及所有的了解都是从泰塔那里获得的。她渴望了解这个国家的每一个细节:它的民族、它的宗教、它的艺术和习俗。特别是,她渴望对她很久以前所生的孩子们和他们的后裔的描述,后者现在正统治着这个国家。
“告诉我法老尼弗尔·塞提的事。”
“你已经知道你现在要知道的一切了。”他申辩道。
“再给我讲一遍,”她坚持道。“我渴望面对面见到他的那一天。你认为他会知道我曾经是他的奶奶吗?”
“如果他知道的话,我会感到惊讶。你还不到他年龄的一半,那么年轻漂亮,他可能会爱上你。”他逗她道。
“那永远不行,”她严肃地说道。“首先,那是乱伦,但是更重要的是,我属于你。”
“芬妮?你真的属于我?”
她吃惊地睁大了眼睛。“作为一位巫师和渊博的学者,你有时真的很傻,泰塔。我当然属于你。在前世我向你保证过了。你亲自告诉我是那样的。”
“关于乱伦你知道些什么?”他变换了话题。“那是谁告诉你的?”
“茵芭丽,”她回答道。“你没有告诉我的事情,她告诉我了。”“乱伦是有血缘关系的人们相互间****。”她平静地回答。
在她天真的嘴里听到那样的脏字,他屏住了呼吸。“****?”他小心翼翼地问道。“那是什么意思?”
“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泰塔,”她说道,带着一种长期受罪的神情。“你和我一直在****。”
他再次屏住呼吸,但是这一次控制住了。“我们是怎么做的?”
“你很清楚。我们牵手,相互亲吻。那就是人们如何****的。”泰塔呼出了一声轻松的叹息,她意识到,在这声叹息中他在隐瞒着什么。“啊,那不对吗?”
“我想是,或者说至少有一部分不对。”
现在他完全引起了她的怀疑,在晚上余下的时间里,她超常地安静。他知道她不会被轻易地搪塞过去的。
第二天的晚上,他们在去雅里的旅途中曾路过的一个瀑布上面露营。那时尼罗河几乎已经干涸了,可是现在水位已升至高高的浪花柱所标记的位置。当岸上的小分队在砍伐荆棘丛来修建一个围场和搭帐篷时,泰塔和芬妮上了马,沿着堤岸追踪着一个猎物的踪迹。河岸上深深地印有水牛和大象的足迹,到处都是它们一堆堆的粪便。他们带着已备好的弓,谨慎地前行,期待着在小径的每一个拐弯处撞上一群这种或那种野兽。可是,虽然他们听到了大象的吼叫声和在附近的森林里折断树枝的声音,但是当他们到达瀑布上面的时候,却连个影子也没有见到。他们把马拴好,让它们吃青草,自己则向前步行。
泰塔想起了这段河流,那时候它仅仅是狭窄的岩石峡谷深处的涓涓细流。现在,它已流动在高高的两岸之间,跳跃在岩石与黑色暗礁之间,白浪滚滚地翻卷着泡沫。前方看不见的瀑布轰鸣作响,溅起的水花落到了他们仰起的脸上。
当他们终于出现在大瀑布上方的岬角上时,尼罗河已经从二百步宽压缩到只有二十步宽。激流冲过灿烂的彩虹拱门几百肘尺后,落入了翻滚着泡沫的大峡谷。
“这是我们回到埃及之前的最后一道大瀑布了,”他说道。“是我们归途上最后一道障碍。”他沉浸在壮观的景色之中。
芬妮似乎同样为之陶醉,但事实上她全神贯注地想着其他的事情。她倚靠在他的臂膀上,脸上显示出似笑非笑的样子,神情恍惚,当她终于讲话时,那是一种低沉沙哑的耳语,以至于几乎——而不是完全地,消失在尼罗河河水的轰鸣之中。“昨天我又和茵芭丽谈起人们相互之间如何****的事。”她用那双绿眼睛斜视着他。“她全都告诉我了。当然我见过马和狗交配,可是我从未想过我们会做同样的事。”
泰塔不知所措地搜寻着合适的回答。“我们现在必须回去了,”他说道。“太阳正在落山,在野外有狮子的情况下,我们不应该走夜路。我们以后再来讨论这个问题。”
他们上了马,沿着河堤开始往回走。通常他们的谈话是顺畅而无止无休的,一种想法引领下一个话题。但是这是头一次两个人都没有什么说的了,他们沿着狩猎的小路默默地走着。他每一次偷偷地看她一眼时,她都还是满脸的微笑。
当他们骑马进入围场时,妇女们在忙着生火做饭,男人们三五成群地闲聊着,喝着啤酒,在他们划了一整天的船后,缓解一下酸痛的肌肉。当他们一下马,麦伦就匆匆地来迎接他们。“我正要派出一个搜索队去找你们。”
“我们去探路了,”泰塔告诉他。他们下了马,把马匹交给了马夫。“明天必须把船只拆卸,然后绕着瀑布运过山。下面的小路是陡峭的,因此在我们的前头还有更艰苦的工作。”
“我已经召集了所有的队长和头目就这件事来开会讨论。我们正等着你们回到营地。”
“我会把晚餐给你送过来的。”芬妮告诉泰塔,然后迅速加入到煮饭的妇女之中。
泰塔在参加会议者的前头就座。他已经给这次会议制订了计划,而且给每一个人提出和大伙利害攸关的重要问题的机会。它也是纪律和司法的审判庭,在它的面前,不法之徒将会因他们的罪孽而受到严惩。
在会议开始之前,芬妮给他端来了一碗炖菜和一杯啤酒。当她离开他的时候,她耳语道,“我要一直点着灯等着你。我们有好多重要的事要讨论,你和我。”
泰塔被芬妮的话激起了好奇心,匆忙地进行会议的日程。当他们就如何运输船只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后,他就留下麦伦和蒂纳特去处理一些不太重要的事情。当他路过在火灶旁的妇女们身边时,他们互道晚安,妇女们发出咯咯的笑声,好像有什么令人开心的秘密。麦伦把他们的小屋安置在围场的远端。当泰塔弯腰通过开着的入口时,他发现芬妮确实留着一盏燃着的灯,她已经躺在皮毛毯之下。可她还完全醒着。她坐起来,让皮毯落到她的腰部。她的乳房在灯光下闪现着柔和的光泽。自从她第一次月经后,它们已经变得更加丰满和匀称。****欢快地展现着,****已经呈现出更深的粉色暗影。
“你比我想的回来得早,”她轻声说道。“把你的袍子扔到墙角,我明天要把它洗了。现在到床上来。”他低下头去要吹灭灯火,但是她拦住了他。“不,让它亮着。我喜欢注视你。”他来到她面前,在她旁边的睡垫上躺下来。她仍然坐在那里,向他倾过身来端详着他的脸。
“你要告诉我什么事,”他提醒她。
“你太帅了,”她小声说道,并用她的手指梳理着他前额的头发。“有时当我看着你的脸的时候,我是那么幸福,我想要叫出来。”她顺着他那弯曲的眉毛理下去,然后是他的嘴唇。“你太完美了。”
“那是你的秘密?”
“是一部分,”她说道,她的手指继续向下移动着,他的喉咙,他的胸肌。接着,突然她用拇指和食指夹起他的一个****,捏着它。当他喘着粗气时,她得意地笑了。
“你那里不是太大,阁下。”她托着自己一边的乳房。“但另一方面,我却有足够我们俩用的了。”芬妮继续说道,“今天晚上,当我们坐在炉火边的时候,我注视着莱维给她的婴儿喂奶。他是一个贪婪的小猪。莱维说,当他裹奶的时候,那感觉很好。”芬妮朝泰塔更靠近些,递上她的乳房,用****触到他的唇上。“我们假装你是我的孩子,可以吗?我要知道那种感觉如何。”
接着,该轮到她喘息了。“啊!啊!我从没有想到它会像那样。它使得我肚子里的什么东西在收紧。”她沉默了一会儿,接着嗓子里发出了轻微的笑声。“啊!我们的小矮人醒了。”她抚摸着他。她的手指,随着实践的深入,变得更灵巧和更娴熟。“自从我和茵芭丽谈过之后,今天晚上我就一直在想你。你知道她告诉我什么了吗?”他的嘴还在忙,因此回答得并不清晰。她把他的头从乳房上推开。“你永远都不会相信她告诉我的话。”
“这就是你对我保守的秘密吗?”
“是的,就是。”
“那么,告诉我吧。我兴奋地期待着。”
“那话太下流了,我必须小声和你讲。”她双手罩着他的耳朵,但是她的声音因为咯咯地笑得喘不上气来而中断了。“那不可能,是吗?”她问道,“看看我们的小矮人才多大,它永远不会适合。我确信茵芭丽在戏弄我。”
泰塔长时间地考虑了这个问题,然后认真回答说:“只有一种办法可以确定,那就是把它检验一下。”
她停止了笑声,认真地端详着他的脸。“现在你也在逗我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