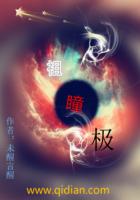二郎屋里的二等丫鬟宝玲来唤她们几个一道去膳房。
二人才晓得不知不觉已到了晌午。
宝衣这一茬就这样揭了过去,她心里仍觉得有些不安,可又不敢轻易解释,怕多说多错。宝槿却好似方才什么都没发生似的,亲亲热热地拉了宝衣一同去用膳。
行到门口,她顿了一顿,感觉到宝栖跟了上来,三人才不远不近地隔着两步路,一同去用了午膳。
纪氏却连午膳也没有用就匆匆地回了府,说是照顾怀孕的儿媳,脱不开身。
可二娘却只送她到了房门口,便关了房门谁也不见。直到过了午时三刻,才叫了人端上饭菜。
是了,再怎么样,她也要为了她的孩子保重自己的身子。阿娘说的,她怎么会不明白,可真要做起来哪有那般轻巧。
她毕竟还怀有身孕啊!叫她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去劝二郎将绿珠收房呢!可她现在身子不便,二郎真的会像阿娘说得那样吗?
食色,性也。
阿爷他。。。二娘实在有些吃不下,心里像揪乱了几团麻似的,强自用了半碗饭便放下了。
二郎回来的时候便已经是晚膳时间。
见到自己的夫君归来,二娘纷乱的心绪稍稍定了定。
二人用罢晚饭,又一同聊了会儿子闲话,二爷嘱咐了她仔细身子,便起身回了自己的院子。
自从二娘有了身孕,二郎便日日来陪二娘用晚膳,可自从中秋那日留宿在了二娘的房里,便再没有与二娘同榻。
有时二娘耍起娇来,他便握了她的手,等她入睡后离去。
二娘从没有睡着过,她不过是为了面子装睡罢了!
她都那样挽留他了,可他说为了孩子着想,她也没有法子。
二郎待她真有那般好吗?她是不是该听了阿娘的话?
她喊了人服侍她洗漱。然后独独留了绿珠下来,绿蓉看了绿珠一眼,便领了两个小丫鬟退了下去。
绿珠也很乖觉,纪氏匆匆地来又匆匆地去,看在有心人眼里都知道是怎么一回事。
她有心,且有智!
二娘有些懒懒地跟她问起她的意愿,她便重重地跪在了二娘面前。
“好教娘子知晓,绿珠是娘子的奴婢,自是愿意伺候娘子和阿郎的。可阿郎是娘子的阿郎,绿珠从不敢有妄想。可是。。。”还有一个碍眼的陆浅云。
听到自己的奴才忠于自己,她岂有不知道的,可她对二郎的心思,真当她看不出来么!她本是不想成全她的,绿珠远没有绿蓉好把握。
阿娘却道,横竖是个奴才,你还怕她翻了天不成!要是个蠢笨的,给了二郎又有什么用!
为了家族,为了她自己,她都要找一个能帮到自己的好帮手!
阿娘劝她许久,她却只抿紧了唇不说话,阿娘气她看不开,拂袖而去。阿娘不明白她的心!可她的心,二郎能明白吗?
她又看了眼面前的绿珠。绿珠,值得信任吗?
“你有什么顾虑只管说罢,我定会为你做主。”她听得绿珠的尾音,以为她要拜托照料家人。绿珠的家人都还在裴家的庄子里。
她又稳稳磕了一个头。“好教娘子知晓,绿珠愿为娘子分忧,娘子教做甚都是愿意的,可待娘子方便了,绿珠还回娘子这里来,只怕娘子不要嫌弃奴。”
二娘闻言,仔细地盯着她的眉眼,想要看看她是否真心实意。
眼前这个跟了自己近十年的丫头,这会儿眼观鼻鼻观心,容长的鹅蛋脸,透出坚定与从容。
“你有这个心,我很欢喜。但我也不能叫阿郎亏待了你,你也放宽心,我自会与你名分。”不过就是让人喊她声姨娘罢了,她一个贱籍出生,莫非还想着官府上册成为良妾么!若是日后她有异心,她的身契在她手里,她还收拾不了一个贱丫头么!
绿珠闻言,便知道大局已定,就算是二郎不要她,二娘也会抬举她的,有了名分,她自然就有办法。
她便露出些小女儿娇态来,二娘见了颇觉得有些刺眼。便道:“可还有什么别的愿求,一并说来罢。”
绿珠听出了她的恼意,现在可不是得罪她的时候。
她忙整肃了表情,“好教娘子知晓,绿珠深知自己的身份,只怕不能服侍地阿郎舒心尽意。莫不如,还是阿郎身边的宝衣更得阿郎的欢喜,娘子还是。。。”
宝衣?
这个名字仿佛是听过的。那个被二郎抬举进了书房的粗婢?!她这些日子真是混过了,怎么竟然混忘了她?
她一时没有了继续这个话题的心思,挥了挥手让绿珠退下。
那个丫头真能影响二郎吗?
翌日一早,二娘破天荒地到了方圆斋。
这是宝衣头一次见到二娘。好一个端庄娴静的美人!她看了一眼就慌忙给她行了礼。二娘却盯着宝衣,也不叫起。
宝衣不懂规矩的望她一眼她看到了,果然有过人的容貌。假以时日,必定更加动人,这样的美人日日在跟前,二郎能不动心吗?
她心底有了主意。便笑着叫她起来,又亲切地问了她的名字。
闻听“阿郎给赐了宝衣”的名儿时,她的笑容有一闪而逝的僵硬。二娘只赞了一声“好名字”,便转头对二郎道:“阿郎可好文才。”
褚明沛已放下手中的紫毫,绕过书案,迎上来执了她的手。有些凉。对于妻子的调侃,他只笑了笑遮掩过去,女人,从来就喜欢多想。
“怎么也不多穿点,可仔细了风凉。”
他总是这样体贴入微。是心中有她,还是本性如此呢?她忽然有些不确定起来。
“不妨事的,今日日头好,阿娘和徐大夫都嘱咐我多走动。走走就不觉得凉了。”她笑着回应他,又携他一同走到书案前,“二郎今儿写了什么字?”
“不过是临摹父亲的《阴符经》手帖。”他不甚在意地回道。
“阿郎深得公爹的真传,自是写的极好。”她虽然识字,可是书法一途也没有多么精进的造诣,只说能写几个字罢了,是以她从不踏入这方圆斋。
可她第一回踏进这个只属于他的小天地,却觉得自己好似不是那般的了解他。
那个宝衣在这里都做些什么呢?
她独享了她的二郎这么许多时候。她深吸了口气,稳住心神。其实二娘真是想多了,木齐活生生地站在那里,她却连他方才给她见礼都没有注意到。更何况陆浅云才来书房多久啊,之前一直都是宝槿在的啊!再有,如不是二郎唤她,她大多时候也是在房门外守着的。
“好教阿郎知晓,儿有些事想说与你商量。”
若是寻常的事,她断不会到他的书房来,他便想携了她回房商量。可二娘却阻止了他。
“也不需去别处,也省的再累人吩咐传达。”她说着便望向了宝衣。“昨日阿娘来府,道是我现下有了身孕,吃食上还得有个仔细人照看着。”
二郎一时没有说话,他有点摸不透她想做什么。
“阿郎这里的人最是谨慎了,儿原本就想着借您屋里的宝栖一用。可宝栖跟着阿郎许久,怕少了她阿郎可不习惯。儿本正游移,不想今日见了宝衣,才知晓阿郎竟藏了这样一个妙人儿。瞧她将这书房打理的,想来也是个谨慎可靠的。儿就想借宝衣一用,阿郎若是舍不得,回头还你便是。”她撒娇卖痴道。
她这般说,宝衣愣了,褚明沛却知道他不能再装傻。
“阿裴要是瞧的上她,只管领了去便是,横竖这后院是你来打理,只管自己做主便是,不用来说与我听。”他不可能为了个丫头与结发妻子分歧。
“既是如此,一会儿就让宝衣到我那儿去吧。”她达到目的,便不再看宝衣,她看了看书案上新摆上的青瓷花瓶,又娇声道,“儿可不敢叫郎吃亏,回头儿便让绿珠来顶了宝衣的差。”
“绿珠虽做事疏漏,可自小跟我大,阿郎可不许亏了她。”这是要给他房里塞人了!
他带着怒意凝视着她,直望得二娘都快绷不住脸上强挂的笑意了,才开口道:
“你做主便罢!”颇有些无奈宠溺的调调。
二娘鼻子就是一酸,差点掉下泪来。却还是坚定地拜谢了他,才施施然又出了书房。
方圆斋一时静的,落针可闻。
木齐乍然见这变故,有些转不过弯来。二娘也闻听二郎对宝衣的不同了吗?
宝衣却对自己突然换了岗位有点接受无能。绿珠要来顶替她?她真的将褚二郎当做冯迪吗?
见她脸色变幻不停,褚明沛幽幽地开口:
“去了之后小心伺候,娘子也不是难相与的。”她已经决定了,他又能如何?更何况他还没弄明白自己的心,让宝衣远离自己的身边,或许也不是一件坏事。
“好教阿郎知晓,宝衣是阿郎与娘子的奴婢,自会尽心服侍娘子,将来更尽心服侍小郎君的。”她真的是恨透了每句话要加上这知晓来知晓去的,一有机会她肯定远远地离开这里,从此海阔天空任她这朵云飘了!鬼才想着伺候完大的伺候小的呢!她又不是奴性坚强的小强!
“恩。”二郎又专心于自己的大字。
却怎么也写不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