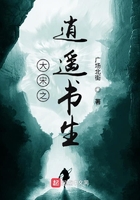卧牛山外百多里远的介阳府城正沐浴在一片喧嚣的市井气象里,府城南大街上有间高悬酒望子的四层酒楼,名曰高朋。这高朋酒楼可不简单,是这介阳府最上档次的酒楼之一。有道是,高朋满座不可无酒,这高朋酒楼正有一种好酒,名叫梨花白。梨花四五月份始开,清晨自梨花上采得露水,以此为引酿出的酒,再在梨树下埋上一年方叫梨花白。这梨花白不似其他的酒那般浑浊,酒水色泽清澈,饮一口爽洌甘甜,当真是不多见的上品。
在这酒楼的四楼临街的座位上,两个青年正对着一壶酒发呆。桌子一头坐着个头扎方巾身着灰白色长衫的年轻人,此人淡淡的眉毛,不算高的鼻梁,嘴也不大,唯一能算福相的就是耳垂饱满,其他再无可观之处,只是眉宇间隐隐有书卷气,看上去像个求学的书生,却又在腰间用麻绳栓了柄牛皮剑鞘的剑。桌子另一头则是个贵公子,青色的锦袍上隐隐有金色的流光闪动。他腰间也挂着柄剑,不过卖相可比那书生强的太多了,他的剑鞘和剑柄都用白玉制成,泛着羊脂般柔和的光泽,还有金丝飞跃其上雕出玄妙的花纹来,只看这穿着打扮就是一派富贵相。往脸上看就更加出挑,此人面如冠玉、目似朗星,两条浓眉直飞入鬓中,一脸的英气勃勃,让人忍不住想多看两眼。这二人怎在一张桌子上喝酒,着实不搭调。
说是喝酒,其实两个人只是看着酒壶发呆,滋味妙不可言的梨花白也没能让二人稍有兴致,两个人既不斟酒对饮,也不向外观望,只是看着一壶梨花白呆呆的对坐。
这正呆呆对坐,且极为不搭调的二人正是从破道观出来的范无咎与谢必安。
“范没救,咱俩都坐了一上午了,那狗东西不会来了吧?她定是怕了,你那一剑当真神妙!小爷我见了都要赞叹一声,那厮定是怕的要死,不敢来了!要我说,就该杀上门去,管他那么许多作甚?!”谢必安没精打采,拿着根筷子在桌子上敲来敲去。
“谢仇敌且放宽心,正午时分定见分晓,现在时辰尚早……”说罢,拿起酒壶自己斟了一杯梨花白,看了半晌,眉头一皱才仰头一饮而尽。刚放下酒杯,范无咎立刻满脸通红,张开嘴大口的咳嗽着,眼泪也伴随着咳嗽声夺眶而出。
“哈哈哈哈!你这小伙子好没深浅,第一次饮酒?”谢必安一边拍着桌子,一边哈哈的大笑着。
“并不是。”范无咎咳嗽了一阵,冲谢必安摆摆手,“这酒……这酒太烈,我不大习惯。”
“嘿嘿,酒不烈喝着可没意思!要喝就得喝这烈酒方才过瘾!”说罢,谢必安也给自己斟了一杯,也是一仰头就一饮而尽。紧跟着,刚才桌子那头的景象在桌子这头又重演了一遍。谢必安满脸通红的大口咳嗽着,眼泪淌的满脸都是。
两人都咳嗽够了,互相望了望,又哈哈的大笑起来。
二人正笑着,一个丫鬟模样的小姑娘噔噔噔的快步跑上楼来,张望了一下,一眼看到了临街靠窗位置上的两人。小丫鬟赶忙跑过来,屈身福了一福。
“二位公子有礼,我家小姐请二位公子雅间一叙!”小丫鬟年纪不大,语气轻快的很,听着感觉很清脆。
范无咎起身冲小丫鬟一拱手,右手向前一伸做了个请的手势,“劳烦姑娘头前带路。”说罢伸手一扯谢必安,两人一同随着小丫鬟往雅间走。
其实早在昨日,范无咎和谢必安就已经到了介阳府城。
本来两人从卧牛山出发一路北行,说说笑笑、打打闹闹,一路上游山玩水四处游历,也自有一番快活。可谁想三日前,两人正在一条荒郊小路上行着,却听得前方有人呼喊,还有打杀之声传来。二人急忙向前赶,一见才知是有盗匪剪径劫掠,正与一队护着自家车马的家丁护院打斗在一起。谢必安虽说不靠谱惯了,却端地是古道热肠,正欲拔剑上前相助却被范无咎按住了。
“不可展露修为,只许见招拆招。”
范无咎千叮咛万嘱咐,要谢必安不可运使法力,谢必安虽然心里老大的不情愿,觉得多此一举,却也相信范无咎的判断,只用剑招去与剪径盗匪对打。谢必安一身修为全赖法力高强,论起招式来真是九窍通了八窍——一窍不通!结果被盗匪打的抱头鼠窜,望山境能丢人至此也着实不易!范无咎只得自己下场迎敌,他的剑法可是十几年来日夜磨炼而来的,做不得半分虚假,一上手就将那伙盗匪一一撂倒,犀利非凡。
打退了盗匪,那队车马的主人家才在家丁护院的保护下,来与二人致谢攀谈。还提出想请二人一同回介阳府城,要重重酬谢二人。谢必安本是想应的,范无咎却又拦住了他,还拉着他赶紧远远的跑开了。
谢必安自然疑惑万分,不明白这范无咎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只得等跑的看不见人影了才问了起来。
“范没救,你这是作甚?放着到手的真金白银不要,跑得这么快干啥?”
“谢必安,你又不缺银钱……亏你还是望山境的高人,你就没看出这车队中有何不妥之处?”
“嘿嘿,银钱自是不缺,可那白给的如何不要?至于不妥之处,不就是有个阴气重的女人罢了,区区养气境的小毛贼,能伤的了你我?你怕她作甚?”
“我倒不是怕她,我只是觉得奇怪……”
“哪里奇怪?我看你最奇怪!”
“那群剪径的盗匪身上有古怪,不似活人……”
听范无咎这么一说,谢必安才觉出不对来。他本来是望山境的高手,神念外放之下有无大敌自然瞒不了他。刚才正是察觉附近并无威胁,这才轻敌冒进,经范无咎一提,他顿时也觉出不对来。
那群盗匪身上活人的气息少,倒是死人的气息多!而且皮肉僵硬,不注意的话还以为练了外家功夫……
“那也不用怕她,不过是个用邪法养了一群邪物的娘们罢了,又能折腾起什么风浪来?”
“话不是这样讲,地底下恐怕这种邪物更多,我觉得没有一千也有八百,她一个养气境,哪来的这么多邪物……”
“范没救,你净瞎操心,任她邪物有多少都当不得你我一剑!”
“我都说过了,我只是觉得奇怪,她如何做到的,又要做什么?”
“多想无益,他们不是住在介阳府城吗?你我二人去了不就知晓了?”
所以二人一直远远的跟着车队,一路停停走走,在昨日与车队一同进入了介阳府城。车队进了城也不停,直接绕奔城南,在府城南大街的一条胡同里停下了车架。那条胡同只有一家,高高的府门上悬挂着朱漆的匾额,上书三个鎏金大字,刺史府。
道路上所救的那家主人居然是介阳刺史!
而这时,两人从刺史府中感应到了一个筑基境修士的气息。
“玉清的人!”谢必安冷冷的说到。
“你确定?”
“她们身上的味道,我到死都忘不了!”谢必安的声音越来越冷,范无咎后悔自己问了这么蠢的一个问题,对于玉清,谢必安怎么会错!
“那养气境的蠢货是奔着她来的。”
“你确定?”这回轮到谢必安问了个蠢问题,他知道范无咎很少犯错。
“确定,两个娘们儿相斗,我本不想管,但是可怜了城中无辜百姓……”范无咎的声音也变得冷了起来。
“玉清的人有筑基境,却放任养气境的宵小在自己眼皮下妄为……她必是觉得很有趣吧!”范无咎的声音冷的像块冰。
“我没懂……”谢必安有点迷糊了,自己才是跟玉清有深仇的那个,为何范无咎一副要杀人的表情。
“路上的那些邪物,有几个是用这府里的家丁炼成的,样貌变了,气味却变不了。明明知道,却偏偏假装不知道,玩什么欲擒故纵!还不知有多少无辜将死在她二人之手!”范无咎想起了当年的王小姐和费管家,不拿别人的性命当性命,恐怕是修行者的通病吧。范无咎突然真气外放,那府中的筑基修士顿时惊了一跳,气息都乱了起来。范无咎运真气于胸,声音化作剑意直奔那筑基修士而去。
“明日正午时分,请高朋酒楼一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