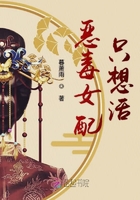高中二年级第一学期的最后一天,开完班会,我和几个同学在教室里围着玩斗地主不想回家。
“打一对勾,要不你就输了。”背后突然来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声音,“关你屁事!”我扭头骂去,眼前却是那个就要被我忘记的外星人聂鸣。
聂鸣看看我,笑笑说:“你不是想和我再打一场么?”
“啊?”
“带上你抽屉里的画,球场见。”
“什么?”
“带上你抽屉里的画!”
他背着黑书包走出了教室。我手忙脚乱地翻开抽屉,拿出一张卷得皱皱巴巴的素描纸,那是我高一美术课的作业。
诚惶诚恐的我一手拿球一手拿那张皱巴巴的画纸来到了球场,远远看去,聂鸣端站在篮球架下等着我。
我往身上擦了擦手心冒的汗,走到他面前:“开始吧。”
这时聂鸣嘴角边露出了诡异的微笑,并向我伸出手来:“你好,冯海!”
他突然转变的态度让我放松了,我没有和他握手,只是击了一下他的手掌:“嘿,你不是要和我单挑吗?”
“行啊,不过作为交换,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什么事?”
“你那幅画带了吗?”
“带了!”
“跟我去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
“拿车,跟我走。”
我取出我的小绵羊摩托车,慢悠悠跟随他26寸老式五羊牌自行车的后面。我们走了大概二十来分钟,来到南城旧区的一个城中村,是南城最久老的居民区,我们叫牌街。我从没真正进来过这,聂鸣却带着我娴熟地在狭隘的街道里间辗转腾挪。也不知道转了几道弯,淌了多少水坑,过了多少摊贩,转到一个3、40年代的三层老楼前,我们把车停好。
那座房子的入口,是个长廊,长廊被一个理发屋改造成了“发廊”和“走廊”的两用空间。里面坐着两个3、40岁模样在染发的妇女。空间窄得在我们穿过的时候,做头发的师傅不得不走到两个女妇女的中间让出路来。
“小心,台阶前有个坑。”聂鸣在走廊黑暗的尽头转身上了楼梯。我只好摸索着,扶着墙跟了上去,来到二楼,聂鸣走向右边的那扇纱窗门,扭头和我说:“稍等。”
穿过纱窗,只见聂鸣放下包。只隐约见一个妇女同聂鸣说:“回来了啊?”。“你们先吃,不管我。”聂鸣推开纱窗门,走了出来,往三楼走。上楼前,还听见屋内传来一个男人咳嗽的声音。或许这就是聂鸣的家。
我们来到三楼。聂鸣用钥匙打开他家顶上的这户的门,打开屋里的日光灯,我立刻看傻了眼。
有一个1.5左右的大卫石膏像竖立在我对面的墙前,除了小一号,就像我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看到的一样。不对,那不是一个真的雕塑,那是画的!我跑走进屋子,走到大卫画前,画得太像了,细腻的笔触迷惑了我的双眼。
“来里面。”聂鸣走进里面一间的房子说。,
我跟着走进去,这里是一个更精彩的空间。不到15平米的小房间,里面挂满了各式各样的画,有风景,有人物,有静物。窗前墙放着一张大画桌,上面摆着成堆的画具,还有我叫不出名字的各种石膏像。
墙边有一张布沙发,沙发前有一个木茶几,茶几两端是两张沙发凳。
“坐吧,这是我的画室。”聂鸣坐在对面的沙发凳上。
我往跟前的沙发凳坐下,抬头看四周:“都是你画的?”
“恩,我今天叫你来,想和你交换你那张画。”
我迟疑了一下,拿过我的包,抽出那张皱巴巴的白纸,一个我为了美术课随手涂的美术作业,曾经被美术老师在班上展示过。我拿出来打开,说:“是这个吗?”
聂鸣眼睛突然一亮:“就是它……”他欣喜地看着我,平日里冷漠的眼神现在变得格外友善,“你是怎么画出来的?”
“哦,中考完我去了一趟欧洲玩,欧洲的教堂里都是这种壁画,我拍下来,抄相片的……”
“以前你学过画画么?”
“以前在少年宫学过一年。”
“为什么不继续学?”
“我不知道,反正我什么都喜欢一点,后来又去学了吹长笛,上初中以后跑去学打篮球了,我爸说我两天打渔三天晒网……”
“那……你现在还喜欢画吗?”
“还行吧,呵呵……”
“你想跟我学吗?”
“啊?这个……”我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这么问我,这让我有些不知所措。
“放心,我不收你学费。”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还没想过。”
“那你以后想干什么?”
“我……”我一时语塞了,我想起我对我爸说我想去当摄影师,结果被教训了,一定是自己的想法太儿戏,所以在聂鸣这种好学生面前就更不敢吱声了。
“你以后想干什么?”他又问。
我摇摇头:“不知道……考大学吧……”
“考什么大学?”
“不知道……你呢?”
“我想考美术学院,成为艺术家是我的梦想。”聂鸣笑起来其实不那么冷漠,就像我常见到的朋友一样。
“梦想……”
聂鸣看向窗外,脸上漾出幸福:“梦想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它可以带你远离这个现实的世界,即便生活再苦恼,你也可以在追求梦想中找到你自己……”
他说得很生动,我听得很动心,因为以前我只听到我爸说“看看别人多努力,你怎么不学学别人?”,但从来没有人和我说“在追求梦想中找到你自己”。
聂鸣又说:“梦想可以让你忘记一切烦恼,让生命不再无趣,找到活下去的动力。”
听到这,我又有点感伤,我不知道他哪里来的想法,却好像也说到了我的心坎里,虽然还不至于活不下去,我时常觉得我生活无趣,是不是就是因为我是个没有梦想的人:
“可怎么样才能有梦想?”
聂鸣看着我,停顿了半响说:“你想和我一起去画画吗?我们可以一起去追梦,你很有绘画的天赋,你以后可以成为艺术家。”
“我可以吗?”
“当然了。”
“怎样才是艺术家?”
“你过来……”聂鸣走到窗台前的书架上抽出几本画册,“你看,这是马蒂斯,这是塞尚,这是马奈,这些就是艺术家,他们的画你喜欢吗?”
我压根就没看明白,但我已经被聂鸣所说的梦想打动,点头如捣蒜。
我问:“我要怎么做才能和他们一样?”
“画画啊,一直画下去,就可以和他们一样!”
“怎么样?”
“影响人类,影响人类文明,改变历史,成为流芳百世,记入史册的人。”聂鸣如同一代伟人,要说服他的朋友去为革命理想,抛头颅洒热血一样,诚恳地对我说。
我听着听着就兴奋了:“我怎么感觉自己身上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
“是不是感觉自己特别有力量?”
“对!”我点着头说。
“这就是有梦想的感觉!”
我很高兴:“你……为什么把我带过来,跟我说这些?”
“因为这是我的秘密,他们不理解……”
我懂得不被理解的苦恼,心中狂喜:“你觉得我能理解你?”
“我在这个画室6年了,看过各种人画过的画,那天美术课我看到你这张画,我就觉得你是那个能看懂我的人,你有那个天赋。”
我高兴极了,好像找到了丢散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伙伴,特别当我知道这个伙伴是聂鸣时,我更是心花怒放,这可是神奇的外星人,那个衬衣从没超过5条印子的外星人。
我站起身来,踱步看着墙上的画说:“你有这个画室6年了?”
“画室在我手里时间不长。原来是个师范学院的老师开来教艺考生的,租的就是楼下发廊王老板的房子。后来他们不知道什么原因闹翻了,王老板不租给他了,我就续租了下来。”
“你租下来做什么?”
“画画啊,我从小看很多学生来来往往到这里学画画,我喜欢,经常跟着他们画,那个师范的老师见我是街坊,又那么好学,就不收我学费。我小学的时候就想,以后要和那些哥哥姐姐一样以后去考美院。后来他们搬走了,我舍不得,我就租了下来。那些复读的老生不想找再交钱跟班,但又想找一个地方聚在一起练习,我只收他们一人100块钱一个月的场地费让他们来这画。因为我比他们画得好,有时候我还能指点一下他们,我还教美术中专生和附近幼儿园的小朋友画画。”
我简直听傻了,不敢想象一个和我一般大的愣头青已经开始当老师了:“太牛逼了!”
“所以我不会忽悠你,你要相信我的眼光。”
“抽烟吗?”我很高兴,拿出烟来递给他一只。聂鸣接过了我给的烟,我给他点上,他说:“走,去阳台聊。”
画室外有一个很大的晒台,我们走了出去,走到围栏边,不远处淌过一条穿过旧城的人工河,对面密密麻麻红砖房房顶上顶着日落的最后一道光亮。我们在晒台聊了很久,聂鸣和我讲了很多关于艺术的事,聊到落日的最后一道光亮被黑夜淹没,天边的明月挂上墨蓝色的天空,照亮整个大地。
聊着聊着,我恍惚听见我的BB机在屋里响,我跑到屋里从沙发上的包里找出BB机。看到好几条消息,都是我妈问我在哪,让我回家的消息。我看看时间,已经晚上8点多了。我背上包,到晒台的门前,和靠着围栏抽烟的聂鸣喊:“时间不早了,我要走了!”
“好,我送你下去。”
“不用,我自己走。我们什么时候开始?”我心中已经确认我找到那个我心中缺少的,聂鸣所说的梦想了。
“我明天上课,你可以过来。”黑暗中,我看到晒台上聂鸣手中燃烧的烟头在灼烁。
“好!明天见!”
那天,神秘的外星人聂鸣带着他的结伴计划从天而降,顺带给我捎来来了梦想的伴手礼,我也因此看到他不为人知的一面,我以为这就是外星人的秘密,走到后来我才发现,外星人的秘密远远不止这些。就像今天,我们一道来美国,他以为我是为读书而来,可他不知道,我来美国的目的远远不止这些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