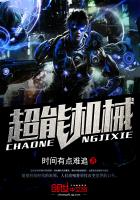在家已经等了两月有余,期间谢凭曾数次叫我出门,而刘子兴也几次相约,但我除了去了宜初家,其他地方,都是恹恹的,提不起精神去。
两个月来,每天都是那么难熬,索性闲来在家看书习字,或者随着阿芙进进厨房做羹汤,陪她刺绣说话,所幸恍惚间,光阴有时也悄悄的走过,方能过得快些。
如今已是十月,气候渐渐凉了,人也变得懒懒的,早晨不思起,中午不思睡,夜来不思书,唯有那一个人,日日思念。说来今年的冬天来的那么的慢,虽已转凉,却不是那么冷,我多么希望,飘雪的日子能快点来到,而怎么等,也没有等来家中的人们穿起棉衣,大氅。
我懒懒地在房间里看着书,看着王嘉所写的《拾遗记》,本是看过几次的书,因我闲来无事,又被翻出来看。
“哐哐哐”
门外传来叩门的声音,我心想这是谁,便问道:“是谁?”
只听见那声音是爷爷身边的忠伯,在外恭候道:“小姐,太老爷,二老爷,请您去一趟太老爷的书房。”原来是祖父与父亲有事找我,我也未仔细拾掇,便跟忠伯去了。
爷爷的书房甚大,我进去的时候,爷爷和父亲正坐在椅子上叙话,似有重要的事情。
我向爷爷问了安,他让我坐下,带着慈祥的笑,似一颗外干内润的蜜柑,受了风雨的洗礼,更见内涵,他对我说:“莞笙长这么大了。”
我向爷爷撒娇道:“在爷爷心中,莞笙难道不该永远是个长不大得小姑娘吗?”说完便往他身上蹭。
爷爷大笑道:“就算爷爷真这么想,别人可不这么认为咯!小姑娘家,留不住咯。”
我倏地从爷爷身旁站起,听得这话,一下不能明白,转头皱眉看父亲,父亲向我点点头,似有话,又不说。
“爷爷这话是什么意思,您是不要我了?”我纳闷道。
爷爷捋了捋小须,展颜笑着,一如小时候对我的惯纵。
“瞧你这小性,女儿大了,终究是要嫁人的,爷爷和你爹已经为你挑好了人家,你嫁过去后,可不能再像家里这样了。”
轰!如一场暴雨向我袭来般,萧正清走后不到三月家里竟给我订了亲。
而爷爷和父亲仍是不知我的想法,自顾自的说着。
我急着眼睛泛红,只觉得眼泪正在喉咙里,一不小心,恐怕就要泛上来。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竟也没告诉我,谢凭刚刚订了亲,怎么就轮到我了呢?”感觉自己语有泪声,艰难得说着话。
爷爷似乎以为我是撒娇,摸摸我的头道:“本来也不想这么快就把我们莞笙嫁出去,谁想已经有人上门纳彩了,为着是一门好亲事,也就答应了,爷爷可不想以后莞笙怨爷爷把你留成老姑娘了。”
真想告诉爷爷,我应该也留不成老姑娘。
父亲也说道:“正是,本是不着急,然而为父看此人人品确是不错,你们也曾有一面之缘,便听你爷爷的,替你做主了。”
一面之缘?我心中欣喜,莫不是萧正清真的提前派人来了,问道:“爷爷替我定的,到底是谁家的亲事?”
刚一问完,便被爷爷笑称,女儿心急,一点也不害臊。
“正是京中大司马家,兰陵萧家。”兰陵萧家!这四个字,虽然爷爷吐的轻描淡写,对我而言却有万般重。
大司马家的公子,与我有过一面之缘的,除了萧正清,还能是谁。
爷爷继续侃侃而谈,似有流水收不住,掩不住眼角的笑意:“萧家已经着人来问名,爷爷小时候着人给你看过,你八字清白,你俩属相般配,这门亲事,定是要成的,今日也便先告诉你。”
他离去时说四月便来提亲,没想到,三个月未到,他便早早的叫人来提了亲事。我也不想,大司马竟这样由着他自己将这门亲事定了下来。
“咣当”!门口一声响,吓了我们祖孙三人一跳,出门一看,原来是谢凭在门外,听到了我们的谈话,他凝视着我们三人,旁边的阿芙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茫然问道:“相公?”。
正如谢凭的反应,兰陵萧氏的提亲,在我家掀起了轩然大波。
爷爷,大伯,几位哥哥,很是高兴,虽都是四大家族,但大司马权倾朝野,与萧家结亲,自然是为先祖添光。
父亲母亲却有一丝担忧,当日大司马萧禹与丞相萧子升同为辅政大臣,为皇上的左膀右臂,而皇上毫不留情将萧子升杀害,大司马一族亦是岌岌可危,父母总是希望儿女平安,而不求过分显达,所以欢喜中添了一丝忧愁。
而唯一有不同的,是谢凭,他与我说,他自是知道我与刘子兴不会有什么结果,但这变故突如其来,不知该如何与子兴交代。
我与他说,刘子兴是旷世之才,治国安邦,文才武略,皆是个中好手,他不会为了这件事而愁楚,而我,也期望他早日实现心中的理想。
又过了一月有余,萧家便派媒人来纳吉,虽只是过聘,但萧家阵仗豪华,谢家前后两条街皆知晋国公府上的小姐要嫁到京城大司马家,人人羡艳。
据说,媒人来到了我家,送来了聘书,两家交换了庚帖,她说萧家请来了钦天监的监正为我们合婚,监正说我二人的八字是天作之合,大司马甚是高兴,并为我们择了成亲的日子,由于萧家大公子还未成亲,所以将我们成亲的日子定在了乙巳年八月初三,也就是后年。
我问哥哥,为什么萧家的大公子还会成亲,哥哥说,媒人说原来萧家的两位公子皆是正妻宇文夫人所生嫡子,是对孪生兄弟,两人前后只差一个时辰,大公子萧正源,也刚刚才到娶妻的年龄。
我又问大公子是否定亲,原来萧正源早我与萧正清一步定亲,未来的大儿媳与萧正源青梅竹马,是琅琊王氏王少府的女儿王樱。
琅琊王氏?萧家的长媳确实只有王家的女儿才当得起。
是夜,刘子兴来见谢凭,偷偷地溜进了我的后院,有话要与我说。
我自然是知道他想对我说什么,心中却还是忐忑。
刘子兴神色苍凉,开口道:“几日不见,莞妹妹大喜了,这样的喜事,还没来得及恭喜你呢。”
虽觉得无法直视他,但提到这婚事,我难免还是会有小女儿的欣喜,不知这份小小的喜悦在他看来,是否那么刺眼,不觉说道:“多谢子兴哥哥,时间仓促,还未来得及与大家说,不想你先知道了。”
“今日晋公街锣鼓喧天,恨不得整个阳夏都能听见,我自然也会知道。”他的话中有一丝酸意,我不是听不出。
只能安慰他:“您能这么关心我,我很高兴,若是没什么事,我先回房了,公子也早些回去,免得叫谢凭担心。”
我正要转身,他拉住了我的衣袖,声音略带一丝沙哑与不甘,向我问道:“你是不是嫌弃我出身不及萧正清?”
我惊愕地看着他,这般伤尊严的话,往日的刘子兴是断然不会说出口,而他今天却这样问我,我截然对他说:“彭城刘氏是大家族,怎会出身不及别人,子兴哥哥这么说,肯定是急糊涂了。你自己不觉得,我却要为刘氏抱不平了。”
他仍不依不饶,又向我问道:“那我的心意,你怎么会不知道?为何你见了他几面就与他定下终身,他送你墨宝,我也送你墨宝,我终究想不通,我究竟比他不如在哪儿。”
“你从来没有说过,我该知道什么,我怎么会知道?”我如是问他。
他慢慢的松开了我的袖子,喃喃自语:“我以为你该知道。”
“可你确实没说过。”我慢慢低下头,紧张地把玩着指甲。
“晚了。”他摇摇头,“现在已经不是说不说,谢家肯不肯,而是你确实对萧正清心生爱慕。”
想起刘子兴往日的心怀,我只能鼓励他,使他重拾信心,他是天地的灵气精华,即使没有了我,我鼓励他道:“对于你来说,没有晚不晚。”
他疑惑地看着我。
“天地之间,凡尘俗世,有的人是来感受,有的人是来指化,子兴哥哥是天地的精华,红尘万物了然于胸,你的脱俗正是你比凡尘中的俗人多了一份清醒与透彻,你看着尘世间的人忙忙碌碌,我们是来感受的人们,而你,生来便是观看这个世界,看花开花落,看萧条繁华,你不会难过,因为你的心那么大,不会被这点红尘俗世所伤,等着你的事情还有很多,金麟岂是池中物。”
“你……”他说不出话来。
我摸了摸自己的脸,有些发烫,对他道:“我不知怎么的,语无伦次了,子兴哥哥莫见怪。”
他突然大笑:“爱上妹妹,是我此生做得最错的一件事,妹妹与我而言,是世间难得的知己,我却把他归为了这般俗气的情感,今日你所言,我定铭记于心。”
见他已释怀,我也松了口气。
他凝视着我道:“我只允许自己难过一天,明天起,便又是你所熟悉的刘子兴。”
“我相信你。”我相信你,这是我当晚对他说的最后一句话,而日后,他也当得起我当晚所说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