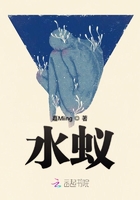杜悦最关心钱茈情的就是她要怎么用姥姥那点儿退休金念完四年大学?钱茈情拍了拍她的肩膀说:“不用担心,我之前就了解过C大,每年都有助学贷款和国家奖学金。况且大学里的课时也没那么紧张,我也可以打些零工。只要我够努力,四年应该没什么大问题。”
看着钱茈情的坚强,杜悦反而心生惆怅。自己虽然家境一般,却也不会因为念书而负债累累。她无法想像面前这个看上去温温柔柔的姑娘肩上的担子有多重,该是一个多么骄傲的人才会不屈服于这个物质的社会。
分别前杜悦把自己新买的手机号留给了钱茈情,叮嘱她安顿好以后一定要用寝室的电话打给自己。常联系,是钱茈情听过最温暖的告别。
车站对于离别是再凄凉不过的地方,就像是立在城市中的奈何桥,这一头连着所有熟悉的前尘往事,那一头却如迷雾一般充满未知。
钱茈情在站台前把姥姥脸上的泪痕擦了又擦,她轻声细语的道别就怕稍一用力震落眼里的悲伤:“姥姥,谢谢你。千万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怀里的姥姥抽泣的像个孩子,一声鸣笛阔别那个大大的拥抱,钱茈情坐上了火车。几千里的距离,三十几个小时的路程,将她带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南方城市。
这里到处弥散着不绝于耳的方言,理解起来的难度一点儿不亚于一门外语。出来乍到的钱茈情,还来不及适应这里的一切就投入到紧张而又辛苦的军训中。
这座特别的盆地城市,即使到了秋季也有一股熬人的闷热。仿佛是在头顶上扣了一锅盖,在这个密不透风的蒸笼里,每天早上刚从宿舍楼下去,后背的汗就会洇湿军训时穿的衬衫。就连楼下的宿管阿姨都忍不住感慨:“闷了这些天不见太阳,唯独这群孩子军训的时候天天顶个大太阳,也真是够受的了。”
军训的队伍里已经有同学陆续晕倒,钱茈情咬紧牙关以为自己可以坚持到最后,不成想自己脚下一软,脑袋里闪过一道白光,跟着也就不省人事。
学校的医务室被整个大一新生承包了,来这里输液的全都是穿着军训服装的同学。钱茈情闻见越来越近的消毒水味儿,针头还不等扎到她身上,她撑着身体站了起来。
“我不用输液,我回宿舍休息一会儿就好了。”
舍友在一旁焦急的说:“你脸都白了,还是输完液再回去吧。”
“真的不用。”
钱茈情拿起一旁放着的帽子,歪歪扭扭的往外走。舍友紧跟着跑了出来,无奈只好把她扶回宿舍。别人看她柔柔弱弱的外表都以为她是害怕打针,只有她自己清楚,她不能再额外负担这突如其来的开销。
整个下午她接到过姥姥的电话,不想姥姥担心,她佯装出忙忙碌碌的声音,匆忙挂断。接到过杜悦的电话,但是还来不及倾诉辛苦,就听见电话那边匆忙的集合声。
她一个人躺在宿舍床上对着发白的墙壁,前所未有的孤单混在空气中紧紧的包裹着她。她就像一只掉队的羊,迷失在苍茫的草原上。如果不是一阵急促的电话铃,或许她又会晕厥过去。
“喂,你找哪位?”
钱茈情从嗓子眼里挤出一句话,却听见那边深深的叹了一口气。其实不必介绍,她心中早已有答案:“钟漠?”
“是我。你是不是不舒服,怎么说话听上去有气无力?”
钱茈情曾经以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打倒自己,没想到就在此刻,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倒成了无坚不摧的利器。她擦了擦眼里落下的泪水,过了一会儿才说:“没事,可能是因为这里太热了。”
“那就好。我……本来不应该打扰你的。可是,我最近看了看天气预报说成都气温很高,又听杜悦说你们在军训。所以……哎,就这样吧。我没什么特别的事。”
“谢谢……再见。”
如果电话那端的钟漠仔细听,一定听得见钱茈情声音里的颤抖。她匆忙的挂断电话,是害怕自己的哭声吓到钟漠,更怕自己从此会想念这种无微不至的关怀。
在钱茈情看来,所有的关系都应该是对等的才会长久。可她和钟漠就好像此刻她在成都,而他在北京,中间隔着千山万水注定无法相守。她更不知道一个一无所有的自己可以拿什么回应钟漠对自己的好。
钟漠站在电话亭里,长久的听着那端传来的嘟嘟声,心跟着一沉。她不会知道军训的时候自己上交了手机,趁着休息的时间跑遍了整个校园才在角落里找到这么一个不起眼的电话亭。她一定不知道自己有多么不想打这通电话,只是自从知道这个号码开始脑子里就再也装不进去其他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