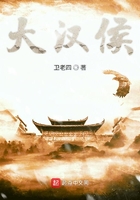“不说两句吗?”立着的的菜刀回到这人手上,他的目光很冷。
北斗还是沉默。
“北斗!”一把匕首从地上滑了过去,是断咬金的手里的那一把。
男人瞥了一眼断咬金,菜刀微微倾斜,往上一举。
断咬金面露一丝疯狂之色,他抓了一块瓷碗的碎片,捏得很紧,他没看到滴得很快的血,他的眼里只有这一个人,他盯着的是这个人脖颈的动脉。
一把半锈的菜刀能劈开木椅,这时落在断咬金身上,是断没有侥幸的道理。
这是一个必死的抉择,是菜刀先对准的他,然后他抓住瓷片。就算这个卫兵动手慢了,可一片瓷片,又能伤得了他几分呢?
断咬金当然没想这么多,他只是凭本能在行事。
这世间有一种人,行事全凭一个狠字,因为够狠,比他强大的敌人也不敢轻易招惹他,弱肉强食的世界里,这是弱者护身保命的利器。
这一把利器,却不是每一个弱者都能拾得起的,它需要一样东西,那就是胆。
断咬金已经想好了两面见血,或许自己会死,但是你,也休想好过!
他扑向前的刹那,一只手臂从后面环抱住他的脖颈,一口呵气从耳边响起,带着些余温,这是另一名卫兵。
冷,非常冷,断咬金的心凉了一截,因为意外,因为自己就要死了。
断咬金身后的卫兵,另一只手捂着腰间,但仍无法压住不断流出来的鲜血,但他没也不去管,他盯着身前的断咬金,脸上的一抹阴笑,像是在问:后悔吗?同时,这名卫兵在等,等前方半空中的一把菜刀落下来。
菜刀没有落下,因为那把匕首来得很快,笔直冲来。
或许这一刀不是来不及落下,只是这个卫兵很自信,自信可以先杀了前面这个少年,拿了匕首,再一点一点折磨旁边的小兔崽子。
卫兵突然觉得很冷,因为他看到了匕首上面反射出来的一缕寒光,这把匕首是崭新的,比自己手中半锈的菜刀锋利的多,所以以伤换伤,不见得明智。
少年到了身前一米,这名卫兵没有动,他在等。
少年到了身前半米,卫兵还没有动,直到少年贴得更近了,他才动,他的手臂仍是弯折的,没有挥刀,他退了一步。
少年的手肘贴着腰,也没有出手。
卫兵又退了一步,他不想受伤,哪怕是用自己的伤换少年的命。他在等少年出手,避开的那一刹那,就是他反手一刀的时候。
卫兵还是没有看到少年出刀,他再想退,发现到了墙边。他也是果断的人,不能退,那就攻,一刀劈去,正是少年颈部。
卫兵睁大了眼瞳,很惊恐,这一刀空了!
少年在片刻之间,骤然加速,他的脸都贴到卫兵的胸口,而卫兵的菜刀却落在了身前半米,北斗加速前站的那个地方。
卫兵满脸的不可置信,表情渐渐僵硬,他想不明白,为什么这个少年能这么快?
出刀可以快,奔跑可以快,但是加速,哪能这么快?刀落不过刹那,这个少年凭什么,靠腿部发力,就躲了过去,这样的身体素质,他只在百夫长身上见过。
酒馆安静下来了,只剩下重重的喘息,和泣咽声。场中无声不代表众人得了一丝喘息的间隙,更不是说这一劫已过,而是心头的重石压得每一个人不敢轻易开口。
徐风、徐水的父亲开口道:“能制服他们就好了,杀了一个,这下怎么办呢?”他看着汉北斗,问道。
徐风、徐水的母亲小声道:“是啊,这是城里卫兵,死一个都是很大的事,要查到底的,这不是把所有人都连累了吗?”
“唉!”徐风、徐水的父亲这一叹,带着浓浓怨气。
汉北斗看着地面,有些茫然,无助,唇枪舌斗不是他擅长的,但他就是觉得自己没有做错,所以和徐风、徐水父母的眼光对上的的刹那,没有闪躲,因为问心无愧。
“不是为了救你,我们犯的着和四个卫兵拼命?老子的脑袋差一点就被砍掉了,你知不道?你要不是我兄弟的爹妈,我现在就宰了你俩!”断咬金恨道。
徐风、徐水低着头,自幼跌爬滚打,吃过不计胜数的伤,这时候因为断咬金的一句,眼中噙满了泪。
场中又是一阵沉默。
还是断咬金先开的口,他问:“怎么办?”这话是对着陈庭说的。
徐风、徐水也抬起头,当着兄弟的面,擦拭眼角,目光落在陈庭身上。
徐风、徐水的父母也觉得诧异,四个孩子都直直的看着这个叫陈庭的孩子,目光深信不疑,像是不论陈庭说什么,四个孩子都会照做。
陈庭背负双手,来回走了一圈,又扫过每一个人的眼睛,道:“如今之计,只有当机立断了!”
陈庭谋断在胸的样子,让徐风父母都听得全神贯注。
陈庭看着徐风父母,道:“今晚的事一定要有人站出来扛,不然的话,我们都要死!因为,只要找得到借口,那些官衙的走狗们不介意多几条人命。”
徐风问:“这些走狗交情也不深,会查的这么严吗?”
陈庭道:“这不关交情深不深,而是炫耀武力,这是他们一贯的作风,只有让我们这些平头百姓怕了,他们才能继续跋扈。”他继续看着徐风父母,很认真的说道:“那么谁能扛得起今晚的事呢?”
少年毕竟是少年,要说五个少年就杀了四个卫兵,还一个没死一个没伤的,谁信?那些走狗们,又有谁肯信?
女人拉了拉自己男人的衣袖,紧张的摇了摇头。
谁也没有开口。
就这么干等了好一会儿,期间,陈庭把断咬金拉到一边,低语了几句。
之后,断咬金拿过匕首,在三个半死的卫兵旁边走了一圈,女人惶恐道:“你,你干什么?”
男人想过去阻止,却是晚了。
断咬金把滴答滴答留着鲜血的匕首一甩,哼了一声,头也不回的顾自坐在一张桌前,斟了一杯。
过了半刻钟,酒馆打烊了。
平常的这个时候,北斗已经到家了,因为晚上漆黑一片,路不好走,所以他走得很急,趁着还有一点昏暗的余晖。
“今日收成不好,说不得又得去扮一回霸王了,本来这几张薄纸也够我凑合一顿了,偏带着你这么个饭囊酒桶,哎。”
“师傅,出家人不打诳语,每天都是我挑担做菜,没见师傅你做了什么,所以师傅,你又破戒了。”小和尚说话的样子很认真,语气里还有一点委屈。
北斗看去,一只杆子上挂了一张条幅,写着:“药医不死病,佛渡有缘人。”地上的毯上摆了瓶瓶罐罐二十余个,有周易八卦、甲骨、铜钱、竹签,旁边还竖着一座黄钟大吕。
一大一小两个和尚,大和尚很是魁梧,脸相有六七十岁,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咕噜咕噜直转,小的不过七八岁,大眼厚唇,抿着小嘴,本分老实。
北斗犹豫要不要过去,老和尚闭上眼,敲打木鱼,喃喃道:“见实相,诸法空,刹那顿悟万法同,……习显教,修密宗,方便门异归元同……”
这话呢,北斗是听不懂的,但细看之下,这一大一小两和尚只背了件袈裟,露了半个肩在外面,当下已是白露时节,逾秋近冬,一般人怎么敢这么穿?
想到方才惹下,偏还惹不起的血案,不免对这算命的有了些许期待。
“请坐。”
“你好。”
大和尚愣了愣,小和尚噗哧一声就笑了出来。
大和尚咳嗽了两声,问:“小兄弟这么晚还没有归家,定是有心事了,这世事总叫人发愁啊!我说的对不对?”
“嗯。”
“你也不必讲要看前程、姻缘什么的了,我为你看一看近期的运势、祸福,如何?”
“好的。”
“伸出手来。”
大和尚看了良久,开始还带着点微笑,这时候眉头渐渐紧了起来,他往北斗的手掌心上吐了一口气。
北斗也看着自己的手掌,这时候只觉得手掌的纹落清晰了起来,像是在发亮,又不像,就是能看得清了,在这昏暗的光线下。
大和尚缓缓抬头,看向北斗,目光愈发的沉邃,像是望到了山的那边,海的尽头,云的来处。
北斗不知道大和尚看到了什么,那是群魔乱舞之地,无尽深渊之下。
大和尚闭上眼,再睁开时又是一副能知过去未来八千年之事的模样,道:“你来看这一道命理,这是你十到二十岁的气运所呈,非与常人一般,本就是一道半隐半现的命理线,如雾里看花,充满变数,且这里却有一道大缺,生生断了纹路,这一道坎,……!”
“那我该怎么做?”
“这世间本是没有路的,人走得多了,就有了路。遇山嘛,那就凿道,遇崖呢,就筑桥好了,往前走、径直的走、自顾自的直走,这也是一种道。”
北斗没有都听明白,但能听得懂大概的意思。
“小兄弟,前路崎岖,还需一样护身的法宝才能保你平安,我这里的丹药,不说能生死死人白骨,但接续断肢,愈合内伤,都不过半天功夫。”
“多少钱?”
老和尚又看了一眼少年的衣着打扮,想了一想,说:“今晚正要收摊,偏巧在最后碰见了你,佛渡有缘人,那这瓶药,浑和尚我送你好了,收你一枚铜钱权当买口水喝。”
汉北斗的目光一下变得小心谨慎,这一枚铜钱就是普通人家半月的支出,买口水不过几张纸钱,哪用得着一枚铜钱?
大和尚咳嗽了两声,朗声道:“看来小兄弟还是不太信得过我这个浑和尚啊,别看我现在的破烂样子,今后你出了这小小的烛火镇,问一问我的名号,看哪个不知哪个不晓?”
“大师的名号是?”
“我佛号寸知,取天下之事,一分一厘,无所不知,无所不晓之意。”
两人相视无言。
“罢了。”和尚说着,从后边拿出一卷毯子摊开,有刀剑,玉佩,令牌,酒囊,竹编。
老和尚道:“这是一些拿不出酬银的客官,赊这里的。你挑一样好了,算赠品,这样你可满意了?”
北斗迟迟没有去拿,老和尚又道:“无序蛮荒之地,一把兵器可以防身。”
北斗看中一把精钢刀,很沉,他双手一齐发力,才勉强将其托起,这毯子上的几把兵器都是如此,沉且锋利。
北斗把铜钱递了过去,老和尚指尖一弹,小和尚接过铜钱,放到一个囊袋里。
老和尚看着北斗,轻轻一叹,道:“若是有朝一日,你觉得自己劫数难逃,不妨来我柯陀寺看看,我佛奉的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法旨,或许能为你驱挡一些劫数。”
北斗听不懂,但是记下了这段话,他点了点头,这时突然看到了惊人的一幕,因为小和尚轻而易举的举起了黄钟大吕,一大一小两个和尚消失在暮光下。
过了前面的弄子就到家了,但是北斗的脚步越来越慢,最后停在了那里,过了半分钟,他转身又往回走,起初走得很慢,之后是用跑的。
风雨码头医馆的门口,灯光很亮,照出一男一女两个身影,都是北斗熟悉的人。
断咬金走了,北斗又等了很久,他等的是自己说服自己内心,他心中有一道声音,连他自己都不知道,声音说的是,既然你们这么要好,我就不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