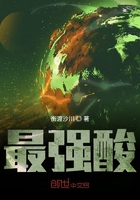小凤英端回那半盆子烂七八糟的驴肉,捡好的剁烂拿咸盐腌上,准备过年捏扁食吃,皮皮碎碎的留下来现炒着吃,剩下的那根黑不溜秋的东西想扔到猪圈里喂猪,可又琢磨牲口靠它传宗接代,人吃了一准能补身子一准会顶事儿,这样想着就又放回盆子里。但一想到王吉合跟驴比跟人情分还深,小凤英心里就有些犯难了。随手从盆里拿起那根东西颠来颠去,两头儿跳上跳下,脑子里便又不正经起来,觉得下身也湿乎乎的难受。想起来,她和他在一起就像是摸着黑拍巴掌,带着风,带着响,带着麻麻的刺痒,动作完全像他的脾气一样僵硬。她似乎习惯了他的僵硬,她喜欢他孙猴子一般用金箍棒把她挑向天空,再打到地下的感觉,说不清是“痛”还是“快”。世上最难用语言表达的就是痛感和快感,最容易忘掉的也是痛感和快感,这是两个最不长记性最没良心的东西。她只记得在飞向天空的一霎那,电闪雷鸣中那刺眼的太阳和赤身裸体的嫦娥以及突然炸开的王母娘娘的寿桃;她只记得突然很冷,浑身打战,别的就全忘了。
看着手里那根又粗又长又黑的东西,她又想起曾经听说过的一个故事,说的是一个仙女看上了一个小伙子,同房那天夜里发现那小伙子的本钱太小,就从怀里掏出一根银针在小伙子的命根儿上扎了两下,立刻就变得又粗又长又大……她情不自禁地捻着手指头,好像捏着一根银针。
回过神来,小凤英看到地上那个酸菜缸,忽然想到了给王吉合做造吃的法儿了。她把那东西放到案板上,先把它切成片儿,再把片儿剁成碎碎的肉末儿,和着点儿酸菜整了满满一大碗放着,然后就盼着天早些黑下来。
其实,这时太阳刚偏过头顶,除了天狗吃了日头,哪能黑得那么快。吃了午饭,小凤英就到三队会计家串门儿。三队会计媳妇板妮是棵粘老鼠草,见小凤英来了就把她按坐到炕沿儿上,赶紧放下饭碗,然后便家长里短、咸老婆淡舌头地说了一大堆,最后说出一段稀罕事儿,把小凤英惊得差点炸了尿泡。板妮说,你说二队喂驴的满柱丢人不,自己有老婆,非得把傻牛牛哄到驴圈,还是在驴槽上,哎哟,臊死了,现在是二队抓住了,三队也抓住了,就差一队了,都嚷破肚皮了你还没听说?汉子才去了水库几天就憋不住了,真骚气。小凤英忙小心试探道:“一队妇女们还比较平稳,不知你听到啥风声没有?”板妮说:“这倒没有,也许有不过可能干得严实,又都不是太监尼姑谁能说得清?”听了后半截儿话,小凤英就又心慌起来,肚子直往下坠,紧得上茅房,忙说这两天走肚,我得赶紧回去。说完就告辞出来,回到家在炕上静了一会儿才去地里上工。前晌小凤英告了半天假没上地,后晌去了听到的全是些那方面的事儿。妇女们在一块儿嘴都骚,想象着说出来的话都不能听,其实那都是编造别人过自己的干瘾。小凤英也不多插话,专意听有没有关于自己的话头话尾;听了半后晌也没听到有关自己的话音儿,心里才安稳了下来。
其实,谁能当着她的面说她的闲话啊?荒珍前晌那些话不会立马让她听到的,倒是后晌收了工在半道上五金扔给了她一句话:“背后有眼,窗根有耳,你胖了啊。”小凤英听了有些发蒙,一时儿拿不准五金指的是啥事儿,可自己除了是富农老婆,还有和王吉合的事儿以外,没有其他事儿啊,富农又不是一天的富农了,富农老婆就不能胖啦?一准是指和王吉合的事儿,她五金看见啦?噢,碰见过一回哩,可一队哪个娘们不去驴圈找王吉合问驴啊?五金你恐怕去得最多了吧?去多了莫非就胖啦?哎哟,是不是她也看出我的肚子不地道了?肚子迟早也掩盖不住,这可咋办哩?管他哩,仰排脚擤鼻子擤到哪儿算哪儿,只要没有光着屁股叫人捉住,这肚里的孩子不是你王大门的也是你王大门的,登科的话里话外明显向着王吉合,明显是想叫王大门认上这孩子,到时候这个哑巴亏王大门不吃谁吃?不想这么多了,车到山前必有路。
快收工时大喇叭的广播,小凤英也听见了,她想以后黑夜肯定闹得紧了,再去驴圈脱裤子绝对是不敢了,为了肚子里的孩子也不能了。但她知道这两天王吉合太伤心伤身了,估计吃不好睡不好,远远瞅到过他,人瘦得像扒了一层皮,脸色也不好,发灰发黄,她心疼他,别管他脾气好赖,是人不是人,反正是自己肚子里孩子的爹。小凤英下了决心,这碗酸菜肉一定给王吉合送去,哪怕这是最后一回;她琢磨好了,最好别碰上人,就是万一碰上了,为了讨好饲养员自己以后用驴方便,送一碗好吃的也很正常,给他缝缝补补、送吃送喝的也不是光她小凤英一个人。
回到家,小凤英在蛤蟆炉里焱上柴、放上铛锅,拿大麻籽油了一下锅,搁了一瓣蒜炝味儿,再倒进那碗酸菜和驴鞭肉末,炒好了拿勺子刮进大碗里,先拿盆子扣上。然后,小凤英从盆子里拽出两疙瘩已经发开的白面,在案板上擀了四个狗舌头饼,搁进铛锅里烙熟了。小凤英拿过用边角布缝成的棋子书包,先把那碗菜放进去,再把那四个狗舌头饼插到碗的四周,系紧书包带儿,提起来试了试,又放到了坐柜上。王大门回来闻到香味儿就问:“做啥好吃的啦?这么香。”小凤英没带理他。王大门吸着鼻子,循着香味儿走到坐柜跟前,用手提提那个棋子书包说:“有一股尿骚味儿,驴****肉啊?吃啥补啥,快去送吧。”小凤英看看外面天有点麻麻扎扎黑了,瞪了一眼王大门,提上棋子书包就往外走。王大门在后边坏笑着说:“小心点儿吧,黑夜可有民兵站岗哩。”
小凤英出了大门,正要往驴圈那个方向走,听到背后有人喊她,扭头见是歪歪他媳妇捧金,便转过身来说:“是你啊捧金,叫我有事儿啊?”捧金说:“你去干啥啊提着书包?”小凤英稍一迟疑说:“噢,咱队不是分了驴肉啦,我去给俺姊妹送点儿尝尝。”捧金说:“凤荣不是在东头啊,你咋往西头走啊?”小凤英立马又说:“噢,我想先去问个驴,再去俺姊妹那儿。”捧金说:“啊,那正好,我也想去问驴,歪歪今儿后晌回来了,我想明儿早碾磨点儿面给他改善改善。”小凤英赶紧改口说:“噢,哎哟,你先去问驴吧,我得先把驴肉给俺凤荣送去,看一会儿凉了。”说着立马往回走,捧金在后边说:“那我先去了啊。”
扭头看看捧金已经走没影儿了,小凤英赶紧又转回了家。王大门一边吧嗒着旱烟袋,一边阴阳怪气地说:“告诉你现在风紧势头不好你不听,让民兵给堵回来了吧?”小凤英没好气地说:“别放屁了,你就不念个好经。”王大门说:“我这可是为你好啊。”小凤英说:“哼,你一撇拉那根拐腿就知道你心眼儿也歪了。”王大门说:“不撞南墙不回头,我看你也是个犟驴。”小凤英没拾他的话茬儿,往锅里添上水,出去揢了一把柴开始烧火做饭。她想稍等一会儿再去驴圈。
驴圈里,王吉合觉得胃口顶得慌,从早起到现在就吃了一个烧山药,先是烧心,然后就是肚胀,憋得耳朵嗡嗡响,老想打嗝出长气吐酸水,只有平躺下才感觉舒服些。
刚迷糊上,原队长歪歪提着个送饭罐子推门进来了,见王吉合躺在炕上睡觉,便把罐子放到三屉桌上,然后咳嗽一声坐到了旁边那个卧柜上。王吉合听到动静,眯瞪着眼看了看歪歪说:“你老婆刚才不是来问过驴了吗?你咋又跑过来啦?”歪歪说:“我知道,我后晌刚从水库上回来,想过来跟你坐坐。俺大伯他们自己淋了点黑枣酒,快过年了,给你拿了点尝尝。”王吉合边起炕边说:“拿那干啥,我又轻易不沾酒。”歪歪说:“尝尝吧挺有劲儿,倒到酒盅里拿火点着基本上能烧完,喝两盅晕晕乎乎哩准能睡个安生觉。给你倒到啥里头啊?”王吉合说:“就倒到龛里那个送饭罐里吧。”
王吉合起炕往锅里倒了半桶水,焱上干柴,边烧火暖炕边说:“水库工地上那么忙,你跑回来干啥?”歪歪说:“家里捎去信儿说俺奶摔了一下子,躺在炕上不能动,屎尿都得俺老婆拾掇,摔得确实不轻哩。”王吉合说:“打算啥时候走啊?”歪歪生气地说:“我就不能听别人催我走,后晌俺奶让我别管她让我走吧,我就嚷了俺奶一顿,吉合叔你评评理儿,咱贫下中农出去受罪,留下王大门那富农分子在家里背炕头,他腿拐了手也断啦,我就是攀比他王大门。”王吉合说:“你跟他攀比不着,他是啥阶级,留在家里也没有少批斗改造他,这种人危险,要是到水库上搞起破坏来可不得了。”歪歪说:“这么说还差不多,哎吉合叔,小凤英不是说要来问驴推碾哪,是说瞎话还是来问完走啦?”王吉合没好气地说:“你小子心眼儿不正,噶咋子货,她不走我还能把她拴到槽里喂着啊?”歪歪笑着说:“不是不是,我也是顺口说出来的。”
歪歪又没牙没齿地扯了一些咸淡话,最后扯到了那条口袋上。歪歪说:“吉合叔你也不是别人,待我也不薄气,我就告诉你实话,那天口袋里的粮食我吃了,也不清楚是哪个****的鼓捣粮食,当时要是有人敢认领了口袋,我非收拾****的不可。知道也没人敢撑头儿,****了好长时间的心,看谁敢对那条口袋多看两眼,我就敢问问他个究竟。”王吉合说:“我就多看了两眼。”歪歪说:“吉合叔,你就是把眼珠儿都看到口袋上边儿了,我也不疑心你。倒是小凤英有些不地道,听说她走到半道儿又返回去了,可我思想她也没那胆气。我还是猜疑那两个民兵,****的弄得我人不人鬼不鬼的,得空我要刨刨根问问底儿。”王吉合说:“要是弄清了也够他们喝一壶的。”歪歪说:“话又说回来,也没啥意思。多个朋友多条路,多个仇人多堵墙,今儿也是说起闲话来随便叨叨,可我就是咽不下去这口气。”王吉合听他这么说也不想接茬儿再说,眯着眼张着嘴哈欠连天,歪歪看出这是在撵他走,就顺势说天也不早了,该走啦。王吉合也不说挽留的话,任他走出去,然后自己也到炕上歇着了。
在歪歪去了驴圈时间不长,小凤英也出了自家大门,她没有打保险灯,左手提着棋子书包,右手遇到墙就摸着走,遇到空地儿就摆动右手平衡着身子。运气还算不赖,一道就碰上了一个人牛犊,还是个哑巴,担着一担水过去了;已经看见驴圈窗户上的灯光了,再走几步下了一溜光台儿,往前十来步就是驴圈场。这时,地上突然旋起一阵风,刮得沙土和叶子欻欻作响,小凤英吓得赶紧躲到了墙角,绷着嘴侧着耳朵听听没啥异常,便吐掉嘴里的沙碜,赶紧跌跌撞撞地往驴圈摸揣着走去。到了驴圈外间屋门口,听到里面有人说话,立马转身快步去了圈那边大门口,待了一会儿,冻得实在呛不住了,就踮起脚把顶绊儿拔起,幸好还没插着插关儿,轻轻推开个门缝儿挤了进去,然后又轻轻关上。和外面相比,圈里暖和多了。小凤英靠到拴大闺女的槽边上,摸摸它的脑袋,小声说:“多吃点,明儿早我还使你推碾哩。”
外间屋歪歪说话的声音很大,小凤英并不在意他说了些啥,只关心他啥时候走,就盼着听到一声“我走啦”和紧接着一声门响。小凤英觉得过了快半年时间了,才终于听到歪歪说:“吉合叔,天气不早了,我走啦。”随后就是叫她心动的一声门响,但她没敢立马过去,怕歪歪万一又返回来或者躲在外边偷听,她在心里数着数,边数边笑自己干啥也得数数,从一数到了三百下,她这才长出了一口气,提着装着酸菜肉末和狗舌头饼的书包,走过驴槽,迈上台阶,轻轻吭吭了两声,撩起门帘,快步过去把书包里的那碗酸菜肉末和狗舌头掏出来,放到了墙根大瓮上,然后抓上书包,赶紧退回来站到了过门口。
赶王吉合听见动静猛地起身下炕,小凤英已经退站到了过门口。王吉合小跑过来,低声吼道:“奶奶呀,你想找死啊。”小凤英拿手指指墙根的大瓮上,小声说:“看看你都耗成啥样儿了?给你炒了一碗酸菜,烙了几个狗舌头,趁还不太凉赶紧吃了吧,你不是后天去开会啊,就算是为你送行吧。”王吉合丧着脸说:“不要不要不要,赶紧拿走赶紧拿走,以后咱俩势不两立,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永远不要见面了,快拿上你的东西走吧。”小凤英流着泪说,“好不容易拿来了,幸好还没碰见人,东西我是不拿走了,不愿吃就喂了驴吧。不用你撵我,赶死我也不来登驴圈的门边儿了。”说着就往门口走,王吉合上去拦住她叫她还走圈那边大门,她头也不回走向那边门口,王吉合紧走几步赶上去,猛地从背后搂住她,然后又轻轻一推说:“走吧。”她说:“别忘了我肚子里怀了你的孩子。”他说:“还有点儿麦……你快走吧。”她拉开大门扭头说:“明儿早起我使驴推碾,还给我留下大闺女吧。”
王吉合送走小凤英,关上大门,把脑袋抵到门扇上小声呜咽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