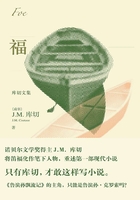那个周玉谷一进派出所,看见黑风着脸的公安,腿一软,跪下就说:“不用打我了,昨天夜里皇沟村已经替你们揍了我半宿,我主动交代吧?”公安叫杜中秋,听了有些好笑,上去踹了他一脚,说:“谁对你说公安打人了?”周玉谷赶紧说:“没有没有没有。”杜中秋说:“跪着干啥,上坟哪?给我滚起来,老实给我交代。”周玉谷于是老老实实交代了他们的罪行。
皇沟大队全民皆兵抓贼的事,受到了公社的表扬。特别是王吉合与坏人搏斗,英勇负伤的事迹,通过公社报到了县里,县电台采编成了一篇通讯稿《一心为公干革命,奋不顾身抓坏人》,并在全县的小喇叭里广播了。
这下子王吉合出名了。如果外边有人不熟悉皇沟村或打听皇沟村在哪儿的,知道的人就说:“连皇沟都不知道啊?就是王吉合他们那个村啊。”说驴也离不开王吉合,这是人家王吉合的驴,看人家王吉合的驴喂得多壮实。他的英雄形象算是树起来了,连大人们都拿他吓唬孩子们,再不听话就让王吉合把你背走了啊,还啼哭?王吉合来了;小孩们生气,也拿王吉合挡驾,再欺负我我去告吉合爷爷说,拧烂你的耳朵;快跑啊,王吉合来啦。
大队学校校长文奎想叫王吉合给学生们上堂阶级教育课,于是后晌散学后就去了驴圈。那天,王吉合刚放驴回来,驴群撒在驴圈场上。文奎挤在驴群里向王吉合摆手,王吉合大声说:“稀毛,你不上课来这儿充数啦?”文奎小名叫稀毛。文奎使劲儿拨拉开驴群,走到王吉合跟前说:“吉合爷爷,你可是出名啦。”王吉合摸摸头上那块疤说:“出****啥名哩,出了一摊血。”文奎继续套近乎:“吉合爷爷,刚放驴回来啊?”王吉合说:“有事儿说事儿,没事儿赶紧去上课。”文奎说:“都啥时候了,早散学了。吉合爷爷,黑夜做啥饭啊?”王吉合没好气地说:“吃啥饭?我吃驴粪蛋子你管着了啊?快走吧,别在这儿瞎搅和了。”文奎说:“吉合爷爷,我想跟你说点正经事儿。”王吉合边给驴抹拉身上的土,边说:“有屁快放。”文奎立马接话:“我放我放,不是不是,我说我说,吉合爷爷,我想请你给学生们上堂阶级教育课,沾不沾?”
王吉合一听这话,马上住了手,说:“嘟嘟了半天,这才算拉了点正经东西。阶级教育课早就该上,学生们都快让那个夜生给教歪了你也不管,你看看现在的学生,坐不安立不稳,每天光知道****打架抱骨碌。有的孩子都上学了,像正月家那个老三,十二三了还钻在娘怀里摸****吃奶哩,也不嫌害臊;还有帮牛家那个五小,八九岁了还赤着屁股乱跑,屁眼沟里儿里还夹着半截儿屎,真****干哕。文奎你小时候更操蛋,双灶在平房上躺着睡觉,你撅着屁股冲人家嘴里放屁,差点儿把双灶呛死。”
文奎红着脸说:“你说这干啥。哎吉合爷爷,别人都说你平时丧着个脸、咕嘟着个嘴不言语,凡人不搭话,我看你今儿黄昏的话一箩一筐的挺多哩。”
王吉合说:“废****话,该说才说哩。”
文奎问:“吉合爷爷,你啥时候有空去给俺们阶级教育啊?”
王吉合说:“这是正经事儿,啥时候都沾,越快越好。”
文奎说:“那就明天上午吧?”
王吉合说:“少给我转文,啥****明天,是明儿啊,啥****上午,是前晌。”
文奎说:“对对对,明儿啊前晌。”
第二天前晌,文奎早早就把学生们集中到了窑洞课堂。讲台上放着一张课桌和一个板凳,黑板正上方贴着一张主席像,两边是用红纸呈菱形贴的语录,左边是“好好学习”,右边是“天天向上”。窑洞两边墙上各贴了三条新标语,后墙上是“贫下中农管理学校”、“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向王吉合同志学习”,前墙上是“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不吃老本要立新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文奎正在训练学生们如何欢迎王吉合的时候,他推开门进来了,学生们马上七嘴八舌地喊叫道:“吉合爷爷好。”王吉合一辈子真还没见过这么热烈欢迎自己的场面,激动得他直后悔自己没带半簸箕炒玉茭豆给孩子们发发。
那天,王吉合穿了一件对襟粗布棉袄,一条大裆粗布棉裤,小凤英背地里给他拾掇得还算干净利索。他站在讲台上往下一看,黑哇哇一片,脑袋有些发晕,心也慌乱地跳,赶紧用手扶住了课桌。
王吉合使劲儿咽了两口唾沫,定了定神,然后大声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高举毛主席思想伟大红旗,领导咱们事业的孩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咱们思想的是******思想,同学们记住了没有?”
孩子们齐声说:“记——住——啦。”
王吉合又接着问:“大伙说毛主席说得对不对?”
孩子们拉着长嗓儿说:“对——”只有一个小女孩儿站起来说:“吉合爷爷,毛主席说得对你说得不对,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我们不是咱们,不是孩心是核心。”
王吉合说:“你是南坡格冉她孙闺女吧?鸡蛋大的人你知道个屁。毛主席是咱老百姓的大救星,他老人家知道咱没文化,就是念差一个半块儿字儿也不会怪罪,稀毛你说是不是?”
校长文奎站在讲台下边,听王吉合问他,赶紧说,是是是,哪能不是啊。
王吉合高兴地咧了咧嘴,然后神秘地问:“大家说一滴儿汗水儿掉到地上能摔几瓣儿?谁知道就举起一根胳膊。”
有一个男孩儿站起来,正要说话却被王吉合拦住了,说:“没规矩,不举胳臂不算数,坐下重来。”
这个男孩儿只好坐下举起了手,王吉合看没别人往起举胳臂,便就坡下驴,指指这个孩子说:“就你吧。”
这个孩子站起来说:“吉合爷爷,你说的那滴儿汗是掉到石板上还是土地儿上?土地儿上是玄土还是实土?”
王吉合白了那孩子一眼,没好气地说:“你是河滩边拗到底他小子吧?跟你爹一个****毛病,卧下吧。”
老师和学生们听了都掩口小声笑。王吉合并没有觉出哪里出错,继续说道:“就掉到石板上吧,哪个说能摔几瓣?”
学生们你看我我看你,大眼儿瞪小眼儿,瞎猜起来。有的把自己的唾沫吐到桌子上数数儿,有的拿手指头蘸着唾沫在木板上写字,有的猜不出干脆就在自己的指头肚儿上画起小猫儿小狗儿来,胡乱叽叽喳喳一通也没说到王吉合的心坎儿里。王吉合恼着脸说:“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连贫下中农的汗水掉到地上摔几瓣儿都不清楚,真是忘本了。下面全体立起来,到外面儿场上起劲儿跑,跑出汗来亲自往石板上掉掉,亲自数数到底几瓣儿。”
一声令下,孩子们喊叫着拥出窑洞,到外面操场上跑起来。跑到十几圈儿,孩子们头上都湿乎乎了可掉不下汗来,再让跑就跑不动了。王吉合让贫下中农子弟歇歇儿,叫三个富农子弟继续跑,又跑了十几大圈儿,王吉合把三个孩子拉到墙角一块儿石板上,让他们摘下帽子低下脑袋掉汗珠。冷风一吹,三个孩子直打哆嗦,光见头发里往外冒热气不见往下掉汗。王吉合就骂这三个兔羔子也是剥削阶级,根本就流不出劳动人民的汗水。
骂完,王吉合让文奎把碌碡骨碌过来。操场也是麦场,每年夏天二队就来这里碾场打麦子,过了麦收,碌碡便骨碌到窑洞墙根竖起来放着了。
王吉合解开棉衣再叉开两腿,两手紧紧扣住碌碡一头的底边儿,憋足劲儿往起,脸都憋红了也没起来。文奎上前去帮他,他不让,还说他年轻时一个手就能****起来。试了五六次也没成功,第七次他急了,把脸贴紧碌碡,撅起屁股,嘿的一声憋出两个响屁,碌碡终于给了起来。他趴在碌碡上喘粗气,头上已大汗淋漓,汗水顺着脸往下滴,滴到了碌碡上;他忙把孩子们招呼过来,孩子们赶紧围过来看汗珠儿到底能摔几瓣儿,汗瓣儿并不太明显,就数汗珠溅出的齿齿儿,七嘴八舌地也没数出一个统一齿儿数来。
王吉合歇过了劲儿,系上衣扣,让学生们回到教室坐下,然后意味深长地说:“孩子们,当大人不容易呀,做贫下中农更难哪!我啥活儿也干过,汗流了不知多少盆子。有一年给地主家背石头修地,汗把裤裆都湿透了,和尿了裤子一模一样,脸上的汗真的是往下流啊,吧唧吧唧掉到石头上,闲着没事儿就蹲下来专意儿数了数,大伙儿猜几瓣儿?不是吓唬你们,整整二十一瓣儿,回去问问你们家大人谁摔过二十一瓣儿?——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我王吉合的脑袋为啥跟枣核一样这么小,那都是给饿的。我斗大的字不识一升,脑袋里盛的尽是脓带,没有墨水儿,孩子们以后你们可要使劲喝呀,一天一瓶不够就喝两瓶、三瓶,没钱买墨水就找你吉合爷爷,我就是砸锅卖铁也得供给你们喝啊!”最后的“啊”字已是满含泪水了,王吉合也不管别人,紧着先激动得恸哭失声了。
校长文奎见状,马上举起拳头领着学生们喊起口号来:“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向贫下中农学习!”王吉合用袖子抹了一下眼,也举起拳头领呼了两句口号:“无产阶级**********万岁!”“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岁!”
回到驴圈,王吉合浑身觉得酥爽,看啥也顺眼了,连平日下最讨厌的狗和鸡,也让他高兴得扔给了它们半块山药和一把玉茭豆。他抬头看看日头,还不到晌午,便赶上牲口,嘴里哼着山西梆子上山放驴去了。到了阁老沟,把驴撒到阳坡上,王吉合吸了两袋旱烟,看看周围山上没人,便冲着太阳扯着直嗓子大声唱起了《东方红》。在山下干活儿的人们听到这号叫声,议论道,这老绝户是不是夜里做梦娶上媳妇啦?王吉合是不是摔了个跟头拾到了十块钱啊?从来没听到他这么叫唤过,哎呀,他会不会也和他兄弟祥合一样突然气迷疯了?
黄昏,王吉合赶着驴从山上回到戏楼坪,正好赶上学校散学,孩子们见了他,争着抢着跑到跟前喊他“吉合爷爷”,把他美得屁眼儿都流出香油来了。一进驴圈,他就当着驴的面,手舞足蹈地演开了胡子生,本来就没有多少斤两的身子更加轻轻飘飘了,如同憋了一泡尿、一泡屎,终于找到一个背静处一泄无遗后的痛快。王吉合想不起来做什么事儿也这样痛快,他满屋子寻找,当眼光落到炕上那条破褥子上时,心里突然就记起了那痛快。嘿嘿,老天爷造人想得还蛮周全,造出个男人撅着屁股干活儿,又造出个娘们仰着肚子睡觉,让凡人也能尝尝上天入地的滋味儿。想起来,人跟六畜也差不了多少,只是多披了一张人皮,脱了衣裳光着屁股一个**样,吹灭灯没一个正经东西。想起了驴配种,公社配种站的贵庭骑着他那头黑叫驴各村转悠,那叫驴喂得壮实,皮毛明光擦亮,哪个村儿配种都得先给它好料吃。草驴被拴到树上,一个人拉紧缰绳,一个人还得扶牢屁股,贵庭看准备得差不多了,就用手拍那叫驴的屁股,叫驴就耷拉出那长长的东西,贵庭再用手拨拉那东西,那东西就硬了起来,在上面涂上肥皂,叫驴便搭到草驴背上,贵庭就帮着叫驴配种;草驴起先不听话,后来也就闭上眼不闹腾了。想着这些,王吉合身子的中路也便难耐起来,燥得他光找带缝儿的地方瞅。很自然就想起了小凤英,王吉合恨不得小凤英现在就死到他的土炕上来。
想了足有一个时辰,还真把小凤英给想来了。屋外早已黑了下来,除了风吹着一些破草烂叶跑动外,没有任何响动,好像一块坟地;屋里时不时发出驴的喷鼻声和蹄子的刨地声,王吉合倒觉得驴在他的肚子里折腾。微弱的灯光下,小凤英从怀里掏出一包东西,往桌子上一摊,原来是白面狗舌头饼;小凤英腰里鼓鼓凸凸的,王吉合猜是面袋子,便琢磨她今夜稠的稀的干的湿的都要占全了。王吉合已顾不了这许多了,把小凤英拖到老地方便响动起来。这次王吉合心里本来就急,又怕拖长了粮食太多,所以精神都往一个地方集中,没动几下就完事了;小凤英却摁着那东西不撒手,王吉合忍着酸麻又来了五六十下便彻底龟缩了。小凤英下边还是热辣辣地难受,便又强把王吉合鼓捣到半软半硬的程度来了一回,才总算勉强吃了个多半饱。
小凤英软软地躺在干草上不起来,只是伸出右手,先比画了三个手指头,又比画了三个手指头,再比画了五个手指头。王吉合知道她啥意思,可突然想起来了那天黑夜给她的两袖筒白面,就说:“不是提前给过你了,忘啦?”小凤英吃惊地说:“提前给过,啥时候啊?”王吉合说:“那天黑夜,袖筒里装的,不记啦?”小凤英不高兴地说:“啊,原来我还欠着你账哩。”王吉合说:“那今儿黑夜咱就算清了啊。”小凤英忽地坐起来说:“你还欠我哩。”王吉合歪着脑袋说:“我还欠你啥哩?”小凤英蹬上棉裤,系好腰带,一字一板地说:“今儿黑夜总共三百三十五下,两袖筒白面不到十斤,按老规矩一下一把,顶多算八十下,刨去旧账八十下还剩二百五十五下,去了零头,你还欠我二百五十下粮食。”王吉合一听脑袋就大,晕头晕脑地说:“瞎****算,哪有那么多啊?莫非软硬都算数啊?后边那是你硬鼓捣我哩,不能把这数这粮食也归到我头上。”小凤英说:“你这个人真日怪,就算是我鼓捣你,你那物件儿莫非去捅墙窟窿啦?俺穷俺贱,给不给由你,可账得这么算。”王吉合也在算账,他眨巴眨巴眼睛说:“数就按你记的算,可粮食得分成两样,前一百五十下给你玉茭,后一百下给你高粱。玉茭跟高粱和到一块儿碾碾蒸干粮也不难吃。”
王吉合的话还没说完,小凤英抻抻衣裳,拿起口袋往胳肢窝一夹,就往外走;王吉合上去拽她的口袋,她一巴掌打开他的手,继续往外走。王吉合在后边撵着说:“刚才算我没说,不给你高粱了都给成你玉茭还不沾啊?”小凤英只顾跌跌撞撞地走,并不理他。快走到过门那里时,听到那边有人拍门,王吉合小声说:“你快去刚才那儿躲躲,一会儿我给你把玉茭抓到口袋,还给你藏到一队场啊。”说着拽过小凤英的口袋,放到过门台阶上。
王吉合开开门见是五金,就说:“黑天半夜你来干啥?”五金提着簸箕往四下看了看说:“拍了半天门才开,你忙活啥哩?”王吉合斜了她一眼,没好气地说:“正忙活驴哩,你拿个簸箕来干啥?”五金说:“想借点儿粮食。”王吉合瞪着眼说:“让你去了回俺家,替我碾磨了点白面,你就吃惯甜甜跑惯腿啦?你是不是把俺家的大瓮都翻腾遍了?”五金说:“你把我当成啥人了?”王吉合说:“那你平白无故借啥粮食?”五金说:“你着急啥哩,我又不借你自己家的,我想借半簸箕驴饲料。”王吉合说:“那更不沾,驴饲料是公家的粮食,谁愿意借就借啊?驴饲料是有数的,借给你驴吃啥?”五金说:“我又不是光借不还,半簸箕粮食,每个驴少舔一嘴啥都有了。”王吉合说:“你说得倒轻巧,牲口吃不上饲料,你去替它扛驮啊?”五金说:“你越说越不是人话了,全村就我这么一个致近亲戚,有困难了除了不接济我还恶言恶语伤亏我,以后再有事儿少找寻我啊。”说着便提上簸箕往外走。王吉合见状也软了口气,指着墙根的大瓮说:“都快空了,只剩下个粮底子了,明儿啊我给你送家里吧。天不早了,你快回去吧。”
五金听了王吉合的话,不仅没走,反而转身到三屉桌旁边的坐柜上坐下了。王吉合心里惦记着圈那边的小凤英,便打着哈欠催撵道:“咋又坐下了?赶紧回去吧。”五金说:“撵我干啥?莫非还藏着别的娘们啊?哎哟,腰好困,我直直腰就走。”她边说边进去躺到了炕上,王吉合赶紧过去往起拽她,她乘机柔柔地说:“吉合哥,你就不想那个啊?”王吉合狠狠一甩她的手,凶巴巴地低声吼道:“我一直觉得你是个正经人,你这么对得起我土里头的兄弟啊?赶紧走,要不你以后永远别登我的门。”
五金出去后,王吉合赶紧跑到圈那边去,转了一圈儿,见大门的门闩开着,知道小凤英早就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