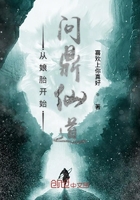小阎王老婆是个侉子,尽管基本上是皇沟话了,但说快了还是叽里咕噜听不清。侉子有名有姓,叫周连盼,可人们还是习惯喊她侉子,孩子们见了她或她的孩子们也总是喜欢叫喊:“侉子侉子呱哒哒,光放屁不生娃。”侉子说自己跟原来的男人生过一男一女,给人家男方留下了,但和小阎王没有生养。村里人都说是怨小阎王不沾,小阎王叉着腰一蹦一跳地骂道:“放你们的狗臭屁,老子的那个硬得嘎嘎的,能把碾盘撬起来,谁敢说老子的不沾?”人们背转他就说,光硬顶蛋事儿啊,莫非人都是拿撬杠撬出来的啊?看你也冒不出一股正经水儿来。
有一天,小阎王家又来了个侉子,这个侉子比那个侉子小个六七岁,她自然就是小侉子,那个就是大侉子了。大侉子说小侉子是她的叔伯妹妹,刚死了男人,老家大名太穷,想来皇沟找个人家过日子。小侉子叫周玉穗。小阎王两口子主张玉穗最好别找有孩娃老小的人家,最好找个光棍儿,就两个人,干大利索的多好;小侉子没意见,但还是强调说,我才四十来岁,千万别给我找那些老得没牙的人啊;大侉子说,放心吧,姐还不知道你的心思啊,不就是浑身两张嘴嘛,都让你吃饱就行了呗。
能满足小侉子两张嘴的,小阎王两口子首先想到了王吉合。大侉子说,王吉合的条件当然不错,但他跟正常人不一样,你给他办好事儿,他还不一定放啥屁呢;小阎王说,他再异样也是人,莫非他长着那个东西一辈子就为尿尿啊?我去给他说,说不定****高兴得能蹦起来哩。
不出大侉子所料,王吉合并没有高兴得蹦起来,倒把小阎王气得快蹦起来了,他倔狠狠地说,谁跟你说我要找媳妇了?我找媳妇干啥?你们不明不白弄回来个东侉子就想给我啊?凭啥就得让我要你们家的侉子啊?想讹人哪?小阎王气得在地上转圈儿,拍着胯骨,腆着肚子,指着王吉合的鼻子骂道,****,狗咬吕洞宾,****,活该你绝户,活该你断子绝孙,****,舔舔你的驴屁股吧,倒给老子窜了一脸,你个老绝户。王吉合说,老子就是老绝户咋啦?你这么献殷勤,想给老子顶门儿啊?想跟我连襟挑担,甭想。小阎王真想一镢脑揳死王吉合。
过了好几天,小阎王才好不容易消下了这口气。那时候的光景,哪能经得住长时间填张嘴啊,两口子都急着把小侉子打发出去,但小阎王是绝对不去厚着脸求人了,大侉子说,我去碰碰秃爪,看看他对玉穗有意没有。
估计快收工的时候,大侉子便端着针线笸箩坐到村口纳底子,瞄见秃爪担着柴筐走过来,低着头很随意地说:“秃爪,给你说个媳妇吧?”
秃爪咯噔一下站住了,说:“啊?大侉子,咋?你想跟我啊?”
大侉子依然没抬头,说:“不怕我淹死你啊?”
秃爪说:“我会耍水,狗刨、仰浮都会,你才淹不死我哩。哎,大侉子嫂,说正经哩,你给咱踅摸个老婆吧?”
大侉子说:“你真想媳妇啦?”
秃爪说:“嘻嘻,不想是假的。”
大侉子说:“俺叔伯妹妹玉穗刚死了男人,也正想找个人家呢,等我给你问问。”
秃爪说:“太好了太好了,你快给问问吧。”
大侉子说:“人你还没见呢就同意啦?”
秃爪说:“哪还轮上咱挑人家,只要是个女的,只要人家愿意就沾,嫂子你快给问问吧。”
大侉子撇撇嘴说:“看把你急的,我简直想象不出你这么多年是怎么挺过来的。”
秃爪说:“嘻嘻,硬挺呗。”
大侉子回去跟小阎王说了秃爪的态度,小阎王说,有点儿成色吧啊,别和羊发情猪跑圈似的倒赶人家,想起王吉合那嘴脸,我就又来气儿了。大侉子说,也是,有井还怕没人来打水啊。
过了五六天,秃爪自己找上门来了,大侉子把小侉子叫了出来。小侉子看秃爪,个子不小,头上毛不多,身体挺壮实,人样也凑合;秃爪看小侉子,长得黑糙污烂的,模样像汉子们,头上还罩着个毛巾,偷地雷似的,嗨,好赖是个女的。
秃爪说:“你看咱啥时候啊?”
小侉子说:“啥时候都行。”
大侉子说:“对上眼儿啦?那玉穗你今晚就搬过去住吧,明天记着去公社登记啊,别叫别人把你们当成通奸狗男女了。”
秃爪做梦一样搂着个寡妇热闹了一宿,第二天请了一前晌假,跟小侉子去公社办了结婚手续。后晌一到地里,人们就撺掇着给秃爪打喜儿,他说,算****了吧,一个老光棍儿一个二茬子货,都是老东西儿,有****啥喜儿可打哩,俺们都睡了一宿了。路宽说,比闹猪闹羊舒服吧?秃爪说,你就是蛋包子皮没正形儿。路宽说,干柴碰见烈火,一宿没睡吧?秃爪说,碰见好东西了还睡啥哩。路宽大声说,喂,大伙儿今儿黑夜都去秃爪家听房啊。秃爪说,不用专门去听,你们躺在自家炕上就能听到。路宽说,****,你敲大鼓哪,还叫全村人都能听到?
秃爪和小侉子厮跟着去驴圈问驴推碾,王吉合看了看小侉子没说话。秃爪说,吉合哥,你也该拾掇个媳妇了;王吉合斜了他一眼说,挺得是吧?奇能啥哩你?秃爪说,这不是为你好啊;王吉合说,用不着,你们想问驴推碾啊?驴都安排完了,等两天再问吧。
王吉合不是眼气秃爪说下了小侉子,那小侉子跟虫打了一样,满脸虫屎,满脸蛀坑,长得跟鞋底片似的,倒贴我也不要,关键是你秃爪不该不是光棍儿,好像就我该当光棍儿,让我的逼脸搁哪儿去?小凤英,你死哪儿了?非得等吃完粮食才来找我啊?哎哟,秃爪你也太能将就了,不管啥眉嘴的娘们就往被窝里挝啊?小凤英你到底死哪儿了?秃爪,我不能连你都不如。
这一阵子,王吉合黑夜早早就插上了门,谁叫也不开,有事儿隔着门说,本来这里鲜有人坐,他这么一倔乎,驴圈除了驴也就他一个人了。外面传来酸枣鬼一般的骂声和猫婴儿一样的哭声,王吉合在鞋帮上敲掉烟袋锅里的灰,使劲儿吹了几下烟袋嘴儿,然后歪到炕上歇着了。
王吉合刚迷糊上,外面有人敲门,他心里激动得嗵嗵直跳。谁啊?吉合哥,是我,五金;有事儿啊?嗯,快开开门。五金是王吉合的堂叔伯兄弟媳妇,男人麦收死后她没再改嫁。王吉合开了门说:“咋了三更半夜的?”五金气喘吁吁地说:“俺小子吉山病得快不沾了,你快给我派个驴拉上车去公社地段医院。”王吉合边往圈那边走边说:“黑天半夜的光你一个妇女家去沾啊?”五金说:“我把邻家巨贵纥捞起来了,哎吉合哥,你再借给我五块钱吧。”王吉合牵出弓脊,把缰绳递给五金,然后又到外间屋炕上的席子底下掏出两个两块一个一块,打发五金走了。
王吉合重新回到炕上躺下,嘴里嘟哝道,刚才我还以为是她敲门哩,差点儿把我高兴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