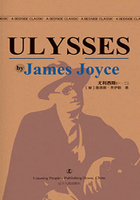那时的天空,那时的风云,那时的乌龙尾巴时常悬挂在东海的上空,说翻脸就翻脸。在夏季收割稻谷的时候,突然来的狂风暴雨,总让充满期待丰收收成的农民们空欢喜一场。天空似变脸的后娘,太阳一阵,暴雨一阵,男女老少在农田里来回地赶跑着。没有让稻谷晒干的机会,稻谷又再次发芽,让农民们徒劳一场。到了秋季就更不能理论了,台风与潮汐一起到来,家家户户都得摊派着人工去打海塘抗暴防潮,恐慌的人们整天忙得湿漉漉的,还要急忙做好秋季里的抢收。总是忙忙碌碌地等待到收获,又突然地失去。因为是老天爷在作怪,有什么办法呢,这对于农民是一种无奈的叹息!
总觉得那时的人间触怒了上苍与众圣,得罪了不可侵犯的神灵。你曾目睹一个佛门信徒的遭难与凌辱,她肩背着红面佛祖的木偶,要受到人间的亵渎与游斗,她是殿主婆,有那种勇敢、忍辱负重的精神,人们总是胆怯地躲避与嘲笑。破四旧,立四新,捣毁了神佛的殿堂。与天斗、与地斗的口号,有人敢说敢阻拦红卫兵小将吗?我们的政策是绝对阳光的,绝对地遵从,绝对地歌唱,可以把晴天说成雨天,可以把黑夜说成白天,但人们不能不服从当时的伟大政策。
到了晚上,在农村里各家的煤油灯昏暗得似鬼火,不能浪费的点灯,只有批斗大会点着的亮灯算是晚上的娱乐。阶级斗争要依靠发动群众,动员群众思想紧跟上,民兵每天在紧张地训练、备战。那时人们的脸色都在疑惑之中,都在紧张严肃之中,都在敌视斗争之中。特别注意“地富反”黑类分子是否不听调教,哭笑正常与否都得经过阶级的鉴定与贫下中农的监督。属于黑类成分的子女,只能多干活。只有埋头地干活,才能在群众中得到认可。
由于家庭成分的关系,阿平长大后的生活不是喜悦的开始,而是忍辱负重的来临。人们把千夫所指的地主后代,指定成永不得翻身的罪人,哪有过上好日子的指望啊!运动激烈的几年里,上初中都要经过阶级的审批,这一关键的条件就决定了前途的夭折,决定了春天的死亡。阿平童年就辍学务农,当了农民必须要埋头地苦干;而贫下中农的子女可以野蛮撒野,他们有着当时优越的阶级成分。
夏季里,有一次阿平与同龄的小孩,在田野上栽插秧苗打前阵。阿平是带头拉绳的,右手拿着不到一米长的竹条尺,而左手要用力地拉紧塑料绳子。因为对面拉绳的人离阿平很远,如有风吹来是很难拉直的。而阿平做事很起劲儿,总要做好。本来已拉直的绳子,中间有一女孩把秧苗栽成了弧形,每次总是她在磨蹭着,让田埂两边拉绳子的人等她一人。也许田里的水很满,摸不到绳子,阿平嘀咕了几句要她快点,而她一副傻傻的面孔,有些不服气。她哥哥本来和阿平好好的,却冲上来咒骂着阿平,说阿平欺侮他妹妹,抢去阿平手中的竹条尺抽打着阿平,说阿平是地主的儿子,没有资格说他的妹妹。他打够骂够还不过瘾,把阿平头上所戴的大草帽拿去,用脚踩在稀泥里,田里的同龄小孩好奇地瞧着,没一个敢说敢劝架的。还好大人们都不在,如果在的话,有人会说她的哥哥像电影里的英雄一样,打了阶级敌人的儿子。回家后阿平默默地哭过几回,但没有告诉过父母。
去年开春的一天上午,为了给田里的秧苗施肥料,阿平同生产队的社员们一起站在绿茸茸的地垄沟里。一个大人冤屈地指着阿平说他没把粪水瓢泼到苗圃间,由于他没听清楚阿平的回答而以为在顶嘴,就肆无忌惮地举起手中硬质的木扁担往阿平脑门敲来,几天下来额头的伤包浮肿都没消。后来,阿平的父母去责问那个大人怎么动手打小孩,但是对方恃着凶恶魁梧的躯体还理直气壮地说:“就打你们地主分子又怎样!”那时,阿平的父母被辱骂得狼狈而归。但是对方也是富农分子,那年月在同类里也有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皮那种鄙视的观念。
阿平少年的时候羡慕《苦菜花》《迎春花》书里的英雄人物,也讨厌汉奸、地主阶级的虚伪与剥削,并且迷恋上了文学作品。父亲很反感阿平看书,总说他自己念了这么多年的书没什么用,还不是照样当农民。但阿平有什么力量深入学习知识呢,才念了三年半的书,就随着父亲起早摸黑地在农田里干活。有的时候晚上在煤油灯下偷看着书本,又怕熬干了煤油挨父亲的骂。
阿平喜欢第二次耘田时候的绿油油的稻苗。不像第一次跪地耘田时稻苗无根不结实,稍不注意动荡着泥土,稻苗就浮上水面,还得赶紧地掩盖重新栽插着秧苗,怕被老农民看见说不会干活,破坏了稻苗。阿平还喜欢收成季节大片黄澄澄金灿灿的稻穗耷拉着,村前村后一眼望去是那样地平直而整齐。这里有他问心无愧的汗水!他已经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了,但阿平害怕收割稻子,那是最累人的季节。
在一次工分评比的晚上,按要求阿平能评上八分的劳力,而大人们一直拖延,不赞成给他加工分。有一位同宗族的长辈,因为是贫农的代表,说话做事在生产队里有着威慑力,他的性格倔强而霸道。在大伙聚在一起的一个晚上,他恶狠狠地说,给阿平加到五分就可以了。他的意思是说,这已经恩惠了“地富反”的儿子。原来四分五厘工分的阿平,等待了两年的时间,才加了五厘。每次阿平心里都有敢怒不敢言的委屈,因为出身是黑类的后代就得忍让,就得窝囊。但这次在他心中的一股火爆发了,忍无可忍地和对方顶了嘴,反驳他凭什么不按干活能力评工分,说加多少就多少,你世道好吗!他气势汹汹地走近,一拳击来,急忙中阻拦的父亲挨了一拳,哀求着阿公高抬贵手,说阿平年轻无知,说话随便。父亲被训骂得一无是处,对方才摆休。几天里父亲的脸还是青肿着,但是父亲总是不记恨对方,还是低着头尊称他阿公,好像以前挨打没发生过。那些靠边站的大人们不出来打抱不平,默默无言的,而且侥幸地为虎作伥认为年轻人说话不懂礼貌,挨打是应该的。也许在中间不说公道话的人,怕着贫农代表,有奉承的,有拍马屁的,还有笑哈哈了之的,更有的人心里在高兴。不多加劳动工分对自己没有害处,只有益处的,何乐而不为呢。老贫农蛮横的举动震慑了“地富反”的子弟,要老老实实、忍气吞声地干活。总之,父亲的心里也在恐慌着,担心贫农阿公要到大队汇报,说“地富反”的儿子对社会主义不满,说贫农在耍世道。
在一次社员大会上批斗阿平父亲的时候就是贫农阿公指出父亲梦想回到旧社会,做他的书生公子哥。贫为阿公揭发说,在岐山上的地瓜园里锄草的时候,父亲给社员们讲封建社会的故事。那天本是贫农阿公的堂弟,在劳动无聊时要求父亲讲“俞伯牙和钟子期墓前摔琴”的故事。台上的干部又发狠地质问着父亲是在腐蚀广大贫下中农的思想,不老老实实地劳动,是梦想回到旧社会的“牛鬼蛇神”。坐在台下起哄的群众指着父亲,同时指着一起挨批斗的祖母,说地主不应做损害社会主义的事。两人总是低着头,承认了自己的错误思想。台上的干部反感、责骂祖母尊称他们为阿公阿伯,说不需要地主婆对他们这样的称呼,为了划清阶级的界线,怕玷污了他们的阶级尊严。
若是台湾反攻大陆的话,首先枪毙了“阶级敌人”阿平的全家,这是一位老贫农在田埂上对阿平所说的话。阿平他才十二岁,双脚深埋在冰凉的泥水之中,用锄头耕耙着泥土,有些胆怯!有些恐慌!阿平心里怨恨着台湾不该有亲戚,特别是那个一九四九年逃跑到香港的伯父,为此他父亲每次在群众批斗大会上都得低着头认罪,大会上批斗说清台湾有无书信来往之事,还要批斗祖母想念敌方的儿子等等。
每天阿平随父亲在农田里不懈地劳动着,白天累得精疲力竭,到了晚上还要承受着耻辱的群众大会。这使阿平的童年过早失去了活泼与乐趣,过早懂得做人的忧伤。看着父亲从小学里背回了一摞摞的长凳子,还有自己家里所有的凳子,为了给会场在座的群众。批斗大会批判“地富反”的牛鬼蛇神阴魂不散,指责阿平父亲是否想着台湾的兄长等。在台下的阿平,弱小的心灵胆怯、战栗着,是否又遇到了可怕的阶级斗争运动。
“过对嫂”在那些岁月里是新中国农村男女婚姻交换的新名词,也是男女婚姻不幸的无奈选择。特别是出身地主家庭的子女,娶妻难,女儿嫁人难,都是被社会所贬弃的群体。他的父母只能采取婚姻包办,用女儿调换儿媳妇,这种婚姻的结合,只是为了传宗接代,并不是像古人所说的几百年前所注定的姻缘。但要通过媒婆或亲戚从中寻找着对象,择偶就不能选择同类的阶级成分,再让下一代继续承受辱骂声,而是要选择贫农的家庭。这种调换的婚姻,女方多数成了牺牲品,不能由自己恋爱他人,而是为了哥兄而嫁人。否则的话,在当地被歧视而没有女人敢嫁她的兄弟,甚至有的终身成了光棍汉。
自从阿姑、阿姐出嫁后再回到娘家,阿平从农田里干活回来,见到她们的脸上总是忧郁寡欢,从没看到有喜悦的神色。她们为了兄弟能娶到媳妇而满足,牺牲了自己的婚姻并不重要,农村人不就是这样地不用爱情过日子,她们总是拿这样的思想安慰着自己。因此她们一直乐不起来,这种调换来的婚姻,有时候婆婆还是会指桑骂槐地说,她们娘家是地主的成分,才肯嫁给她的儿子。
阿平十五岁那年,堂房阿公突然猝死。原因很简单,外甥女嫌弃娘舅是地主成分,待到出嫁的时候违背了婚约。阿公子女一共有八个,生活十分困难,大儿子三十来岁娶不回媳妇,如果外甥女违背了婚约,还有谁敢嫁他儿子呢。作孽的阶级成分,要牵涉到儿女的婚嫁,因此阿公非常痛恨、生气,心脏病复发就猝死了。乡亲们此时也到场哀怨着,有的还抹着眼泪,惋惜说他是好人。阿平作为家族里的小字辈,在送殡的那天派上了用场,与堂弟俩人抬着颤悠轻飘的遗照容亭。从山上返回的时候,堂弟没觉得累,而阿平感觉肩上背的不是摇荡的空架子,似乎抬的是一块沉重的石头,越抬越伤心。谁也逃脱不掉家庭历史的荣辱关系,阶级成分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命运,就连亲戚都成了敌我的对象!为什么一个外甥女说娘舅阶级成分是黑类是地主,就违背了婚约?地主是剥削劳动人民,欺压着劳动人民,是永不得翻身的阶级对象,是罪有应得的。这种阶级观念就在小学的课本里都已灌输到每个小孩的心灵中、头脑里,地主根深蒂固地成了可耻的概念。在广播里,在群众大会上,在村民的眼光里,都在排斥着旧社会所遗留下的牛鬼蛇神。或许外甥女是护卫着阶级的清白,大胆正确地违约,不是叛逆不道,而是明智的选择。她能够分清阶级的路线,是为了划清生存的荣辱观念才起来反抗的。
阿公的死带给人们沉思与警示,也得到了一些乡亲们的宽恕与怜悯,尤其是对外甥女的一些社会言论压力,娘舅用死来证明着亲戚间的绝情。外甥女经过亲人们的劝告,无奈中才同意了这门亲事,男方担心夜长梦多再次地被违约,就来了一次哀伤冲喜的娶亲,叫作“红白喜事”连着办的形式。这从没听说过、遇到过,这世界可悲而可笑,父亲尸骨未寒,新郎新娘七天的洞房花烛夜,难道新郎恪守着野性的冲动吗?四十九天应该给父亲戴孝服,乡亲们难道同样的糊涂吗?真是亵渎了苍天施予人间的文明。阿平抬着遗照容亭回来后,伤心地回到家里掉泪,不去吃那顿哀乐分明的糊涂筵席。
几年后,在阿平童年的印象里,还是对父亲被打的那一拳而耿耿于怀。有时总是从善良的角度来忍耐着,觉得这位老贫农性格耿直并不坏,不像其他的社员,拍马屁、谄媚奉承混杂的阶级,看不出他们的态度是真是假,站在中间打着哈哈。总而言之,是阶级成分把我们划分为对立面的,甚至用有色的眼光来压制少数的弱者,乡亲、亲戚之间相互鄙视,或仇视地斗争着。那位贫农阿公有一个贤惠善良的女儿,与阿平是同龄人,经常在农田里一起干活。每个季节到来的时候,干所有的农活,她都不次于男儿的技巧和干劲儿,从不旷工,同男儿一起下地。播种,插秧苗,施肥,割稻子麦子……样样都是得心应手。她都在默默地劳动着,但是阿平也很少同她说话,尽管心里羡慕她劳动的熟练。几年来在生产队里,虽然阿平心里还记恨她父亲倔强粗暴的性格,但阿平恩怨分明地对她有了好感。生产队农田挨她家里很近,阿平每次到农田劳动都要经过她家的门口——先要到少年朋友的家里,再一起到农田干活。少年朋友就住在她家的隔壁,是她同堂的兄弟,在同一个屋檐下相处着。这是前后两厢的五间矮屋,要从狭窄杂乱的走廊穿过,她在屋里总是那样友好热情地打招呼,阿平总要站上几分钟才离开,或许是同她套近乎。她不像她父亲那样对地主成分充满隔阂与敌视,甚至对他热情得似兄妹,因此阿平忘记了仇恨。
离开家乡在闽西的几年里,有一次回到家里,在一年秋收过后,冬种已经结束,这是喜悦轻松的日子。只有这时农民才有了空闲的几天,阿平偷闲几天在家里,对少年的朋友,对这座黑色陈旧的砖瓦矮房,有着深厚、特殊的感情。想到少年朋友家里串门,也想顺便去看望她,回味一起在农田里汗津津地你追我赶的干劲儿,力争上游的纯洁思想。不知道她已经出嫁了,但很巧她那天回到了娘家。阿平坐在少年朋友的屋里,听外面嘈杂的声音在找人,原来是在找她。赶紧出来帮着找人,首先到了小河的埠头上,孤零地摆放着一盆洗净的衣服,但却不见人的踪影。此时河面上平静地没有来往的船只,河边的水连一点涟漪波动、鱼星泡沫都没有。邻居们惊慌地又返回到各家屋里,在各个旮旯胡同寻找着,连拉屎的尿盆里都查看过,还是不见她的踪影,最后大伙的目标又锁定到小河。
此时,整个屋里老少邻居都来到了河埠上,拿着两根长竹竿的兄弟俩,是同一个生产队的社员,又是她的邻居,在河埠边往下测探着有无异物,划弄了半个时辰,水面上才漂浮起几根发丝。乡亲们又撑回了一只水泥船,挨离河埠几尺的距离,兄弟俩还是用竹竿探划着落水的位置,岸上的人们都焦急地等待有人下水救人。阿平看着那兄弟俩蔫巴慢悠的性子,心想:亏他们长得大个子的体形,胆小如鼠地犹豫着不敢下水救人,还指望着别人下水。年轻气盛的阿平,有些瞧不起这兄弟俩,脱掉外衣就自告奋勇地钻进了水里,摸到了绵软肿大的身体,埋在河泥里推挪不动,也许是落水时间过长的原因。阿平只好冒上水面,叫岸上下来一人一起拖起她,此时才有人大着胆子敢下水。怪的是,原来推挪不动的身体,为什么两人下水只轻轻地用手从底部一拨,她的身体就像停在水里的皮球,就变成了漂浮的异物。有的人还是用迷信来恐吓,说是阿平性灵小的缘故,河底下的鬼魂在作怪,她才被水鬼拖住不放。
整个河岸上已聚集了全村的人,都在盼望着。被救上岸的她还是活人,这纯属异想天开。早已有两位赤脚医生在那等候,做起了人工呼吸,挤压着她肚里的死水。但是她肚里已经怀胎将近十月,医生不敢狠劲地挤压着,她瞳神早已经散去,魂归阴间了。有的亲人还是不放弃,赶到太祖殿里,跪在神堂前求签许愿,做起死回生的祈祷。
阿平虽然捞起的是一具尸体,人们在质疑少年勇敢胆量的同时,设想着若是一个十月怀胎的女子,如果还没死在河里,反而被她拖住不放的话,那结果就不敢想象了。而阿平没有去想这些险恶,只是救人心切而已。从那以后一些红类的阶级家族,才放松了敌视与警惕,不像从前对外星人那样地歧视着黑类分子,也赢得了一些群众的另眼相看,但是谈不上转变人格尊严。
我们在这里沉思,历史带给无辜的人们的,是那样绝望而深刻的伤痛,不是其中的人们,是根本体会不到的。扪心自问,不就是阿平的祖上在勤劳中积攒了一些财富。有些贫下中农到了八十年代,仍居住着所分给的阿平祖上的房屋,他们的进取心在哪里呢?
巴金老先生在一篇文章里提到,国人还是不敢说真话,有怕说真话得罪人的弱点。根深蒂固地只在感激一个世界观念,一个王朝的胜利。阶级斗争所搞的运动,麻痹了几代人的思想,违背了人性的本质和社会的规律。到了二十一世纪,人们有了和谐做好人的社会理念,这绝对与国家的口号有关,这与教育子女是相同的概念。
一个人应有的财富,是要依靠辛勤劳动得到的,也是冒着风险胆量才拥有的,绝对不是靠依赖、嫉妒他人的富有。经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的大多数贫困群众,还在依赖着国家对他们的一些优越与恩惠。到了改革开放,国门大开的八十年代,仍怀疑地抱怨着,仍在不平衡之中,原先的阶级斗争到哪里去了,为什么不用运动派性扣压的帽子来整治兢兢业业的人们?为什么农业不集体劳动,要分给个人单干呢?本来在各个行业里滥竽充数的人们总是存在着,此时五花八门的现象展现在每个人的眼前。
幻想回到过去的阶级斗争的迷梦已经被历史所淘汰,为现实所抛弃。社会要和谐,每个人都要努力做一个好人,如此方可摆脱千年来农民们悲苦的宿命。
1996年8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