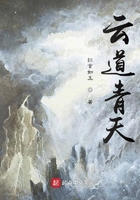大妹去世已经九年了,这九年的时间里……似乎有某种寄生虫在你的灵魂里啃噬着,无法让你有安睡的日子,在你眼前时常浮现着大妹的身影……她死后的多年来,已长大的外甥女来过几次,都被母亲拒绝相见。这事你很理解母亲,她的伤感是无法消失的。但是她们毕竟还是孩子,应该得到宽容了吧,没有理由再次加深孩子们的孤独与忧伤。
一九八四年农历七月上旬的一天晚上,快要熄灯的时候,你隐约听到了两个陌生人的说话声。这声音来得匆忙,这声音来得慌张而口吃。倾耳细听……说什么骂了几声小孩,她脾气那么大,喝了农药而死的。不可能!不可能!似乎在错觉中呼喊、祈祷着,你从二楼“噔噔”地跑到了店堂外,那两个陌生人已踩上自行车匆匆地离去。
这是晴天霹雳!父母这时已经没有了主意,发傻似的自语着,只能依着你同房族的亲人的主意,速去探清大妹的死因。村庄里只有几盏鬼火似的灯光,就在瞬间灯光多了起来,乡亲们骚动地到了你所住的小桥边。只有此时,各位乡亲才真诚地惋惜着,宽慰着,为了你家叹息着不幸!而你也懵傻了头脑,在匆忙之中敲开几家乡亲与朋友的门,大约召集了十几人坐满了颠荡不稳的小船,从小河往前村方向驶去。机器在木制小船内裸露着震颤的力量,船在呼啸的逆风中冲刺着,冲开了阴沉静寂的夜色,也冲散了夜幕狰狞舞动的鬼影。欲隐欲现的月光随着乌云在走动,两岸河沿那青绿的晚季稻苗,随着秋风沙沙的声音似鬼在赶路。坐在船头的你,傻了似的麻木,傻了似的黯然,沉重的心坎里还怀着大妹活着的希冀!心在寒意中颤抖着!为什么多灾多难的日子层出不穷地降临到你家?纠缠着你的灵魂不放呢!大妹她因何走得这样仓促?因何过早地毁了自己?她就不留恋那五个可怜巴巴的孩子吗?她活够了吗?或许她害怕着生活的累赘,是为了逃避孩子们幼小淘气的纠缠吗?但她又为什么不在最困苦时离去呢?
就在七天前,你从县城骑着自行车返回途经她家时,她还是好端端的,对生活满怀着期盼。对孩子们的怜爱,粮食够吃,在家里有私工可做,她乐观地说到承包后的结果,总之是农户们从没有过的舒心日子。你与大妹的对话没一会儿工夫,不知从哪个旮旯涌出了五个可怜巴巴的小孩,瞧见陌生的大舅到来都活泼地蹦跳起来,在亲昵的喊叫着。那一双双稚嫩“狡黠”的眼睛里似乎在搜寻着舅舅身上的什么,或许能找到些可吃的东西。你这个很少来过的大舅,只是让小外甥们失望地站那儿瞧着,而你手空兜平,被孩子们瞧得慌了神,懵傻的脸无光彩,后悔带些果品进来该有多好。一年多没来看望这帮精灵似的小外甥们,但是你赶紧地从裤腰小兜里掏出所剩的五元钱,叫大妹去买点糖果来给孩子们解馋。她是那样稀罕地看着钱,只是那五元钱,她总是推来推去地不愿收下。你欲要动身回家干活,她坚决地要留你吃完点心再走,那五个孩子的眼睛傻盯住不放,不让你轻易离去。或许那时她家里还是穷得叮当响,没一点东西可做点心。而她很快地到小店摊上买回了一瓶龙眼水果罐头,未等她撬开瓶盖时,大的女孩早已被她撵出了屋外。像馋猫的男孩发愣地站在那儿瞧着,巴望地追逐着瓶盖的旋动。瓶内荡漾着的龙眼,令小孩们馋得直咽口水。她催着你,快点吃这瓶已斟在碗里的鲜龙眼。那碗里的龙眼个个像小孩的眼睛那样盯着你,真不好意思吞咽这被孩子们盯梢的点心。只喝了两三勺的汤水,你就撂下了勺子,端去给了两个男孩分吃着,那两个孩子毫不客气、拼命般地慌抢着。不一会儿的工夫,就连沾在碗上的糖水,也用舌头不放过地舔个精光。坐在那看得入神的你,在心扉中激起了从没有过的蠕动波纹。使你怜悯!使你动情!使你深深地陷入了沉思中——忆想儿时的寒酸、苦涩的生活,不就是这些馋相的小孩吗?你惭愧地别离了大妹家。就在七天后她怎么会突然地想到死呢?这是你意料不到的事。那天鬼使神差地经过,竟是兄妹间最后的一面!最后的永别!大妹,她,自杀?他杀?是一个让你恨之入骨的谜团。在机器的震颤声中,你的脑海一直萦绕着大妹生前那些阴暗的日子。她生前像在天空中寻找归宿的鸟儿,坠落的噩耗终于来临了。
大妹婚姻的不幸就是那无辜该死的家庭阶级成分所造成,也深深地折磨着她的灵魂。她一投胎就是那个复杂的被阶级烙印着的黑类分子的家庭,她一出生就是那个饥荒要命的五八年。她没有了春暖花开的童年,没有了少女恋爱的权利。在那个年月里,她就像一盆被泼出去的水,嫁出的女儿就似甩掉包袱的累赘。这就是农村里传统的观念与意识,这就是黑类阶级的心里话。待到她结婚后,大妹的命运也是挨苦的命。生了三胎都是女孩,像她在男方贫农加贫困户的家庭里,计划生育措施总是落实不了,接着生了第四胎,又是一个瘸子的男孩。而她想想不顺心,东躲西藏地又过了一年,第五胎才是一个机体健全的男孩。农村风俗的意识与偏见,要的就是传宗接代的男孩,而她偏偏肚腹不争气,几胎生的都是女孩。生男生女是谁前世作的孽,是谁今世罪过重重,专家也无法考证、鉴定的因果,何况我们这些粗俗的农夫呢。尤其在六七十年代里,生男生女在农村往往使婆媳间掀起了不可调和的矛盾,这或许是忧虑着绝代的可怕,甚至有的成了一种口头缺德的谩骂工具。因此她嫁到男方生育了三个女孩的错误,出身地主家庭,还有那微薄的嫁妆,未能达到婆婆的要求与愿望。即使婆婆时常阴着脸色,骂她的肚子不带福,骂她娘家是个吝啬的穷光蛋,骂她是地主的女儿才嫁给她儿子。有时婆婆变本加厉地骂,狠毒泼辣地骂。不像她第一次登门代儿子相亲的时候,彬彬有礼地同你吃着午饭,斯斯文文地说了一大堆客气的话语。
她婆婆又同二儿子的媳妇结伴着,欺侮她的软弱,欺侮她娘家懦弱无能是地主家庭,而她老老实实地只是忍耐不作反抗。比如大妹回娘家也是走走过程而已,首先到女友那里待几天,后又回到了娘家,反正娘家从来没人为她撑腰,或警告那男人。过几天受欺侮忍辱消停之后,她照样想着家里的小孩,照样想着窝在男方的家里。她是封建观念中嫁鸡随鸡传统的农村妇女,是一个善良的贤妻良母。她!她!三十一岁的她!人世间给予她的是何等的不公平,何等的短促生命,何等的刻薄与炎凉!什么青春,男女的恋爱,愉快的日子,对她来说谈何容易,她只有生养着孩子的权利,给丈夫使用的一块园地。她的期盼,她的等待,生活中的美好不属于她的世界。
小船停靠在前村河堤后,你同着堂叔与几位朋友先后登上了岸,向大妹的住宅走去。早已在那里守候的外公与两位舅舅,正在翻看着躺在板门上的尸体,大妹她似乎安然地睡去了很久。微紫色的脸部毫无痛苦抽搐的现象,只有那双半掩的眼睛似乎等待着亲人的到来。母亲看到了大妹倒在板门上的惨状,倏地晕厥了过去。三妹同四妹扑在尸体上狂哭着,旁边的你在做些什么呢?你真想狠狠地用拳头惩罚那个没有保护住妻子生命的男人。而你动手了吗?自从大妹死后的几天里,你在遗憾,你在愧疚,你在窝囊中……还要忍受着阶级区别的意识吗!你后悔不听二舅的话——要把大妹的尸体解剖示众,不能让她蒙冤受屈死不瞑目。你这个软弱无能的兄长,在停尸三天的时间里,未曾动她男人的一根毫毛,又没有去叫法医来解剖验尸。你作为兄长,你对得住死去的大妹吗!这是为什么?这是为了什么!或许你只想到那五个可怜巴巴的孩子。如果验身证明是男人失手打死的,假装用农药服毒喝死的话,他肯定要负法律的责任。而你只好作罢,免得在光天化日之下打开大妹清白的尸体。或许那菩萨心肠又在作怪,饶恕了这个恶魔似的男人,难得又做了件善事,神灵又在记录着你的因果与你的涵养、气量。我们的亲族要男方拿出大妹服毒的证据来,那恶人妹夫从床底下找出布满了尘埃的农药“敌敌畏”空瓶,在狡辩、伪装着。只有五舅忍无可忍勇敢地甩了那男人几巴掌,大妹尸体被亲人们抬回到屋内的床上。
屋外的月牙还高悬在天空上,今夜这颗渺茫陨落的星星对人们来说是毫无瓜葛的,毫无伤害的。我们亲属的到来,我们的离开,毫无惊扰着周围人的沉睡。夜,万籁俱寂的夜,星光闪烁的夜,乌云遮月的夜,在夜幕降临、灯火熄灭的时候,把自然界尘世间的万物收了回去。夜色中的宁静,夜色中的朦胧与诱惑是生命死亡的一种魔力。或许夜色远离人世间的苦涩与烦恼,只有沉睡在夜色里,才是属于阶级平等的世界……
深夜返回的途中,月亮早已躲进了炭灰色的云层里,使整个黑暗、沉寂的夜,埋伏着狰狞可怕的鬼影。船舷两边十几人的面孔越来越模糊起来,沉重压得小船离水面只有一尺多高的距离,小船随着丝丝的水波在颤抖急行着,似乎因承载沉重如铅而停顿。大地张开了黑魆魆的大嘴,吞噬着那多灾多难的生命……大妹的灵魂随之而去。
第二天早上,你同几位朋友到镇政府报案。寻到了正在写着材料的公安员,进了他的办公室,他身子也没有摆动一下,只是无精打采地叫你们先等着。以为他抄写材料是有时间的,很快就能完成,你们只好耐心发傻似的等待着。哪知道他抄写了大约半小时后,撂下笔去了某个办公室,回来后也不询问什么事,又继续地抄写了将近半个小时……你们等待得实在有些不耐烦,情绪似乎在燃烧在冒烟地嘀咕着。拿着国家月薪的人民公安员,他装模作样磨蹭些什么呢,他就不能先撂下笔了解一下死者的家属,以打发你们沉痛、焦虑的等待吗!或尽快地派人去村里调查一下死因,究竟他杀或自杀。而他是那样无谓的拖延,无谓的回避态度。他根本不理会亲人的心情是如何得悲痛,在如何紧迫发疯似的抑制着。假如你们的亲属们蛮不讲理,想着大妹活活被打死的惨痛,名正言顺地去捣毁男方的家具与房屋,不是没有道理的。农村人本来多数是法盲,人死大于法,又不是在男方家里病死的,可以什么也不怕,可用蛮横对峙着仇恶。这个维护社会治安的公安员不及时来,有何理由,有何结论在拖延着。难道他就没有家人罹难掉泪的时候吗?原来他昨天就知道此案的发生,然而恶人先告状:死者是服毒,是自杀,不是男方吵架动手或失手打死的。他是一个乡镇的公安员,又是驻在前村的干部,有权力包庇、听信单方的片面之词。或许存在偏袒着阶级优越的意识,因为男方是贫农的儿子,有理由让你们几个人在办公室里坐等了将近一个小时后,岂有此理地没说几句话,要你们先离开!
因为昨天深夜里,男方重又把大妹尸体搬到堂屋板门上,其中个别的帮凶骚动而嚣张,总以为死亡的一方是可以欺侮的阶级对象。往往是某些人歪曲的意识可怜活着的人,模糊地颠倒黑白,要把悲痛化于活着的躯壳里。当天下午,亲属们又把大妹的尸体抬进了房间里,此时才有人请来了派出所的那位公安员,他是来威慑着各位要妥协不能闹事的。这一家人的守法!这一家人的懦弱与窝囊!何苦还要劳驾他们这些战士打击违法分子呢?或许他们是来看热闹的吧!但是在你的这些亲戚的头脑里,还是烙刻般深陷于六七十年代那种阶级斗争的胆怯里。那种绝无仅有、被驯服不做反抗,对那些被划分在阶级圈里的人们,起了一定的副作用与效果。那位让你们坐等了一个多小时的公安员,甚至还对着你们亲戚说了一些令人心寒的话语,他们是贫下中农的子女,你们要谅解他,同情他。还含着揶揄讽刺的意味,他又面对着男方的人说,你们斗不过他们的理论,他们是知识分子。这是在讽刺、痛戳局限在阶级圈里的人们的创伤。那位能干、敏感的表舅舅,当场就同这位公安员辩驳起来:“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你的意图指的是什么?”而他无话可答,看到你们亲属仇视的眼光,就偷偷地溜走了。
知识分子是臭老九,地富反外右,牛鬼蛇神,如果这些名词放在阶级斗争为纲的日子里,就可以直截了当地指出来:你们这些黑类阶级的坏分子,你们要老实点,不能在贫下中农的家庭里捣乱哭闹。大妹不是贫下中农的家属,是地主的女儿就轻于鸿毛。如果大妹真是被打死的话,等于在贫下中农的家庭里荣幸地沾光了。在那个黑白颠倒的岁月里,都一律论家庭出身贬低着黑类的生命。阶级斗争的理论死死地控制着民众的脑子,根深蒂固地在农村里运用着。
大妹的介绍人——媒婆是你的乡邻,原来也是邻村改嫁过来的二茬媳妇,与大妹的婆婆是老相识。因她每天天花乱坠地来说媒,说男方的家庭历史三代都是清白的,不是一个瑕疵的贫农,男方的父亲搞渔业失落在海里,就剩下了孤儿寡妇的。像这样的家庭成分,今后你们与他家连上亲戚的关系,女儿和你们家少受些阶级成分的委屈与凌辱。男青年是个赶海潮逮鱼的能手,但是他不计较地主家庭出身的女儿。这些理由把父母说得心满意足,难得人家对我们地主家庭有好感呢。不像本村有几个贫农的儿子,看上妹妹长大的模样,但是瞧不起出身在地主家庭的子女。父母本想寻找一个黑类分子比较门当户对,免受红类的虐待或歧视。因为你是长子,坚决反对父母落后的思想——与贫下中农攀亲沾故是我们的荣幸,是我们前生修来的福分。何况这门亲事的男方又是个孤儿寡妇的特殊户,待到他们俩结婚后,谁还敢欺凌地指着大妹是地主的女儿。这就是做女人比男人的优越,这就是做女人的造化,这就是五百年前定下的姻缘。这样的想法极其可笑,愚蠢之至!但在当时却是很多黑类分子家庭的普遍思想。
这介绍人又跟对方说我们的祖上在全县是有名的大好人,父母都是有文化的人,地主家庭遗留下一些古董的家私,到了媳妇娶进门的时候肯定随带些嫁妆回来。介绍人总在两方面传好话,就这样草率地订了这门婚姻,大妹她根本不认识男方是何种模样。母亲只劳驾外公同父亲跑一趟男方相亲。外公也是一个破落的地主成分,又是一个酒仙样的老好人。他们俩急忙地只是瞧一眼就回到家里,说看到的侧面这青年人个头不矮,家里两兄弟劳动力也不赖,确实是一个正宗的贫农成分,阶级历史清白。父亲也同样地说着。就这样匆匆地,好像害怕被别人抢去未来的姑爷似的,又怕嫁不出去女儿而焦虑,收了一些彩礼,草草地给大妹定了终身。因为又在饥荒的年月,粮食紧张,减少一人,能温饱了家庭,也能减轻了人口众多的困境。那边又急催着要讨媳妇,大妹还不到十八岁的那年结的婚。但是你已经离开了家乡,到了闽西山区里谋生。你在过年回家的时候多次听到大妹与家里人忧虑地诉说,婆婆情绪反常似只母老虎,经常凌辱她是地主的女儿,娘家是个苛刻的穷光蛋。你经常对母亲说,该给的东西都给大妹吧,免得大妹被对方瞧不起。母亲总是固执己见,女儿出嫁似泼出去的水,有东西也要给儿子留着。而你一直看不惯并怨恨着母亲,认为大妹的死与她有关,不孝的你经常使母亲生气得脸红发抖。很多的时候,你看到大妹的眼睛……似乎掉进深渊里在寻找着求救的绳子。长年在外地做工的你,心有余而力不足。曾经多少次大妹回娘家,在你的面前徘徊彷徨着。或许她已经站在井沿上,或许她已经站在火坑的边缘!那双从困疾中所伸出的双手,那双巴望乞求的眼神在你面前停留着。待到她死后……你才寻觅着那双溜走了的眼睛,空留遗憾而惭愧。
男方知道我们不采取解剖验证尸体,看出了我们的忍受与懦弱,甚至出尔反尔,取消了一些给大妹应该做到的入殓事序。你终于在忍辱中愤怒地反抗着,坚决不能答应提前入殓出丧。亲属们要再次地把大妹尸体抬回到房间里。农历七月上旬的南方,中午的阳光仍然炎热地炙烤着,尸体旁边摆放了多少的冰块都无济于事。你抬着大妹的头部,有种难闻的腐气冲鼻而来,突然间反胃呕吐的紧急,你努力地抑制食物不从胃里冲吐出来。这就是要挟着对方,这就是我们做出的懦弱的示威。男方不得不同意我们原来说定的口头协议。
大妹死去停丧的几天里,她婆婆一直不露脸,假装身体不舒服躺在床上,或者她婆婆心里惭愧地躲避在别处。亲属们坚决要她婆婆出来对质,要她说清大妹的死因,如果不出来,我们就要停尸不发丧。后来她婆婆不得不出来——在大队部楼上跪倒在我们的面前,或许是求情,或许是忏悔。那位在场的婆婆的表弟好不愉快,似乎要丢掉恶人的面子,气愤地拂袖而去。总之,有某种恶的势力在他心里萌生潜伏着,恶的情绪在他心中顽固不化地回击与报复。这个恶魔在序幕刚拉开的第一天里,你就看清了他狡猾凶悍的眼睛……在整个场合里溜来溜去,一直在注意着我们不动武、只摆道理的软弱。他心不在焉地在大队部楼上,一会儿下去,一会儿又上来,好像只有他一人在操作谋划着邪恶的等待与反扑。她婆婆的表弟为什么那种丧心病狂地卖力,又是那种蛮横无理地寻找着空子,歧视欺侮着我们的亲属。发丧入殓那天,三妹同四妹拍打着棺木撕心裂肺狂哭的时候,在中间阻拦作梗的是他,动手打骂四妹的是他。开头你提出对大妹死因的质疑,要采取解剖验尸之事,又是他在大庭广众面前反驳了你,又反过来狗急跳墙,威胁我们,甚至还想扑过来与三弟动手斗殴。由于我们的忍受,没把大妹解剖验尸,尸体已经入殓在棺木之中,又给了他一次为虎作伥、气焰嚣张的机会。这种没有理性、对死难方苛刻的欺辱,在他的眼里所透露出的残酷与邪恶,早已在你的视线中,更在你心中点燃起悲愤的火焰。你那简单冲动的头脑在思想着,总有一天要扭断他的腿,或挖出他的眼睛,惩罚他,报复他,来祭供大妹的灵魂。回家后每天在等待着那恶人的经过,是否出现在你屋前小河上来回驶过的小船里,只要有他的影子,使你刻骨铭心地定格着仇恨。
或许大妹在地府里诉说冤情吧,而她不能!她活着的时候,都未曾说过丈夫的短处,何况已经到了地府呢。后来乡邻透露了口风,说男人经常与大妹吵架,殴打她,甚至有一次把大妹打翻在地,拖过了几条门槛才肯罢休。又传说男人有第三者插足,怪不得大妹有时回娘家不想着回去,要到已出嫁的女友那里寄宿。你听到了这些风声后发疯似的愤怒着,觉得对不住大妹,使她委屈忍辱地死去,真不该饶恕狡猾的狐狸。从前每当节日到来,他同你在一起共餐的时候,伪装得那么斯文而亲切,却是披着人皮的兽类。
你后悔不该因恶人跪地求情就软下心来。你真想挖开大妹的棺木,看她到底是怎么死的。而你惭愧地无地自容,对不住善良的大妹。
大妹啊!都怪无能的兄长吧!她已进入泥土里,哥仍在滴着沉痛愤恨的泪水……
1993年10月于北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