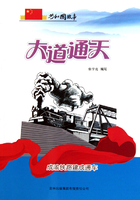客居的地方离铁路轨道不远,每当听到“哐哐”的列车声,仍会颤动那已远去的记忆,你仍想起站立在拥挤的车厢里,在路途中身无分文,没买车票的尴尬场面。在阴暗的空间里,厕所里,躲避着乘务员的查票,或者钻进了座位底下装睡而忍受着被人踢醒的恐慌。
列车到达了终点站,已经是深夜里。肩上背着沉重的工具包,在无人的站前彷徨着,掏着兜里所剩的几块钱,根本住不了旅社。已是穷途末路之际,只能走进静悄悄的候车室,里面空旷得使人直打寒战,你拿出母亲硬塞在提包的棉毯子,缠绕着身体,躺在木栅做的长椅上,不一会儿的工夫就进入了梦乡。
起来!起来!迷糊中被一帮凶巴巴的人推叫而醒,你从提包里拿出大队所开的证明,被查看了之后,仍被强制地跟着他们走出了候车室。外面已停着一辆车,要你爬上露天的拖斗里,迎着呼啸的冷风疾驰而去。大约一小时左右到了市郊,车开进了一个大场院内,你下了车被带到一所平房前,拉开门推着你进去。带队的头儿说,这里是你的住处,明天有活等你去做。你欣喜地以为来到这里,那么容易找到事做。你以为这么快天上就掉下了馅饼,及时地让你充饥,心里就这样胡思乱想着。就在进来时,全屋炕床上****的男人,“刷”地看着新来的是一个年轻白嫩的小南蛮。大约有十几双的眼睛在贼瞪着,身体几乎是光溜溜的,没有人穿背心裤衩。此时你感到如同女人似的羞辱与恐慌。有的手里拿着裤衩在寻找虱子,有的不知害羞地翻弄着阴部,只有几个歪斜着身体打起了呼噜。整个屋里不文明的形象,让初来乍到的你傻了眼,撞着野人似的惊慌失措想要逃脱。
这里是什么地方,这里男人们为什么无所顾忌地****着?这不是在电影里所看到的关押罪犯的情景吗?你心里在委屈地疑惑着,大声地吼叫着要抗议。我不是罪犯!为什么要同他们关在一起呢?其中一个脸上有刀痕的年轻人,凶巴巴地过来用脚狠踢着你,要大打出手,威胁着说再要吼叫的话,整死你这个小南蛮,要你老老实实在地上蹲着。此时你似虎落平阳被犬欺,像绵羊进入了狼窝,门上了锁,又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如果不忍着点,对方动手揍你一顿又怎样。炕床边的****人,看新进来的是一个弱者,肆无忌惮地张开四肢占领了破烂不堪的凉席,一点位置也不让给你。你此时只能忍气吞声地挨靠着炕床的边沿,不在乎旁边放着便桶的尿臭,不在乎坐臀底下肮脏的沙泥,守着包里的工具,煎熬着度过下半夜。后来才知道此处的男人大胆而豪放,而且炕床被木柴烧烤焦热得滚烫,才没有盖被子。
翌晨,哨子响起。昨晚上那个刀疤脸,带头踢醒在沉睡的人,对新来的你,两眼射出仇视般的咒骂,指着你要服从他的命令。今天院内的广场由你清扫干净,开饭后随着大家上工地劳动。你无奈地拿着大扫帚,扫完了整个的广场,才走进了食堂里。早餐是发硬的窝窝头,大锅里的冬瓜汤只剩下了汤水,被这帮人早已疯抢没了。拿起冰凉坚硬的窝窝头啃嚼着,你不觉得委屈,不觉得可怜,不觉得忧虑,只有一个念头,惜命,勇敢地活着。吃好早餐后,匆匆忙忙地排着队到了工地,工地上一片狼藉,各处堆放着红砖、水泥与沙子,同这帮贼似的人分工干活。有搅拌水泥砂浆的,有砌砖墙的,而你自告奋勇地要做门框。管理人员看着你会做木匠活,几天下来勤恳而卖力,就放松了对你的看管。头儿口头答应工地完工后,放你出去找活做。
在一天下午收工后,你心情焦急地去问所长,为什么要做义务工,没有工资要干多长时间。那位所长看了介绍信之后,还阴着脸色揶揄地说:“你的阶级成分是工商业,要向贫下中农学习劳动嘛,暂时不能放你出去,要看你的劳动表现。”还好为了外出做工,你特意请求大队会计在介绍信上抹掉父亲的阶级成分,出身填写了工商业。如果照实填写家庭是地主的成分,那就糟糕了。那时正是阶级斗争紧张严肃的时候,一定像反动派似的要受到地方管制与惩罚。在当时不少人盲目被扣上成分的帽子,劫数难逃的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个。
而你走出了所长的办公室,又去找收容你进来的头儿,请求他给你安排一个床铺。因为不是罪人,为什么要被关押在二十人一间的屋子里,乌七八糟地同他们睡在一起,几天里都是坐靠在地上睡觉。这位头儿听着你可怜的诉说,生出些怜悯之心,就向领导请求,才腾挪出一房间让你住。时间一天天地过去,任凭怎样向他们诉说家里的贫困,外出是为了挣钱还债,头儿还是不肯放你出来。
夜不能眠,而且看到了窗外的马路,使你有了冒险出逃的决心。第二天向头儿请示,要出去购买一块洗衣皂,借此机会摸清了到火车站的路线,为了深夜里出逃的方便。
这一夜,等啊等!下半夜,一点、两点……三点四十五分有北去的列车经过,无论怎样也不能睡过去。今夜无月亮,无星光,而你野猫似的窥探着窗外在等待。马路上又无行人在走动,假如有一个酒徒在静夜里走动的话,也坏了你出逃的计划。此时此刻紧张地推开窗,你扔出沉甸甸的工具包,蹬上了窗户跳到黑暗的马路上,慌忙地怕被人看见。你完全没有像在家乡的小路上静夜里出行的胆怯,当时完全忘记了自我的存在。你急急忙忙地拐进了通往车站的轨道,鸣声响起,你混进了暗黑的乘车队伍里,列车启动的时候才松了一口气。
在拥挤的车厢里,列车长同乘务员走近你的时候,你拿不出车票紧张尴尬地面对,只能诉说在途中钱已用完,又拿出那张已折叠皱裂的外出做工的大队证明。列车长看了之后,质问道:“到这么遥远的地方来做工?”似乎在赞许着你年轻人的胆量。他只是善意的一笑,不问补票的事情而放过你,你心里侥幸地在感激着。也许是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吧。几十年之后,而你总是念念不忘地回忆着过去——贫穷年代真挚的人们。
2002年5月于包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