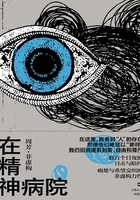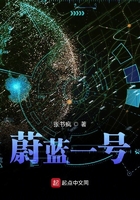不知出于何种理由,出于何种心理,或许你只是心血来潮故地重游,去寻找去追溯那已遥远与渺茫的爱。从厦门乘上三二二次至光泽的直快列车,你在列车上又自然而然地想那些不该想的尘封心迹。
十六年前,因为那复杂的阶级成分,再加上家庭的贫困,社会所给予的是受奚落,是受侮辱,是受阶级划分孤单与苦涩的生活。因此你只能用唯心的信念,去谋生,去拼搏,背离了父母,盲目地冲出了这个令人心寒而又复杂的家庭。来到了一个极偏远的山区里,你谋求着新的生活与新的开始。
记得那年出远门做学徒时你不到十八岁,是通过做油漆工的四舅的介绍,卖掉了自家里养的几个白鸭子,又到叔辈的乡邻那里借了二十元钱。那位乡邻疑虑地看了你几眼说,借你可以,但要写凭据欠条。那时很感激有人借给钱,但是要你写借条有些难为情。你拿着二十元钱做路费,收拾了行装,提着细纹银灰的背包。父亲送你出了门,一路上嘱咐着要你听师傅的话,早点学会技术,可以自己做师傅,到了车站父亲才离去。你换乘了几次车才到了目的地,下车后还在丛林的小路上穿梭地步行了一小时,傍晚天暗的时候才到了地方。
这里一切都是亲切的,友好的,平等的,没有歧视,尊重着每个人的人格。特别是年轻人的戏谑声与打闹声,飘洒在田野上、在山坞里、在溪流中,那是发自内心的纯真的笑声。这正是我们师徒俩藏身匿迹的避风港,这样也隐瞒了那不光彩的家庭成分,不再过着牛鬼蛇神的日子。
这里居住着几十户的苗族人家,有一户是根正苗红的阶级成分,你与师傅商量,只能暂住在这户人家里。如果住到别处,大队的民兵不时要来查夜。有几次师徒俩躲在阴暗的角楼上,在深夜里被吵醒像老鼠似的颤抖着。回想起那年月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其实不在于赶走外流的人员,而是那深夜里的迷惑、好奇驱使着人们。谁家里同床睡的是否有别人的老公,谁家有与外来的手艺人不规矩偷鸡摸狗的习性等。因此民兵们时常夜里出勤,俚语说是“打野猪”,各家各户地查夜。查到在床上不是真夫妻的故事,在当时也是茶前饭后的温饱男女之间****的一种释放。
我们所住这户的男主人长期驻在外地工作,女主人又是小队的干部。家里有个念完高中的姑娘,因她根正苗红的条件,经人民公社与大队的推选,轻而易举地当上了赤脚医生。有一次在她家里做木匠活,你用脚踩着木料切解的时候,不小心被锯子拉到脚踝的大块肌肉而血流不止,被送进了医院缝了十来针,后来休息几个星期都待在她家里。她对你这次的养伤,包扎换药等都是无微不至、熟门熟路地关照着。她并不婀娜多姿、亭亭玉立,但她有着温柔纯洁的性格,稳重沉着气质的外表,她的魅力令人羡慕,充满着诱惑,有着当时女性中少有的一种知识与涵养。脚伤痊愈后,你眷恋地离开了她家,到了二十多公里的地方做活,她曾多次悄悄地送来从山上摘回的草莓,又那么地匆忙,在无声的微笑中害羞地离你而去。在她离去那刻,你只是自作多情地幻想着,这就是初恋的春天吗?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爱情吗?而你不懂,只是干活与夜间做着美梦。院长的媳妇那是个慈善的妖婆,那天早晨在医院的过道上大声对你喊着:“小黎你昨夜有没有看到大头鬼?他死在这房间里不到一个月,住院病号知道的都不敢住进去,是我那个老头让你住进去的,因此住了几天我才问你。”大咧咧的妖婆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在活儿没有完工的几个深夜里,你就没有了美梦,只有那没完没了梦中的恶鬼与棺材。或许大咧咧的妖婆在督促着干活,要你快点离开所住的房间。
在她家里干活的时候,你经常看到她那难言而忧虑的脸色——同阿妈在撒娇着。她没有兄弟,父母给她招进的未来丈夫是一个老实憨厚不吭声的表哥。她一直以反对的情绪别扭着,由于她的孝顺还是尊重了父母的安排。年轻的你出于道德观念,做人总是守规矩地相处着,在爱慕的天平上没有超越过爱河,不能去入侵少女那纯洁软弱的领地。而且在几次处于起伏的波浪里,激流中,欲要冲你而来的浪花都被你阻挡了回去。一次次地,异性在身边冲刺;一次次地,激情在身边挑逗着。少女就像刚开在春风里的花朵,让你吻吻它的柔情,它的芬芳,而你只能远远地躲避着,退缩着。你没有这份勇气与力量,同浪花做一次孤注一掷的较量与决斗!最后浪花失望了,伤感了,风平浪静地隐去了激情。你似乎遗憾地还留恋着浪花,还异想天开地想着再次冲你而来的身影。
夜晚十点到光泽站,你下车后似放飞的鸟儿,毫无目标方向,混混沌沌地寻找着住宿的地方。空荡邋遢的车站前,迈起步来尽是稀糊的尘土,干燥的像冒烟,似隐似现的篾黄火光在小吃摊位上晃荡着,水果小贩那低哑的叫卖着苹果雪梨的声音不时传来。你缓慢地走了十几米远住进了旅社。
翌晨,你乘坐六点的班车,向丛山深处进发着,这条熟悉而陌生的逶迤公路,让你倾斜颠簸旋涡样的颤荡。假如是在十几年前,非得晕车呕吐不可。而在今天拥挤无座的客车里,不知何种缘故你如同小孩似的精神着,你紧拉座位的靠背站立着,窥视着窗外波折层层的山脉,充满原始奥秘的杂林。也许今天你的情绪在舒畅,在扩展,在寻思期待多年的梦幻与意愿的到来。凉爽的秋风从几个破了相的车窗涌入,夹杂着被刮起的尘嚣在整个车厢内扩散着。
十六年了,这块土地,这条砾石飞滚的公路,这条静谧清澈的溪坑,你认为还是原始而古老,这里未能随着改革开放后的春风,搞活经济的洪流而有所改善。有所创新。山,四面尽是山,水,这条清澈透明的溪河从汽车底下滑了过去。汽车在颠簸旋涡地运驶着,难得窥视到丛林的深处,只有那毫不起眼的梯田在山间战栗地瑟缩着。还未进入深秋,在青黄分明的稻田里,已有几个驼着背的农夫,在梯田里正收割着晚季的稻谷,像江南人收割麦子的那种姿势,原始而古老。你瞬间沉思起来,这些农民长年累月地停留在这块责任田里,磨蹭而又散漫,他们没有怨言,他们没有外来的竞争对象。他们只是在无声息的劳动中,只等待着金黄色的收获,嫩绿色的播种。他们是单调而又复杂地劳作着!在这块薄弱而又贫乏的梯田深处,在这块被遗忘的贫瘠土壤里,延续着简单而狭窄的生命。
晌午十一点就下了车,不知为什么,街道上的行人人头攒动。或许这里就是改革开放的市场,或许这是山里人赶集的地方。这里的姑娘小伙们,还是从前那种朴实的善良。有大人领着几个苗家的姑娘,好奇的眼神滴溜溜在瞧着这个不知从何方而来的客人。你那时的装束在家乡是落后的,来到了这块净地,竟觉得高人一筹,似乎腰杆硬朗起来,沾沾自喜地欣慰着,看这些比你低调落后的人们。走进了商店购买些礼品的时候,营业员还是那种顽固不化,服务不到位,零散地把东西递给了你。要求买一条盛东西的袋子,她只是摇头拒绝。你指了指那些扔在旮旯里的纸箱盒,她又是那种莫名的摇头。营业员这些道理都不懂,就是这种素质与修养,此时连你都哭笑不得地摇头,在很大的供销社买东西却没有包装袋。假如是在经济开放的地方,那不是笑话才怪呢。或许山里人买东西都用篾篓背着吧。当你正要转身离去,从橱台外进来了一位三十多岁的男营业员,态度和蔼地对你点着头。你说明了来意,以为他要照顾你把袋子或纸盒卖给你,但是他热情地把一张张报纸铺开在台面上,想用编织绳打捆着礼品。想着节日快要到了,就买很多的月饼,很多的糖果,再加上两瓶竹叶青,如果没有袋子是拿不了的。旁边站着个游荡的闲汉说,外面市场里袋子多的是。营业员又不怕麻烦地停下手里没有包好的礼品,亲自跑到摆地摊的市场,半天的工夫才拿回一条塑料袋子。你这时候十分感激这位服务周到的男营业员。也许从他帅气机灵的眼神里,已留意到远方来客走亲的意图。从那以后在你心目中一直在记着,但再也没有出现第二位像他那么耐心服务的了。
你手拎着礼物穿过大马路,经野草丛生坎坷的石头小路,直往她家方向走去。这个远离尘嚣的净地,这个孤僻的山沟沟,这条通向远方的溪流,这条颤悠在溪河上的独木桥。你至今想着那次在溪流里的旋涡,差点被激流吞没而侥幸地逃脱,是它变得有情给予了你二次的生命。或许陌生,或许熟悉,你是这样好奇、稀罕地瞧着想着。为什么!为什么!像一个情种,千里迢迢地跑到这个僻陋、落后、寒酸的地方来。或许在你的心里有个难以启齿的秘密,或许你绝不是为了秘密,只是特意来感恩的。这里的民风习俗让人们总是那样和谐善良地相处着,特别是那勤劳勇敢的劳动妇女。听说从前这里的女人刚生了小孩就出勤劳动,男人们就待在家里坐月子,怪不得一些女人的脚板宽得像野人。这就是伟大的母亲在劳动中大脚丫皱脸纹的形象。
不知不觉地到了她家院外的台阶上,房屋外很冷清,只有她阿爸牵拉着牛停在庭院里。他看见进来的陌生人,就问:“你是在找谁啊?”“叔叔是我……”你语无伦次地介绍着自己。他才想起那个木匠师傅——小黎。十六年前驻在别处当上了公社书记的他气愤地寄信来,固执己见地拒绝了二姑娘嫁到外地的婚事。这是她阿妈亲口传话也是最后的通牒,要求你别再思想,断了念头,你就这样地被拒绝了。你此时在心里谩骂着,这该死的顽固不化的倔老头。他如今悠闲自在地放着牛,这次你出现在他家里,他是格外地热情,而且你有些承受不了这意外亲切的待遇。觉得屋内缺了些什么,忽然间从后间蹒跚地踱出了那时放牛的老奶奶,老人的出现让你好像似在错觉中——已经百来岁的老人了,模样不变,而且硬朗,神采奕奕地来到了你身边,踌躇地站着。因听不清老人在嘟哝着说了些什么,你只好高兴地同她微笑着。
与她阿爸——这放牛的人,唠嗑了离别后的经历,你又心不在焉地坐不住站起来踱步,看着前后园的面目,寻找着园里原有的足迹印象。然而令你遗憾失望。从前那棵艳色密布的桃树已经被抛弃隔在了围墙之外,只可看到上半腰那嫩绿色的叶子被微风吹拂着。每到阳春三月雾雨连绵时,这桃树的花瓣悄悄地坠落随风飘舞着,在湿润的泥泞里布满了粉红色的世界。使人怜惜,使人失意,使人寂寒,而你在思索中巴望着桃花的永恒,桃花的情愫别只在春风里。前后园所摆设的那些花草,已不如从前那样的艳姿,有的已枯萎死在花盆内,有的或许缺少水分,叶子和花朵耷拉着无生气。
待到她阿妈看病回来后,阿妈忙得来回地小跑着,像招待天上掉下的一个客人,一边沏茶又一边拿出南瓜子摆在凳子上,那番的热情,你无须多说。到了晚上总觉得还缺些什么,掉了些什么,但又不能说出来,忐忑不安地在屋外徘徊着……你痴情地去寻找那些不该寻回的点滴之爱,或许是美好温馨的,但是瞬间爱就变成了累赘,障碍,黯然而冷漠的,成为了生活中的虚影。天空中又是离十五差两天的月亮,看上去比从前的丑陋而偏长,就连飘飞的云朵都模糊似破絮,那么的暗淡而难看。你身不由己地来到了屋的背后,月亮是否从炭黑色的云层里出来,星光是否在清晰的云彩间闪烁着,而且有种不祥的云翳布满你的脑子。你所盼望,所期待的是什么呢?
阿妈忙完了家务活,正在房间里等待着,已沏好了茶水,果子和瓜子盛满在托盘里。阿妈要你坐下来唠嗑,而且你做作地问起了大姑娘现在何处工作,接着就问起了她。阿妈突然阴着脸色说不出话来!你再追问,阿妈才肯说起她死去已经多年了,是服毒而死的。她的男人原是个变相狂的伪君子。这位在家里放牛的原公社书记——她的父亲由于当时攀取阶梯的欲望,一厢情愿地巴结同类的官员,才把自己心爱的女儿当作了一件贡品而献礼。原来所要找的爱已不复存在了,已经永远地离开了人间。你内心悲愤异常,伤感无法言表……
阿妈还在抽泣着!你怕触及阿妈深处的悲痛,停下了唠嗑。阿妈说后间已经铺好了被子,你累了就早点休息。你无法入睡,在等待着灵魂出现吗?似乎有某种阴影隐隐约约地忽闪着,那发红的十五瓦灯泡的房间里,冷清得使人恐惧。或许今晚她真能出现吗?满屋幽灵似的清香,飘然地来了沉睡的灵魂,入梦半醒地对着你说话:“阿弟你真是从千里迢迢相见来了!知道痴情的你要来!”她的音容笑貌那么的真切,似乎早在这屋里等着你,你陶醉在清香的被窝里,是梦非梦地醒来。这已是午夜一点多钟,你神经过敏地起床,抽开了门闩退出了后间,傻样地走到月光明亮的屋檐下。你站在长条的石阶上,倾听着野外的声音。蛐蛐不知在哪块草丛里发出阵阵有序的细杂声,唧唧复唧唧地叫着。又清晰地听那从半爿竹槽里所淌流的水清脆的滴答滴答声,这是山里人从小溪所引进的吃用之水。
月亮在静夜中行走着,在淡灰色的云层里穿梭着,抛开了淡灰色,一时又钻进了云层中,显现了后山的那些杂树和野草。一时狰狞似野兽,一时分明得能辨清,似乎有的在睡梦中不动,只有细长蓬乱的竹子在夜风里晃拂着。
明天!明天你一定要离开这里,这里是使你圆了梦的净地。她爸妈坚决要挽留你过完节再走,而你匆忙地要走会使他们伤心的,你索性明天进山里风光一天,向她告别与祷祝。
每次出行讨厌路两边那些挂着湿漉漉的露珠的野草与荆棘,待到了下午阳光猛烈地晒射,你便顺着人们所踩踏过的山路,顺着溪流的源头缓步前行。此时几只蝴蝶时不时地在水面上戏谑,欲飞欲停地盘旋而起舞着,有时停歇在茸绿的崖壁或芦叶上,是那么不定性地穿行着。崖隙里湍淌汇入的溪水,在草丛里偷偷地哭泣着,时急奔时慢流,似涨似落地湍满,各样的野草被激流冲压着。只有这条路是她所经过的路,是她雅致收敛的笑容,沉稳与魅力的步伐,感染你对异性有了爱慕的情结。在路两旁的马兰花与蒲公英,似乎让出了空间在迎接着,一朵朵金黄、粉白的马兰花在迎笑中,不像蒲公英毛手毛脚使人躲闪。在这条野草丛生的坡路上,或许还遗留着少女的足迹与芬芳。有几只山雀在林间扑飞着,画眉在枝杈上嘹亮地唱着歌,大白天里公鸡在乱弹奏般嘶鸣。已能看到山坳里十几户的土瓦房,几个在山坦上软簟里蹦跳的小孩,还有正在翻晒着谷子的老太太。
在斜坡深处的那几株草莓树,或许是她当年采摘过的那几株。她送去的那些酸溜溜的草莓,那是姻缘的线轴,那是爱的结晶,那是悲痛的开始,那是死的结局。而你正向着草莓树的方向走去,几个天真活泼的苗家少女在那里,发愣好奇地瞧着你这个傻样的人。至此,打断了你那美好而惭愧的回忆。
就这样地祭祀,祭祀着明天生与死的告别!
1990年12于乐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