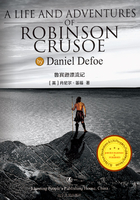人一上年纪,年轻时那种不知天高地厚的浮躁、狂傲,自然而然地就会降温,继之而来的是静静地体味身后那条路的艰辛。于是,人生的酸甜苦辣便从心头涌出。
当年我不能理解一位藏族阿妈的行为,留下了终生的遗憾。
30年来,我常常抱怨自己,可是再也无法当面请她饶恕了。
我怎么也忘不了那具兵尸,那位搬走兵尸的藏族阿妈。
那是我当兵后第一次进藏路上发生的事……
那个暮冬的午后,我有三个没有想到。一是没有想到我们的汽车会在桃儿九山上抛锚;二是没有想到会冷不丁地碰上一个战友的尸体;三是没有想到藏族阿妈会用牦牛驮走尸体。
当时,我是第一次驾驶汽车去西藏亚东执勤。藏北草原的辽阔、荒芜使我这个新兵大开眼界。从唐古拉山下的安多买马出发,车子不紧不慢地已经跑了半天,还没碰上过一个人。偶尔有一只黄羊从车窗玻璃前逃窜而过,会使人觉得仿佛到了另外一个国度。
我手把方向盘,心里总是很矛盾,希望快一点走出这令人胆颤心惊的藏北,却又担心车速快了万一遇到什么紧急情况来不及刹车而发生意外。这分明是一种在薄冰上走路的惊恐万状的心情。
进藏的路呀,为什么这样神秘、恐惧?
世界上的事往往叫人大惑不解:越是怕鬼偏偏就会遇上鬼。
大约是下午四点来钟,我们的车子莫名其妙地在桃儿九山上抛锚,变速箱裂缝。这种故障无法就地排除,只有等救急车来抢救了。
我和助手昝义成,还有一位乘车人——从内地探亲归队进藏的大校,三人像丢了魂一样在山腰急得团团转。谁会想到,我们为车抛锚而焦急的心情很快就转移了,昝义成在车前的雪地上发现了一具尸体。
我记得很清楚,昝的那一声惊异的怪叫声几乎把我的肉和骨头都吓得快脱开了。他像被杀猪刀戳了心包一样尖利地叫了一声:
“唉呀,不好!有人!”
我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便****了一句:“什么人让你这么吱哇乱叫?”
“死人!”
于是,我和大校就看见了那具尸体。
我们很快就判断出是个兵尸,死者的军衣已经扒掉撂在一边,他没带武器,身上有刀砍的数道伤痕。雪地上那凌乱的、密密的脚印告诉人们,他是在经过最后的挣扎后死去的。
我们围着尸体转了几圈,察看着。
昝义成把那件军衣捡起给死者盖在身上。他说:“他很可能是被一伙叛匪下了枪,害死在这里的。”
大校说:“这一带很不安宁。寡不敌众,他败下来了。”
我很同意他们的推断。当时,西藏部分地区正发生着叛乱,叛匪烧杀抢劫,无恶不作。平息叛乱的解放军无情地打击着叛匪。
在人烟稀少的藏北草原发生类似这样战士被杀害的惨案一点儿也不奇怪。
天气本来晴朗,只转眼功夫就飞扬起了雪花。我们三个静立于风雪中,脱帽,默默地哀悼这位无名的战友。
那位藏族阿妈就是这时候出现在我们面前的。我们事先没有预感到她会赶着牦牛来到我们停车的地方。她十分诧异地朝我们这三个军人和军车望了许久,我们当然也很惊疑地打量着这位不速之客,双方都仿佛在猜测着将发生什么洋令人恐慌、惧怕的事情。大概只一两分钟的功夫。只听见她一声吆喝,两头牦牛随之便卧在了地上。她对我们笑笑,从牦牛背上走下来。给我们一边说话一边比划起来。我们听不懂她的话,看不懂她的手势,她很着急,朝前迈了两步,站在那具兵尸跟前,又比比划划地说了刚才那番我们听不懂的话。
后来,我们总算听出了一点名目,她的意思是要把这具兵尸搬走。
这是我绝对不能接受的。昝义成也直摇头。惟大校仍在耐心地听着阿妈还继续比划着的“话语”。
搬走兵尸?她为什么要这样干?死者绝对不可能是她的亲人或别的什么与她相关的人,这就不能不让人怀疑她的用心了。当时,不仅藏胞对解放军缺乏了解,就是军队对西藏的现状也是一知半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这位阿妈要搬走这具尸体做出凶多吉少的判断便是很自然的事了。更何况我们几乎每趟任务都会看到或听说叛匪枪杀战士的惨不忍睹的事情。再加上那时候我很年轻,阅历少,懂的事情本来就不多,看问题出点偏差是情理之中的事。就说对这位骑牦牛的阿妈吧,从第一眼看到她的眼神我就有一种感觉,她今天不会对我们做出什么好事来。这不,她真的要搬走我们战友的尸体……
大校也许就应该比我和昝义成表现得成熟,他始终用友好的态度对待阿妈,耐心地听她的“表现”,还不时用半通不通的藏语与阿妈交谈几句。然后,他转身对我和昝说:“我听出点意思来了,她是说要把这具尸体用牦牛驮去天葬。”
“天葬?”我确实是第一次听说这个名词,很新,也挺怕人。
看来大校对天葬也知之甚少,他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摇了摇头,最后只能用很浅显的话这样回答我的疑问:
“就是让老鹰把尸体吃掉!”
我的心立即像触电般紧缩了一下,老鹰吃尸?太残忍了!不等我开口,昝义成就说话了:
“说什么也不能让他把尸体搬走,我们就在这里挖坑埋掉这位战友。”
我也解释起来:“他是我们的战友,是为保卫西藏而牺牲的,我们有责任保护他的尸体。”
听,我们的理由多么充足。可是,藏族阿妈并不听我们的申诉(她也听不懂)。就在我们三个人讲话的当儿,她吆喝一声,让牦牛起来,走列兵尸跟前,自己动手将那尸体搬到了牦牛背上。她既有力气又能干!但是,我对她没有丝毫的钦佩之情,只是恨她。因为她要把我的战友的尸体驮去喂老鹰……
我亲爱的读者,想你不会责怪一个十八九岁年轻娃儿的稚嫩和无知吧。当时,我实在不甚了解天葬是什么,总觉得那是一种像恶魔一样可怕的鬼怪。当然,今天我知道了,几十年的所见所闻、所学所悟,使我从一个不明事理的小兵嘎予成长为把西藏作为文学创作基地的作家。天葬是沿袭了七百多年的藏族丧葬风俗,被称为人间最超脱、最神圣的藏俗。在西藏,天葬不仅是一种葬俗,而且是一种文化,而天葬台则以具体的过程使轮回的信仰与教仪文化得以生存传播。
多么不容易呀,从对天葬谈虎变色到认识它的真诚和神圣,我经过了几十年的跋涉!
随之而来的,便是对那位没有留下名字的藏族阿妈的崇敬和深探的忏悔。在当时那样的背景和环境里,她冒着各种风险,执意要把一名被叛匪杀害的解放军战士的尸体,从荒野驮到天葬台去举行天葬仪式,这不也是一种精神么?爱有多深,情有多重!
……
阿妈骑上牦牛,走了。另一头牦牛驮着兵尸走在她的前面。
我不能容忍了,追上去,拦住了牦牛,说:“你不能这样做,他是为了藏家人才死去的呀!”
我知道我这么说她是听不懂的。可是,我还是要这样说。
我觉得阿妈似乎明白了我的意思,只见她勒住牦牛缰绳,停下,从牦牛背上下来,双手合十,放在胸前。然后脱下自己的藏袍,小心翼翼地盖在了兵尸上……我的心里得到些许的安慰,同时涌上一股难以名状的暖意。
这时,昝义成也脱下自己的大衣盖在那件藏袍上。因为我们都看到战友一只冰凉的手露在藏袍外……
藏族阿妈走了。她仍然骑在牦牛上,前面是那头驮着兵尸的牦牛。
这时,天色渐渐暗了下来。要是晴天,我会看到太阳落了山。
天空仍然飘扬着雪花,风不大,天气却十分寒冷。
两头牦牛,以及牦牛背上藏族阿妈的影子,渐渐变小。但是,它却不消失,总是在地平线上蠕动……
我望着,踮起脚尖望着……
三十年过去了,这影子始终没有从我眼中消失。岂止是没有消失,而且那影子越来越清晰,越高大。
阿妈,在那个令人心寒的年代,您就是雪原上一泓清亮的温泉。尽管您神秘的行动一度委屈地储存于我的脑海里,但是,您的魄力、魔力和引力是无法抗拒的。当我今天终于找到破译您的密码后,我和我的同事们受到了极大的震动。
我想,阿妈假如今天还活在世上,也许是七老八十的人了。可不是吗?当年不能理解您行为的小伙于也年过五十了。
您还是骑着那头牦牛走在藏北草原上吗?听人说,牦牛是长寿星,它专门在无路的雪山上跋涉,从不知疲劳。阿妈,我企盼您永远骑在这样的牦牛背上,走在终年不化的雪山上,走在连接藏汉两家的四千里青藏公路上……